她有两个灵魂
残雪最早的小说《污水上的肥皂泡》,邪恶、不洁的母亲,在叙述者“我”的幻觉中变成一盆发黑的肥皂水。另一个短篇《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阿梅(我)的母亲和丈夫关在厨房里剥蒜子,“两人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婚后第二天丈夫在屋角搭个阁楼“跟你一起睡我总害怕”,后来丈夫不回家,母亲“仿佛就因为这件事对我更加怨恨”。
几平残雪所有的小说里,母亲的形象总是扭曲、丑化的,与叙述者的“我”永远水火不容。
问起她在现实世界里与母亲的关系,残雪很平淡地回答:
“也就是一般,一家九口人才几十块钱,她没时间管我们。”
一九五七年,残雪的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列为“极右”下放,她的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
她从小跟外祖母,一九五九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自然灾害时,残雪和她的兄弟靠着外婆上山采的野菜和菌类保住性命,外婆因绝食和劳累死干水肿。
“外祖母特别神经质,又特别坚强,她生了十个小孩,生个死一个,最后只剩下我母亲一个。”
《美丽南方之夏日》一文中,残雪深情地描绘与她相依为命的外婆
“外婆年轻时一定是个眉清目秀的美女,她的牙齿很白,很结实,能咬断细铁丝。她是异常刚毅的,但周身总是缭绕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她会在睡下之后突然惊醒,猫着腰去监听一种不明原因的骚响,还用手中的棍子拨出哗哗的声音。”
残雪对遗传深信不疑,她的神经质是天生的,得自外婆:
“月光下,她的全身毛茸茸的,有细细的几缕白烟从她头发里飘出,我认定这烟是从她肚子钻出来的。‘泥土很清凉’。她嗡嗡地出声,‘只要屏住气细细地听,就有一种声音。’她又说。
“天井里传来‘呼呼’的闷响,是外婆手持木棒在那里赶鬼,月光照出她那苍老而刚毅的脸部,很迷人。她躬着驼背,作出奇怪的手势,叫我跟随她。”
一个懂得看手相的人,断言残雪有两个灵魂,呈现在文学世界里那个鬼气的灵魂,与世俗中与常人无异的灵魂两者是截然撕离开来的。
两个灵魂有时是否会交叉,相互干扰’
残雪说当然有一点,我还是理性很强,以后可能不会恶化,中国人的韧性是不可想象的。外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情感的经历跟一般人不同一些,复杂一点。
在日常生活里,她称职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问起她与曾为“有名气的木”、现在打理裁缝店的丈夫感情生活如何?
残:(不加考虑地)当然算好的!
施:要求他懂得你吗?
残:不要求。我还是比较实际,注重一般意义上的感情。
施:有谁比较可能理解你?或者一个都没有?
残:文学上最接近的,是写评论的那个哥哥。十六岁被打成巨革命,一直想搞创作,长篇没写成,索性搞评论韩:就是写《真的恶声》的唐俟。他评《苍老的浮云》。结语说:“六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悲愤于中国文坛的寂寞。曾经热切期望过能发‘真的恶声’的‘怪鸱…,现在他的妹妹残雪使他听到一种真的恶声。
现代主义都是即兴的
残:我写这种小说完全是人类的一种计较。非常念念不忘报仇。情感上的复仇,特别是刚开始写的时候。计较得特别有味。复仇的情绪特别厉害,另一方面对人类又特别感兴趣。地狱里滚来滚去的兴趣。
韩:她是对整个人类生存方式感到不合理,到哪里都是不合理。并不是只限于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她的愤怒不同于伤痕文学的愤怒,而是对整个人类生存方式的愤怒,
施:有人认为文学是一种发泄,将内心的阴暗呕吐出来。达到驱魔的功效。
残:那是现实主义,我不是那么一回事。
韩:她完全创造另一个世界,和我们听看的现实世界不一样——
残:(急急插嘴)实际上又是一样:
韩:一一当中有很多现实的因子,她将它打碎
残:我在塑造自己的世界,人家进去不了,完全进入我的作品也不可能,就要变成我自己。
施:你这种独树一帜的欲望很强。与众不同时你这么重要吗:
残:我本来就不同,现在拼命把这种不同夸张表现。原来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就赶快表现。
施:和读者取得共鸣、交流是不可能的:
残:肯定没有共鸣,至少读了能体验我个人的气质,慢慢会有些人欣赏,现在太少了;
施:有没有感到不被理解的寂寞?
残:无所谓,反正就是这个样子。
韩:她最早写《黄泥街》捕捉一些荒诞的感觉,写法比较写实,她自己不满意,第一稿没写完。
残:刚开始没看现代主义的作品,家里没这些书。从前读了些鲁迅、托尔斯泰、果戈理的小说一九八三年写《黄泥街》,边写边看翻译的现代主义作品,喜欢卡夫卡、怀特,美国女作家——写《伤心咖啡馆之歌》的,记不得作者的名字。
施:卡森。麦卡勒斯。
残:那时创作还很模糊,不知道要不要,能不能搞,后来感觉要搞,一种说不出来的冲动:
韩:第一稿《黄泥街》和第二稿发生什么变化?
残:主要是内心升华的过程。写实主义的写法不过瘾,有些东西说不出来,非得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才说得出来,写第一稿时,没看外国现代派的作品,就知道只有那么一种写法。
施:受哪个作家影响最大?卡夫卡?怀特?
残:川端康成对我影响也很大,但我的东西跟他没一点接近。
施:文学的敏感或许勉强可找到一点联系,思维上完全不同。
韩:就你理解,什么是现代派的文学?
残:现代主义都是即兴的。 卡夫卡的《城堡》就是即兴,写完了还不知道搞什么东西,几十万字。
施:你不以为他是在演绎一套理念?
残:这是后来评论家硬套进去解释的,他的作品可以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并不是由于思索,而是来自内心情绪的积累。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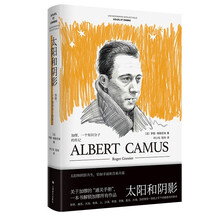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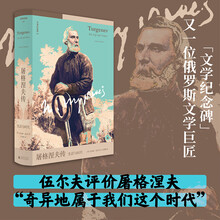





这本散文集里主要收录的是我的一些读书笔记,其中一些产生过较大影响。我是一九九七年才开始写这些读书随笔评论的,这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搞了十多年创作,才开始写这种文字。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某种东西在我的内面已渐渐明确起来,对自己的创作作一个总结的时刻到了吧。评的是别人的创作,讲的是关于自己的创作观念和体会——这种写作同样令我入迷。我所写的,都是我喜爱的作品。我认为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经典性。我想,经典并不是一种靠智慧和理性就可以达到的境界,经典是一种虔诚的、有点神秘的感悟。作家在创造时绝对不会是清晰的,应该说,他们写下的,是自己从未体验过的、出乎自己意料的、而又在多年里在下意识里向往的东西。他们一旦被这种东西牵引,立刻就走火入魔,不顾一切地进到了那个对于每个个体是陌生的,但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巨大王国。而对这个王国的每一次探索,都是一次英雄主义的壮举。我的文字,则是对这类绝唱的应和。
我还会把这类文字写下去,我既评价别人,也评价自己。我想,对于我这种写特殊小说的作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精神上的调整。我现在已想不出,除了文学之外,还有什么能使我的注意力如此地集中。读者将会在书中发现,即使是写生活方面的文字,字里行间透出的还是那一件事:人性中的矛盾——这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我写不来休闲的文字,也许永远写不了,我的文学生活太紧张、太令人激动了,没有时间休闲。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令我很高兴,有心的读者可以从中读出我的文学的大致模样。一个作家,不论多么难以被人理解,他的这类文字总会给读者透出某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