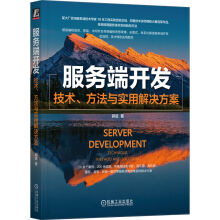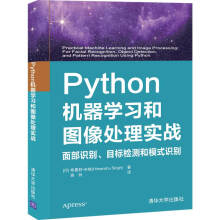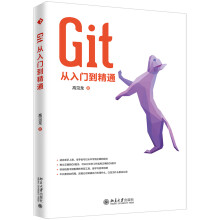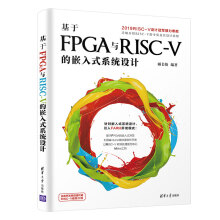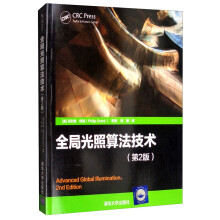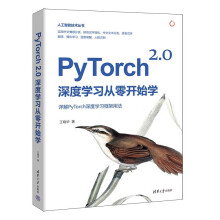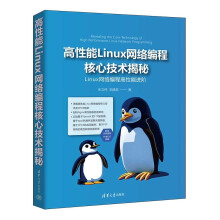不朽的斑斓回忆 ——说不尽的两宋文明 宋人笔记《蓼花洲闲录》中,有这样一则记载: 宋神宗因陕西方面对西夏用兵失利,迁怒于一个主管运粮的漕官。愤愤之下,他亲自书写御批,命令中书处斩此人。转日,宰相蔡确率群臣上朝。
宋神宗问:“昨日御批斩人,今已行否?”蔡确回答:“为臣我正想向陛下奏告此事。”宋神宗闻言不悦:“又有何疑?”蔡确回答:“祖宗以来,未曾杀士人,臣等不欲陛下开此先例。”神宗皇帝沉吟半晌,说:“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远恶地。”时任门下侍郎的章悖当廷接言:“如此,不如杀掉此人。”宋神宗感到奇怪,问:“卿何出此言?”章悖回言:“士可杀不可辱!”一句话,激得神宗皇帝勃然大怒,声色俱厉道:“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龙颜雷霆之下,当朝的宰相、群臣不仅没有在“天威”下震慑惶恐,傲然顶嘴的章悼反而不成不淡回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宋神宗默然。
这样的场景,只是大宋王朝三百多年间一个小小的片断和插曲,但它包含着无尽的寓意。首先,可以见出,大宋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明的王朝。即使口含天宪的帝王,也并非能够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其次,时为侍郎的章悖,日后被史臣赫然列入《奸臣传》,此人党同伐异,“老奸擅国” 。同时,他又是大文豪苏东坡最好的朋友之一,证明了历史人物的立体多面性:“坏人”不一定全坏,“好人”也不一定是完人。
当然,时人言起宋朝,自然首先会想起“靖康之耻”的奇辱和“压山之役”的惨败。相较大汉盛唐、朱明满清,两宋的领土小得可怜,北宋最盛时也只有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别是赵匡胤开国以来“重文抑武”的国策,使得宋朝长期陷于“防御”的狼狈境地,积弱至亡,甚至出现同样的悲剧上演两次这种超奇怪的现象。其实,在我们抚膺叹息之时,大多数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晚唐以来,中原王朝的崩溃所导致的大分裂。致使北中国一直战乱频频。沙陀人石敬瑭更是把燕云十六州献奉给契丹人,深植下其后北宋王朝的滔天大祸。而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诸族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刀光闪闪,血肉翻飞。从现在的眼光看,残杀、争斗自然是波澜壮阔的 “民族大融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就当时来讲,宋代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剑影之下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连年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消耗,以及两次亡国的痛苦过程,使得宋朝人民辛勤创造出的财富一而再地化为乌有。最重要的是,战争使无数百姓死于非命。13世纪初,金朝占据的北中国有五千多万人口,南宋所占的南中国有六千多万人口。蒙古号角吹响后,经过七八十年问的杀伐,至南宋灭亡时,江南及中原地区的人口竟然从原来的一亿人多变成只剩下不到六千万人,这还有赖于元臣耶律楚材的一句劝说,蒙古大汗才没有旋行把北中国“汉人”杀尽以其地尽作牧场的政策。由此可见,文明,尤其是刀锋之上的文明,是何等的脆弱! 汉文明白身的发展总是依据“盛极而衰”的规律脉动,宋王朝也避免不了这种刻骨的悲剧。它的文化水平在当时来讲太先进,文明程度太让人过于陶醉其中,即使囿于一隅,士大夫头脑中仍觉得自己所居之地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自恋至极的宋朝中国人(当然他们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级而自恋),像极了一个酒足饭饱、事业有成而又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他太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记体内的衰落和“高度发展”所引致的迟钝。最让人恐惧的是,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野蛮人垂涎于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逐水草而居之余,他们如同窥视猎物的群狼,随时会蹴然一跃,扑向这些定居的、文明的、软弱的好邻居。野蛮毁灭文明,于野蛮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于文明人而言,却是万劫不复的、可悲的停滞。
暂时忘却那些宿命般的悲剧历史,回顾三百余年的文明成就,确实让我们对伟大的宋朝有骇然惊叹之感。遥想先辈,他们发展高度文明的能力一次又一次被摧毁,国家一次又一次遭受惨烈的灾难,但华夏人民充满激情的创造力、勇往直前的理智力以及百折不挠的意志力,皆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
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也化为过眼烟云。我们却无法否认那一个灿烂时代的不朽与光荣。往事越千年,我们的鼻孔中仍能嗅到那三个多世纪汴梁与临安传来的梅花香气,还能依稀听闻诗人词家那一叹三叠的华丽咏叹。正如一位高卢诗人回忆罗马的辉煌那样:“不可能沉没的身躯,会以不可抗拒的活力重现。它们从深水中反弹而起,将跃得更高!火炬倾翻,反而燃得更亮!你,不朽之城,沉没之后反而更加光芒四射!”(纳马提阿努斯《循环往复》)是的,伟大的宋朝并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它崩溃的瞬间,也如流星陨落一般,照亮了野蛮的黑暗,驱散了内心的恐惧,足以启发后人的心智。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宋朝,伟大的宋朝。已成为永恒。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回顾一下那个与野蛮为邻的伟大时代的方方面面,籍此把记忆的碎片黏合起来,重组三百多年问我们不屈不挠的先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思想方面,随着佛老在中原的失势,宋朝科举制相比唐朝更加注重公平竞争。在《宋史》中人传的近两千人中,平民或庶族中小地主出身的人士竟然高达近60%。言论宽松,议论自由,是那个时代的大趋势。同时。宋朝经学,即两汉以来的对儒家典籍的阐释之学,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士人把章句训诂改为义理阐发。由此,性理之学蔚然大观,北宋有王安石新学、周敦颐濂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南宋有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叶适事功学等等。虽然宋儒理学在日后逐渐发展成为国人的思想桎梏,但就当时来讲,正是对两汉经学和盛唐佛学的推陈出新,粲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以儒学为根本的、兼收佛老及诸子学说的新儒学体系,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文学方面,宋词一洗晚唐浮艳之风,或豪放,或婉约,大放异彩。其中以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陈亮为代表;宋诗也不可小觑,其多于用典的浓郁书卷气,使得中华文化精髓每每跃然纸上,尤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刘克庄昂然执其牛耳,悲沉激荡,脍炙人口。
艺术方面,由于宋朝诸帝皆留意文翰,贵族士大夫亦步亦趋,绘画、书法方面人才济济,甚至徽宗皇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大画家、大书法家(北宋连铜钱上的铸字原体也由皇帝亲自书写)。抛开细腻华贵的“院体画家” 不讲,苏轼、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画”,使豪爽、性灵的“尚意”审美意境贯穿以后数个朝代,长盛不衰。在这种艺术风气影响下,宋代在制瓷、建筑、雕塑、舞蹈、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皆达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陈寅恪不无感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科技方面,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其中竞有三项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培根在《新工具书》中这样写道:“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与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能产生更大的力量影响。”自然,在农业、数学、天文、航海、地理、医学等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让,一部《梦溪笔谈》,不经意间已记述了数项独占鳌头的“新科技”。
政治方面,宋太祖进一步以皇权为中心加强中央统治集权,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权。而后,宋朝又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举考试、官员铨选以及监察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最开明的时代。因此,南北两宋三百多年。
先前与其后各个王朝屡见不鲜的女祸、宦祸、外戚之祸、藩镇之祸、权臣篡逆之祸、流贼覆国之祸,在宋代基本杜绝。即使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认天下“道理最大”,而并非口口声声“朕即国家”。外朝官员能够以“ 祖宗家法”的名义限制皇权,大体可按规矩依程序办事。宰相可把皇帝的“ 御批”攒至数十封一并退还不办(杜衍与宋孝宗),最终,皇帝不仅不恼,反夸奖对方“卿等如此守法极好”。这种君臣温情,在汉唐明清那些所谓的大一统、大有为君王的统治期间是全然看不见的。
经济方面,两宋更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商业社会,其多种经济模式均在世界上开一代风气之先。特别是城市的发展,“屋宇雄壮”,“骇人闻见” 。经济活动“每一交易,动辄千万”。瓦舍、勾栏,熙熙攘攘,娱乐、休闲通宵达旦,市民生活水平在当时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而且,中国首创的纸币交子、会子均在宋代出现并发展定型,这种革命性的货币形式比欧洲要提前六个多世纪。同时,一反前代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宋代商人不仅经济地位得到提高。甚至可以入仕为官,极大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士大夫还得出“商人众则人税多”的崭新价值观。
至于英雄豪杰,两宋王朝更是层出不穷,撼人心魄——杨业、寇准、狄青、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韩世忠、刘铸、岳飞、虞允文、辛弃疾、孟珙、余蚧、李庭芝、姜才、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等,这些忠臣义士,耿耿精忠,求仁得仁。求义得义,不以成败利害动其心,不以生死贫富移其志,才节两全,代表了我们民族至高至伟的精神境界。他们或衔命出疆,或授职守土,或一心为国,或感激赴义,或慷慨就死,或临难不屈,或捐躯殉国,功虽有不成。名却彪炳千秋! 当然,在历数了宋王朝的辉煌成就之后,我们不得不回到沉重而不能回避的话题,即两宋惊人相似的两次灭亡。
“本朝(宋朝)惩五季(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庸悔何及!”文天祥之语,触及的正是宋初矫枉过正的“抑武”国策。当然,王朝灭亡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某个领袖人物的死亡甚至会改变整个历史进程,比如钓鱼城上飞掷而下的、那块击中蒙哥汗的石块,它就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道。但除却天时、地利以外,人是历史行为的最关键因素。正是人为的懈怠,文怡武嬉,不思进取,才最终导致两宋的灭亡。南宋亡国有三要素:民穷、兵弱、财匮,正如王应麟分析的那样,皆源自当国士大夫的无耻。特别令人慨叹的是,大敌当前。南宋朝野上下那种怡然自得的苟安心态,让人切齿扼腕。
宋金隆兴和议后,双方和平状态保持了大约四十年之久。为此,金世宗获得“小尧舜”的美名,宋孝宗也被当时后世腐儒赞为“仁恕”之主。然而大儒王夫之对此很有洞见:“呜呼,此偷安之士。难与虑始之民,乐怀利以罢三军,而不恤无穷之祸。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听之哉?宋之决于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来,宴寝不忘者兴复之举,岂忍以割地终之。完颜雍(金世宗)雄心虽戢,然抑岂有厌足之欲,顾江左而不垂涎者。故(议)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始以息民为名。贸贸者从而信之,交起而誉之,不亦愚乎!” 细究历史,会有惊人的发现:宋金两国,相踵亡于蒙古,其实最早的祸因正是肇于两国当时的和平“善举”。
金世宗史称为明主,但其实也是篡弑之君,因此,他心中肯定认为自己能为众人推立为帝已属天幸,所以,他对南宋的“退忍”和一切“和平”努力,其实出于无奈。至于他“息祸养民”一说,只是腐儒和马屁精的谀词。
“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窥之”,野蛮民族只要确定了开始想向“文明”迈进,他就会忘掉身边又会有像“昔日之我”的更野蛮民族蠢蠢欲动, “一息之余,波流日靡,大不可息之祸,亘百余年而不息!”由此,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中深刻认识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一旦金戈铁马的女真人习惯了风花雪月,蒙古部族的嗷嗷叫声就肯定由远而近,金朝、南宋,就会在血火之中化为文明的碎片。
确实,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南宋对金国不搞姑息议和那套投降伎俩,不断深入进击,派军队攻伐中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练兵鼓舞士气,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后起少数民族闻之惊惕,对宋朝心存畏惧之心。反过来讲,宋金争斗不歇,金国一方也会持志不懈,日习于战,不会逐渐消沦其昔日的勇武好斗。宋金持战不歇,即使是金人兵强占据优势,每年都乘秋高马肥之际逼临江淮,“宋亦知警而谋自壮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师一临,而疾入于海以亡”。历史中可以得见的是,金兀术昔日南侵最大的 “结果”,就是使南宋涌现了岳飞、韩世忠、刘铸这样的忠勇大将,福兮祸兮,实相倚依。于金国而言,恰似当年南北朝时代的北魏,待其一息方新之锐气,通好南朝,安宴于洛阳享天下之际,六镇之祸正由此肇始。彬彬文治,最后的结果是拓跋氏赤族无遗之祸。因此,在血与火的时代,在危机四伏的世界,最怕的就是整个国家“乍然一息”。什么“以两国人民和平意愿出发”,什么“一衣带水、自古友好邻邦”,长此以往,忘兵忘战,国民肯定会溺于安乐享受,一切忽然之祸,正是种于“缘饰文雅”之时。
可悲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从来不汲取历史的经验! 时下的许多历史书籍,皆以“恢宏”的煽情修辞或对历史晦涩的“解构 ”当成卖点,常把《万历十五年》那样以“偏门”剖析历史的准历史研究当作模仿对象,各显身手,纷纷从经济、军事、气候等“专业”刃面“切入” 历史研究。可惜,这些“大部头”著作往往忽略了历史细节的描述,而有些作者功底的不扎实又使这些“大历史”叙述错谬百出,或张冠李戴,或弄混朝代,或把演义人物当成历史真实,凸显出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此外,历史“剖析者”们在铺陈华丽语句大谈特谈历史的“规律”时,他们往往故意忽略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戏剧性、决定性作用:钓鱼城下王坚所率宋朝守军扔下的一块石头,如果离蒙哥汗的身体偏上十厘米,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全部世界历史都将被重写!所以,在学者们以佶屈聱牙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因素试图重新诠释历史的时候。那些真正对历史产生决定性意义的个人和事件,却被不善于注意历史细节的学者们有选择性地“遗忘 ”了。
作为一个甘于坐“冷板凳”的历史守望者,笔者总是试图突破“历史样板戏”写作的桎梏,仔细钩沉,复活那些淹没于茫茫时光中的血肉人生,把已被“格式化”的历史文字,转化为鲜活的、生动的、甚至是“现场的”!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恢复我们民族伟大的、不朽的记忆! 最后,我想以南宋遗民林景熙一首《京口月夕书怀》作结: 山风吹酒醒,秋入夜灯凉。万事已华发,百年多异乡。远城江气白,高树月痕苍。忽忆凭楼处,淮天雁叫霜。
是为序。
赫连勃勃大王 (hlbbdw@163.com)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