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的爪哇研究专家对吉尔兹的文章提出批评——吉尔兹认为爪哇和巴厘的国王更是一位精神领袖,而非军事上的领导,这位学者不无讽刺地指出,“对于国王与王宫大臣而言,那些认为国家只是掌握权力、发家致富的手段的人,那些立志要当将军的人未免有些奇怪”(Ricklefs,1992)。但我在此并不关心巴厘政治图景的正确性,而是另一个事实:即使是在一个伟大的学者那里,对仪式话语和异国(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象征主义,或“文本”的强调,也可使巴厘人似乎与我们迥然不同,而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差别并非如此之大。由于忽略了人类认知的某些方面具有普遍性这一明显事实,从而导致写出一种“普遍性”的历史大叙事比它们的实际存在更难,而它们已经存在了——带着共享一种全球历史意识的严重后果。无论人们怎样囫囵吞枣似地接受粗糙的唯物主义,它都能使我们反对某种形式的东方主义,并可以不断提醒我们,无论新文化史家同意与否,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须完成养育人民、创造经济盈余的任务。当稻米的收获直接关涉到巴厘人的日常生活时、当多数文化都拒绝与社会隔绝时,可以发现前现代巴厘人的(比如说)“时间”概念并非鲜明区别于其他文化。新文化史的“差异”如同旧的现代化理论的“深层结构”一样在其每一个点上都有可能是一种虚幻。
吉尔兹之后出现了许多后现代主义分析家,他们将文化凌驾于社会之上,其做法已超过了吉尔兹,在德里达的文本生产和“文本化”适用范围扩大化影响下,这些人觉得获得了解放,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方法的对立与我们无关。我认为他们却不得不来证明这一点。当利奥塔告诉我们成功地达到正义的观念和实践的第一步是认识“语言游戏的异形性”,而不是财富分配的性质(不论其是否异形)时,他是在冒将自身禁锢在分析的唯心主义诸形式之中的风险,而这种形式只有在任期内或即将上任的教授才会喜欢(Lyotard,1984:66)。
但这样如何能协调中西理论界——协调,而非将二者同一——呢?很明显,在此只是让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知识分子危机不是如假设的那样具有普遍的可交流性是不够的;只认识到当中国的学者参考西方历史(同时西方的学者也作反向参考)时,可以丰富全球性的知识也是不够的。二者理论上的协调还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或其他方面的说明,说明乔恩·斯科特(Joan Scott)在捍卫福柯之时未能成功解决的问题,即人类行动(agency)的问题,或者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积极地影响我们自身的进化的问题。
如果西方史学家将世界视为是后现代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则可将之视为是后殖民的。在后殖民情境中,我们亚洲的同行痴迷于重新发现创造历史的行动(agency)。最近西方对于经济现代性的价值,甚或其“客观性”的否定,也许是一种假装的否定,企图以此掩饰西方对于非西方人民——他们热望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歧视,尽管他们这么做时不得不使用一些(用某种后现代主义的行话来说)“精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叙事”来作为参照点。
当然,更大的歧视,与最近西方对于人类行动(agency)之可能性的哲学解剖的更高的批判敏感性,这二者并不一定是相互对立的:西方的中国史学者(于是)转变成二流的东亚经济繁荣
的捧场者。但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他们都是西方人,对科学作为真理的特权,以及对科学与修辞学无关的假设所进行的质疑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建议我们要警惕科学与社会统治形式之间的联系。人们猜想如果后现代主义将来在中国流行起来,那就是因为人们不断认识到科学主义既可奴役人又可解放人,即使它(科学主义)蕴含在现代化的计划中。当这些发生时,一个对亚洲后现代时刻到来的早期预感,也许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未来学家雷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为之滥觞的有关“谁来养育中国”的讨论(Brown,1996)。
整个亚洲范围内以布朗(1996)有关30年后中国食物供给的末世预言反响强烈,可以写成一本书。即使是在新加坡这样的农民命运不是主要话题的国家中,兴趣也很浑厚。正如中国农业部曹力群所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由一个美国的未来学家所写的短文会引起如此之大的全球性关注?在最新的分析中,亚洲方面的争论并不是真正针对农业,而是针对20世纪末亚洲与西方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基础仍然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亚洲的傲视:认为亚洲没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
众所周知,布朗(1996)用科学的语言预测,由于中国经济和个人收入的高速增长率,以及由其导致的在饮食方面的改变,再加上土地和水资源移做他用等原因,中国人的谷物供给需求将会在2030年大大超出自身供给力,从而导致全球性的食物供给灾难。后现代主义者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寓言性的未来主义文本表面上并不刻意体现政治,实际上却是采用了一种谈论政治的手段。据我所知(当然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学者中尚没有类似做法,回应布朗的中国经济思想家(胡鞍钢,蔡防等)以乐观科学主义来对抗布朗的悲观科学主义。但他们在总结布朗之错误所在时,全体一致,认为布朗在脱离社会现实的预言中,忽略了人的创造力和原创性,特别忽略了像中国的农民、商人、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这样的行动者(agents)将如何创造性地回应生态和其他压力(Renkou yu fazhan luntan[人口与发展论坛],1996)。考虑到这些加强了对人类行动(agency)的自信而不是相反,这一事件实际上对一些中国的后现代视点暗示了一个正在生长的机会之窗。
从根本上讲,中国和西方的理论制造界需要彼此沟通,对此仅靠对科学和“科学文本”的怀疑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借助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的怀疑态度,在此方面,比起内方后现代主义者目前所倾向实现的,他们应该做的更多。这再次包含了西方的去地区主义。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对所谓的四方哲学中心灵与肉体、说与写、中央与地方、认同与差异的对立提出疑问是非常时髦的。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对解构同样突小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对立却没有一点兴趣。但对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址,正当中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地位时,日本汉学家——他们在二战以前便提出宋朝就某些基本特点而言是“现代的”——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将受到新的关注。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去地区化的、真正的全球后现代主义的死后英雄(posthumous heroes)。非常可能的是,我们如此武断地称为“传统”和“现代”的东西之间的彼此交融要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理论语言所允许的范围,这使得现代亚洲经济力的再生看起来比其真实所是更为夸张。在此意义上,尽管沉寂的方式不同,但中国在过去也有相同遭遇,在有关人类事业的当代想像中,被忽视、被除名,并缺乏表现,这都与其他非西方少数民族如出一辙。
分配给这次学术会议参加者的任务是写一下理论是如何指导各自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方式的。这引起了一种反思,它强迫人们进行个人的考古学,考索那些对自己有影响的各种知识。以我为例,我是相当快地被吸引到历史叙事中去的——历史叙事是一种话语,它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总是受着这样或那样的抨击(Klein,1995)。这里无法把我年轻时代读过的历史做一个详尽的系谱学考察。不过简而言之,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父亲——他曾接受教育,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文气十足的历史学家——为我安排了常规的史学训练课程。先读希腊和罗马史学家的作品(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陀等),继而指导我读吉本、卡莱尔、麦考里,最后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至于19世纪早期法国史学家,如米什莱和梯也尔等,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当时我不过是个在法国上学的年轻学生。而大学老师则向我引介了马克·布洛赫和其他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特别是梅涅克和狄尔泰。我认识到,叙事要具有历史意义,就必须处在情境之中。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困难的是要学会区分历史和文学。当我从希罗多德转向修昔底德时,并没有问为什么后者让历史行动者自己说话。毕竟,希罗多德是作为雅典精英中的一员而写作的历史学家,他知道他所写的一切,这一点无可争议。可是,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却让我迷惑。当他写“我,克劳狄乌斯”或“贝利撤留”时,他是怎样知道书中的主人公所说的东西(Graves,1938,1948)的?这使我费了相当的时日才认识到乌姆贝·艾柯(UmbertoEco)在《纽约书评》中的一篇文章中所强调的区别:即一旦您插入对话,无论墩于其中的角色和情境来说是多么的真实,这都由历史转为文学(Eco,1997:4)。这在思考中国历史的真实性时是一个特别令人困扰的问题,因为中国史的“野史”传统——这一传统曾经十分流行,当时史学被认为是享有特权的叙事方式。当我研究明清变迁的历史时,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突显,因为在那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野史,也因为在一些野史中,作者小心地遵守了史家的惯例,并没有借主人公的嘴说出自己的观点,但在有些野史中,事实与假想(所见非所闻)间的界限在作者的想像中消失了。其结果是,现代历史学家不得不自己决定众多材料中哪些更为可信,哪些文本相对于特定的历史的过去——如满洲人人主中原时,那时,各方的举措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更加真实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在写作《顺治空位时期》和《洪业》的部分章节时遇到的最大困难(Wakeman,1979,1985)。第二大困难则是,我试图将多种叙事的声音(它们保有各自特有的方式)与分析的声音(这些都必然是外在和分离的)糅杂在一起,最终,在描述中分析。直到那时我才认识到狄尔泰说的用“感觉去分离”是一回事儿,真正用巴赫金的对话的“两个声音的词”去写作又是另一回事。比如,我发现《大门口的陌生人》比我早几年出版的小说要难写得多,这正是因为需要将两种向度的声音编织在一起。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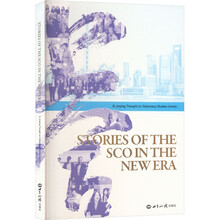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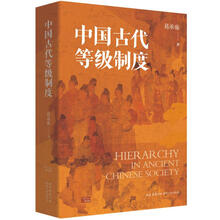




这个论文集的最初想法是围绕“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主题(或者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来组织讨论,或许以两位与会者之间的争论为开端。随着会议议程的进展,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如果彼此之间的交流不是以针锋相对的互相批驳为指向,而是作为通过在更为广阔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适用”的主题下由每个讨论者作自我反思,这样的交流也许更富有成果。其后,有的人在撰写论文时,强调自己的历史研究实践更多于理论的探讨。展现在此的这本论文集是最终的产物,文章事实上包括三个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普遍意义上理论的运用与误用,以及历史研究实践。
后现代主义:赞同与反对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章论说需要对现代民族国家在史学领域传播的民族主义主题进行“反思”。杜赞奇特别指出了将历史等同于民族史,将历史归于线性发展,和将历史归纳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建构这三点。他最后总结道:作为史学家,如果我们不愿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充当“被动参与者”的角色,那么就需要对自我进行反思。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同意杜赞奇所认为的有关民族国家主义对历史著作所具有的强有力的组织性影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论我们的背景或内心倾向,要求置身其间的每个人都归属于某个国家,并且是单一个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主义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使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在国家边界之内用“想像的共同体”宋划分历史才是理所当然的,并将之划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阶段。对于这些现代主义假设的批判性检讨的确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贡献。
与杜赞奇相比,本次讨论会的其他与会者虽然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更多保留,不过大家都肯定了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其他方面的贡献。亚历山大·伍德塞(Alexander Woodside)肯定了它对推翻美国大学中社会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之间旧的区分,以及提高我们对实证主义科学的用语与假设的敏感所做出的贡献。我自己则提到后现代主义对纠正旧社会史中“隐含的唯物主义”和诸多社会科学中西方中心主义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亚历山大·伍德塞和我的论文的重点是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伍德塞特别指出后现代主义由于其“欧洲中心感”,而导致无视非西方国家人民对现代化的渴求。后现代主义把西方所关注的问题普世化了,这一点特别反映在他们在认识论问题上的“着迷”和“焦虑”(伍德塞认为这种特殊的西方式倾向可以追溯到教权衰落时期),这样的倾向与“东方主义”很相似,虽然这正是他们历来所批判的。我在论文中特别强调了萨义德(Ed-ward Said)和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主观主义认识论。当把事实化约为单纯的主观再现时,他们抛弃了对历史研究实践来说至关重要的真理理念。
周锡瑞(Joseph Eshrick)通过何伟亚(James Hevia)新近有关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的著作而提出了自己对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这本书被一些人肯定为后现代主义方法指导的新学术研究
样板。周锡瑞给出许多例证,指出何伟亚书中众多对文本的误读和他认为的对论据的误用。他否定了何伟亚对清廷处理此事件的态度的重新建构。周锡瑞认为在该研究中的众多失误也许就是因为何伟亚深陷于后现代主义的理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