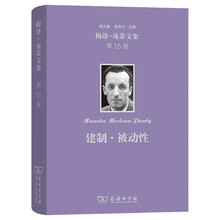当我们说起“某某哲学”(如艺术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时,我们打算指的是那种源自我们思考这某某事物时的一类想法。这些想法必定是哲学的,也就是说,它们一定是普遍的和必然的。诸观念意外地联系起来,例如,框定的讨论与艺术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哲学;若非在思考某主题的每个人心中都引发一种普遍的和必然的意识,没有什么思想可以声称是该主题的哲学。
有鉴于此,从该主题的哲学中,我们必须不仅把意外的联系排除在外,而且,在科学思想不同于哲学思想这种意义上,还要把被称为科学的特殊类别的思想排除在外。科学思想只是在普遍适用于有限范围的意义上是普遍的;这是一种经验普遍,不是绝对普遍;它适用于构成某个研究领域的所有事实,而不是无论什么样的事实;反过来说,如果它适用于无论什么样的事实,它就不再是一种科学定律,而是一种哲学规则;在数理逻辑学家看来,这正是数学遇到的事情。他们错误地认为,数学对任何事物都适用。
因此,某种主题的哲学必定不包括任意的或假想的东西。它不能由该主题的诸种分类组成,甚至不能包含它们;因为每一种分类都是任意的,既然它不过是一种分类,就能被取缔,或者被其他东西替代。这样,把艺术分成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或者分成空间中的艺术和时间中的艺术,这在艺术哲学中是站不住脚的;在历史哲学中,将文献分成书面的和非书面的也是如此。如果能够证明这些分类不只是分类,即如果能够证明它们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思想,是任何思考艺术和历史的人心中都会油然而生的思想,它们在该主题的哲学中也仅仅能要求一席之地。它们若只是单纯的分类,即划分研究领域的简便易行的方式,那就不属于哲学了。
同样地,哲学研究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假想的东西。在其中,我们不能想象某种主题的完美典范存在,如一幅美轮美奂的绘画或一部绝对真实或详尽无遗的历史,其原因就在于艺术哲学或历史哲学关注的是研究艺术或历史完美形态的观念,包括尝试阐明或界定这种观念:这样,先假定我们已经明白这种完美形态是什么或者会是什么,再继续研究就不合理了。例如,柏拉图通过勾画了一幅理想国的假想图画来对政治学进行哲学式研究,这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在单一政治制度存在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抽象而得出的这种完美的城邦观念,篡改了政治生活的现实,而留给我们一种政治理论,其价值(它具有极高的价值)恰恰在于柏拉图没有严格实践自己的计划。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