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也许可以通过自己对本丛书所评析的文本的仔细阅读,发现这些作品中的的更多后现代特征。甚至从自己的新闻记者经验出发对已有的种种后现代主义定义作出质疑甚至重构。我想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作为本书编者,我们也就感到掀起慰了。当然,后现代主义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成熟的实验性特证,由于它在意义上的不确定性、结构上的不完整性和情节上的偶然性,对它的理解或许有着种种障碍。但是我只想提醒广大读者,后现代美学精神的一个主旨便是反对意义的确定性和价值的终极性,历此对后现代文学作品的解释也就没有一个确定的模式,不同的读者也许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期待视野发掘出同一部作品所蕴涵的不同意义,因而对同一部作品见仁见智也就是十分正常的了。总之,我们也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书各位作者的不当观点提出批评指正。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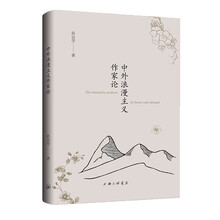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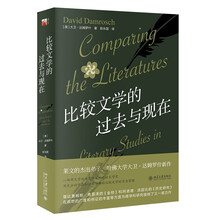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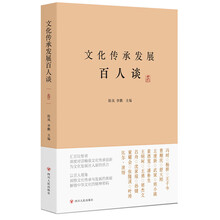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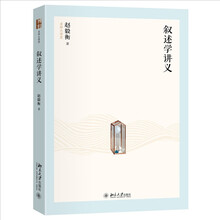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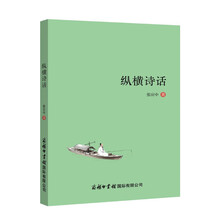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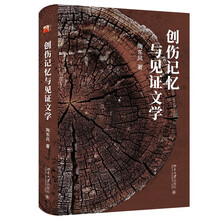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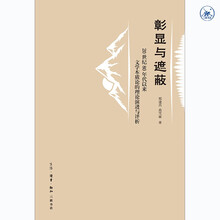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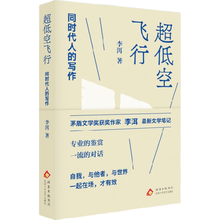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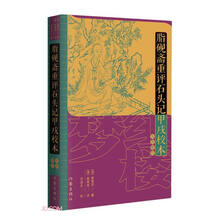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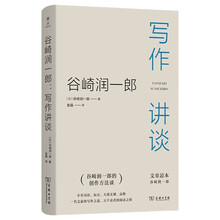
早在1998年,我还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任教时,曾应天津人民出版社约请,主编了一套三卷本的丛书,当时的总标题为《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名著导读》,分为小说、诗歌和戏剧三
个分卷。虽然我本人并不喜欢用”现代派”这个术语来把一部分已经明显有了后现代主义特征和倾向的作品包括在内,但或许是出于编辑的考虑,或者是市场所需吧,结果还是用了上述标题作为丛书的总名称。后来据说那套丛书销路还不错,一些大学还用它作为教学参考书或选修课教材。于是出版社编辑约请我继续将这套丛书编下去,但我考虑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用“现代派”这一过于宽泛的术语来概括所涉及的作品了。经过协商,我们为这套丛书的续辑定名为《西方后现代艺术经典》,只是由于目前的图书市场呈萎缩之趋势,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这个续辑定为两卷,分别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赵冬梅博士和北京电影学院郝建副教授担任分卷主编。在这两卷即将付梓之时,我有幸应编辑之邀写上几句文字,权且充作“序”。
毫无疑问,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大辩论,东西方学者大概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后现代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但它并非西方社会的专利品。越来越
多的事实以及研究成果证明,它有可能在某些先行局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以变体的形式产生。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文化交流和文化接受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某一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内在逻辑所使然。因而连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杜威·佛克马这样一批曾一度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可能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欧美学者也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国际性或全球性的文化现象或一场国际性的文学思潮和运动。我在此基于过去的研究,并且吸取我的西方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再次简略地对后现代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特征及发展趋向作出新的描述,以便广大读者从一个高度来认识和欣赏本丛书所评析的后现代主义作品。
正如美国学者、国际后现代研究理论刊物《疆界2》(BOUNDARY2)主编保尔·鲍维(Paul
Bove)所总结的,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有待于未来的学者去编写,但大家都公认,这场运动始自建筑领域,并迅速波及文化界和文学界,“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权威性著述中达到高峰,这样批评家们便将这一建筑学界的用法发展成为广泛复杂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晚期
资本’的‘逻辑’的叙述”。诚然,按照鲍维的看法,“詹姆逊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诸多思潮流派的仔细辨析,从而将这些流派与后现代主义内部的各种意识形态观念和立场相联系”。显然,詹姆逊的研究之所以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仅是因为他所居于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高度,同时也在于他在承认参加后现代主义论争的各种思潮流派的合理性之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独特描述和分析。此外,作为一位比较文学教授,他也并未忽视对文学文本的仔细阅读和分析,他对包括中国的先锋文学在内的所有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文学作品都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