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雪
素白的宣纸上落下几点浓浓淡淡的墨,便呈大地之雪,雪之景,雪之情。
我见过玉龙山月下显现的通体白亮的身躯,如偷看了苏珊出浴。春天在大巴山遇到一场突然降临的大雪,宇宙立即变色,高山上下,惟余茫茫。春雪来得猛,也融得快,雪片刚止,山间很快出现一块块墨黑,黑块迅速生长,呈现斑驳的豹纹,别具一种视觉之美,是出色的抽象绘画,只瞬间即逝。在喜马拉雅山麓,抬头惟见白亮的水晶宫,连眼睛也难于睁开,未备墨镜便无法欣赏。
平原、河谷、小桥流水……凡遇降雪,披素装,均显现洁净清新之美,雪景在摄影和绘画中是人们永远喜爱的题材。我画过许多旷野之雪,庭院之雪,雪虽都是素白的,但其情调意境绝不类同,这幅《春雪》着意于韵之奔流,虚实之间的缓慢转化。 伴侣
寂寞呵,寂寞无声,寂寞无形,寂寞留给人们细细咀嚼,品味,那是人生的真味。逝者已已,留下寂寞;前途茫茫,而今寂寞。寂寞在时空中没有定位,她飘忽,飘到人们面前,但并不予人慰藉,她又飘去了,使你更感寂寞无边岸。
朦胧的太空,无定形的线之流逝,忽然出现了伴侣,是红与绿的相伴,相恋,她们在太空穿行,她们暂时忘却了寂寞,她们是寂寞滋生的昙花。 老重庆
八年抗日战争,我居重庆郊区五年,忆及蜀中风物人情,仿佛第二故乡,故曾多次入蜀写生,每入蜀,情思脉脉,年光倒流。
矗立在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长江山城气势雄伟,鳞次栉比的重庆的独特风貌举世无双。从造型艺术角度看,其重叠、错落、黑白相间、垂线的统一与横线的连绵构成无比丰富的建筑雕塑感或雕塑建筑感。人家密集,彩点散泼,山径穿凿,是岁月营造之迷宫。山城兀立在滔滔大江之上,江中舟帆穿梭,樯桅林立,纷繁世事,从水上串连到山巅,上上下下人人靠步行,故蜀人脚力坚强,无愧山城人。
七十年代我用油画和水墨写生过重庆,画那密密麻麻的古老吊脚楼之林、黑屋顶白山墙之城,作风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予人感觉是具象的,其实须依靠抽象的手法,如果真具象地画一间一间的屋,则十年也无法完成。
二十年没有再去四川了,换了人间,今日重庆是何光景,谅决非故人之貌了。翻阅自己画集中的老重庆,又生怀古情结,因之用丈二巨幅挥写我曾赋予了青春的老重庆,山城旧貌于是又矗立眼前,蔚成壮观,愿她永葆青春,不随作者同衰老。
点线迎春
冬日,脱尽了叶,园林的一株老树曲曲弯弯垂挂着通身枝条,虬曲而蓬松,像欲覆盖、卫护一群幼小的生命。但树荫下并没有生命,只筛漏下阳光的斑斑点点,像似睁似闭的眼睛,窥视着周遭的人群。
一群老人围树而坐,晒着暖暖的阳光,默默无言,他们满足在大自然的温暖中,懒得说话,全不关心婆娑的树影。
当枝条变得分外柔软,并张牙舞爪般挥动起来,同时冒芽、吐叶了,树丛的色调于是天天换新装。昨夜还只是微微绿意,今朝忽见翠点纷飞,春天已悄悄到来?那边的桃花也绽出了红色的苞蕾。老人们仍来围坐,但来得少了,他们易感冒,怕风,连春风中也不敢久留,春风太活跃。年轻人替代了老年人,情侣们双双来到枝叶隐蔽处,但他们并非来欣赏春的姿色。春在哪里?显现在枝叶的点线上,画家创造了自己的语言:点、线迎春。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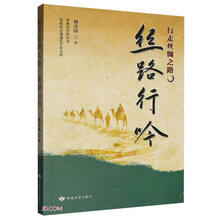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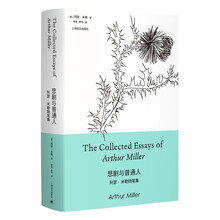




吴冠中
“同床异梦”,常被我用来比喻国画上乱题诗的现象,这一现象几乎泛滥成为艺术的灾祸,暴露了民族文化的衰颓。
苏东坡品王维的诗与画,说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其实王维的画面上从不题诗,苏东坡品味到其画中蕴藏着诗情,但他决没有料到自己成了始作俑者,从此引人混淆了诗与画的各自独特品质。绘画的视觉美感中潜伏着意境美,但决不可能被诗的语言美替代,我曾写过《扑朔迷离意境美》等文章,就是呼吁要重视对画的效果与诗的意境之不可相互替代的分析。
你作画,他题诗,是友情的留念;画家作画,找个诗人题诗,或非诗人的某个名人题诗,拉郎配,更是今日艺坛的常见花招,污染诗画之道,谁管得。
拆了墙是一家,不拆墙也是一家,诗画要分家,诗画又是一家,这种兄弟妯娌的关系确是不易相处的。绘画,依附形象美、形式美而生存,她的家园建立在视觉的世界中,失去了视觉美的家园,她便成了丧家之犬,这种经历与教训,老、中、青三代人都亲自体会过了。
我长期被批为“形式主义者”,我确视形美是绘画惟一安身立命的基地,但我之爱上形式美是通过了意境美的桥梁,并在形式美中发现了意境美的心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与人易于共鸣,我在朦胧中感到风筝不能断线,此线也,作品与人民感情间千里姻缘一线牵之线也。
自己写自己绘画作品的情意,很可能是多余的话,因绘画所未能表达的,求救于文字又有何补?但我也曾写过不少绘画作品题外话,是自己对作品的感触,颇引起一些读者的欢迎。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这集“画外话”,我竭力想写出创作心态的前前后后,裸露作者的隐私、隐痛、隐忧,她们正是我的美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