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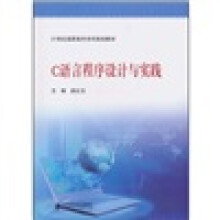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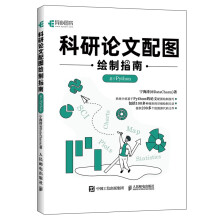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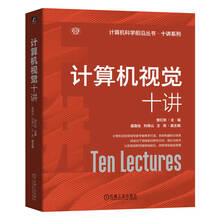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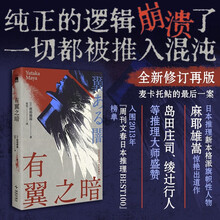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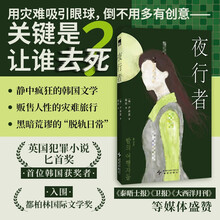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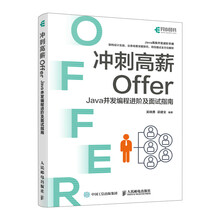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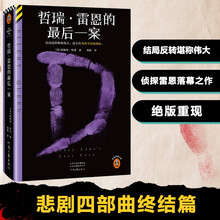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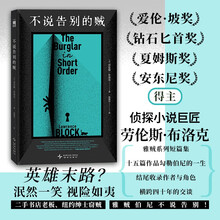
我们的视觉可以毫无异感地从形象看(或读)到文字,反之亦然。特别是对于中世纪读者来说,他们会很自然地根据其熟知的圣像学传统去读解每一个形象的含义,而把形象本身撇在一边。因此,这里的形象和文字是统一于书写的。在第二幅题作《死者弥撒》的插图中,一小段文字和一小幅绘画位于书页的中间,并为复杂的装饰性图案所包围。在图案和文字之间我们仍然可以多少感受到我们在第一幅插图中感受到的和谐关系,但一旦我们看到中间的那幅三度空间感的小画,那种和谐感便立即消失了。一种真正的视觉冲击使我们不得不把它视做一幅独立的、与文字完全“割裂”的绘画。而在第三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内封面中,一幅“自然主义”的绘画布满了书页,而其真正内容,《形而上学》的第一页被悬挂在画中的凉台上。在书页上尽管有大段的文字存在,我们却只想观赏它们。我们又感到了一种在文字与形象之间的和谐感,但这里显然有了一种反转——文字已然从属于绘画了。当然,这时中世纪也已结束了。
不过,在20世纪,人们突然发现,我们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中世纪(后现代?)。这是因为,在我们的世纪同中世纪之间有着某些明显相似之处。例如,根据艾柯的看法,“当我们进入[20世纪和中世纪之间的]文化和艺术的平行关系时,情景便表现得更为复杂。一方面,我们发现在两个时代之间有一种完全的对应,以不同的方式,它们都力图以其家长政治式教育的乌托邦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伪装来控制人的头脑,它们都试图通过视觉交流弥合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鸿沟。在两个时期中,文化精英们都以文字的心智思考书写的文本,但又都把基本资讯或知识和统治意识形态的根本结构转化为形象。”于是,艾柯在中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和20世纪的电视屏幕之间找到了连接点;
……
废墟的经验挑战了整体性,统一性、同一性、自明性、适当性、确定性和恰当性概念,粉碎了一切起源的、本真的、本体的和超验的形式。……于是,我们只能到那废墟中去寻找破碎的痕迹。
——耿幼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