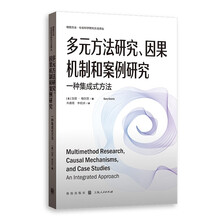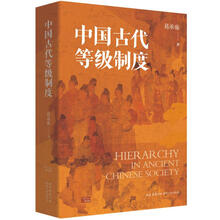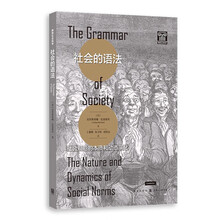而且,这一点对政策也有着其含义。实际控制,从它将受到个人无法选择的环境的限制这种最终的意义上说,这种控制是处在单个企业的生产关系之外的,如果这样,那么就可以推论说,单单改变控制的地理区位,单单改变阶级的区位,如果所有这些改变意味着由不同的人接替,那么就并不能解决问题。在市场力量的大海之中,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合作社可能有所有各种其他的社会和政治有利条件,但其从属于市场“外部力量”的程度,绝不亚于正宗的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获得对当地就业的真正控制权,还必须将生产撤出到市场力量作用的范围之外。这不只是应当提出对控制功能的诉求,更不是只提出对当地企业新人事的诉求,而且还必须对这些功能进行重新设计。如果当地控制权要成为真实的东西,它们就不能仍然由更广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来定义。
因此,“外部控制”这种宽泛、描述性的东西所产生的某些效应’,可能被过高估计或被错误解读了。它们是真实的,但从形式上看,它们与那些通常推导出的情形是很不相同的,而且带有政治意涵。
还有另外一些效应,在从总体经济所有和占有关系当中地理上不存在的功能方面形成外部控制的概念时,它们也是比较容易解释的。正因为如此,它们也是比较容易拆解的。
首先,与整个企业都位于一个地方的情况相比,分厂的当地收益放大效应乘数(multiplier)可能较小。这是由于收益向更具战略性的占有功能所处的总部地区流动所造成的,换言之,是由于主要采购职能的集中化造成的,这些职能既处理资本投资,也处理服务,特别是所有各种企业服务。在许多研究中都已经发现,这些职能在分厂可能是不存在的,而这反过来可能意味着在当地进行较小比例的采购——因此使得当地收益增值作用较小。这种作用的重要性是可以进行经验研究的,而且情况肯定会各不相同,例如,因这种采购物品和服务的市场区域范围是否仅限于所在大区域或者仅限于当地而各不相同。然而,就确实产生这种作用而论,它有着若干含义。它降低了国家地区政策的潜在推动作用,这些政策原本是设计来吸引跨地区和跨国资本投资到衰落区域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