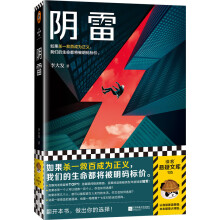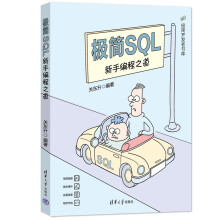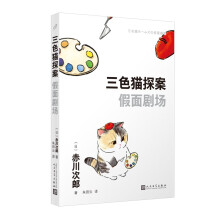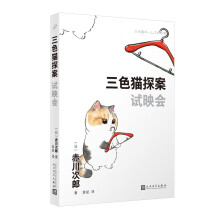并接着说,这个惩罚所带来的无论何种羞辱,他都愿意与其他亲戚一起承担。日复一日,他们重复着自己的请求,但结果却始终如一。最后,他们想到,如果能够说服德圣西蒙公爵是帮助他们,兴许他们能达成目标,因为摄政王对圣西蒙公爵是发自肺腑的欣赏与尊敬。圣西蒙公爵,一个彻头彻尾的贵族,当听到一个贵族刺客将会与一个贩夫走卒一样,公然行刑于闹市时,也与他们一样被震惊了。于是,公爵告诫摄政王,与一个如此庞大、富裕、显赫的家族为敌,实在是不明智。而且,他还说,德阿拉姆博格家族在德国势力庞大。德国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受车裂之刑,家族的任何人都不得出任政府公职,直到那一代全部过世,子孙才不受牵累。因此,他建议将车裂改为砍头,因为在整个欧洲看来砍头远不如车裂那么臭名昭著。摄政王被这番说辞说动了,在他几乎要同意公爵的建议时,劳插手进来,他似乎对这个年轻谋杀犯的命运特别关注。他说服摄政王坚持先前的决定:让法律行使它的权力。
德霍恩的亲戚无计可施,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德罗贝克蒙莫朗西王子也别无他法,想尽办法进入到囚犯坐在的地牢,给了他一杯毒药,让他自尽以保全家族颜面。德霍恩伯爵偏了偏头,拒绝这么喝下毒药。在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之后,蒙莫朗西也完全丧失了耐心,他起身就走,边走还边愤怒地说:“死去吧!如你所愿,你这个贱种!只配死在同样卑劣的行刑手手上。”
德霍恩自己也一再向摄政王请求被砍头,而非绞刑;但是劳对摄政王的影响,无人匹敌,除了摄政王的老师、世人皆识的杜波伊神父之外。劳坚持认为,屈从于德霍恩家族的私利有失公平。摄政王起先也持同样的观点,在德霍恩与米勒的罪行被审判六日之内,两人在格雷夫广场被车裂。而另一名刺客拉斯唐,则依旧逍遥法外。
巴黎民众对这次迅捷而又严厉的执法交口称赞。甚至德坎康布瓦,他们叫他“劳”,也加入其中,支持摄政王铁面无私,对贵族并未法外开恩。然而,抢劫与谋杀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当富有的投机者被抢劫时,并没有人同情。公众道德的集体下滑,以前就已经是触目惊心了,现在更是变本加厉,迅速扩散到中产阶级。以前中产阶级还能保持相对的纯净,介于上层社会公开的贪婪与下层平民隐藏的罪恶之间。对赌博的狂热,迅速蔓延整个社会,在它面前,一切公共道德与几乎所有个人美德都分崩离析、不堪一击。
一段时间以来,只要公众的信心持续,就是给交易不会跌落的一支强心剂,是有益的。在巴黎,这个正反馈尤其明显。人们从全国各个角落蜂拥而至首都,不仅来这里攫取财富,也是来这里挥霍财富的。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王的母亲,计算了这段时间的人口增长,从世界各地奔涌而来的人口就达到了305000。管家不得不在阁楼、厨房,甚至马厩里增设床铺,为房客提供住宿。镇上塞满了马车与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即使是在主干道上,他们也不得不放慢速度,以免惊吓行人、发生事故。
整个国家的织布机一直嗡嗡作响,不停地供应着罕见的蕾丝、蚕丝、宽幅布与天鹅绒。这些物品的价格涨了四倍,给纺织业带来了巨额利润,粮食供应也是如此。面包、肉、蔬菜以前所未有的价格出售,工人的工资也几乎同倍增长。先前手工艺者每天只能挣到15个苏,现在则可以挣到60个苏。新房到处在建,城市往四面八方扩张。海市蜃楼般的繁荣弥漫着整个国家,人人都为这般景象头晕目眩、不能自已,却没有一个人看到地平线那朵预示着暴风雨瞬息而至的乌云。
劳自己,这个挥舞着法力无边的魔杖的魔术师,当然也与公众一样,分享着当下的繁荣。他的妻子、女儿是那些顶级权贵频献殷勤的对象,贵族王孙的继承人也纷纷登门拜访,以期能结秦晋之好。他在法国不同地方卖了两处金碧辉煌的不动产,同时还与德萨利公爵家族商议,购买罗斯尼侯爵的领地。他的宗教信仰成了发展中的桎梏,摄政王许诺,如果劳公开信仰天主教,就会让他成为财政审计总理。劳,其实并不比任何其他的专业赌徒有着更多的真正信仰,所以他自然乐意接受、满口应允。尔后,在一大群投机者的面前,德坦森神父接受了劳的皈依。翌日,他被任命为圣罗奇教区教堂的名誉理事,借此机会,他也捐献了高达50万里弗的礼物。劳的慈善一向大手笔,但并不都像这次这般一掷干金。他私下也捐赠了大量金额,任何他有所耳闻的真正贫困,他都会倾囊相助。
到这时,他俨然已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了。奥尔良公爵对他的远见卓识深信不疑,对他的计划的成功,也是充满信心。所以,常就每个重大事情向他咨询。劳也绝不因为自己的财富而过度膨胀,作出不当举止,他依然是以前那个简单、亲和、明智的人,与当初身处逆境时,毫无二致。他对女士的殷勤,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那是他的天性使然。他是如此友善、绅士,值得尊敬,甚至没有任何情人会因为他对其他女士的殷勤而觉得不愉快。
如果偶尔他表现出桀骜不驯,那也是针对那些卑躬屈膝、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以至于令人生厌的贵族。劳常常以此为乐,他想看看那些贵族为了一点儿好处对他的奴颜媚骨能够持续多久。但如果恰巧他自己祖国的人来巴黎拜访时,他则会完全相反,相当礼貌,并极其关照。当伊斯雷伯爵、阿齐巴德坎贝尔也就是后来的阿基乐公爵到旺多姆广场造访他时,不得不穿过那些被贵族们围得水泄不通的接待室。这些人都等在那里,期望一睹伟大金融家的风采,也期望能够把他们的名字列在新申购名单中。而劳则静静地坐在书房中,给他父亲留下来的位于劳里斯顿的庄园园丁写一封信,信的内容居然是关于如何种卷心菜!伯爵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与劳玩了一会纸牌。走的时候,已经完全被劳的怡然自得、出色品位与良好教养所深深折服。
在那些借由这段时间内公众的轻信而获得巨额财富从而得以弥补他们损失的财产的贵族中,不能不提到德波旁公爵、德吉什公爵、德拉佛斯公爵、德邵尼斯公爵,以及德安丹公爵,还有德艾斯特瑞斯元帅、德罗汉王子、德波伊科斯王子与德里昂王子。德波旁公爵,路易十四的儿子,母亲是孟德斯潘夫人。他在密西西比股票投机中相当幸运,他用投机来的巨额利润修复了在尚蒂利的皇宫,其风格异常华丽绚烂。他还对养马情有独钟,修建了一排排的马厩,在整个欧洲声名远播。他从英格兰进口了150匹良种赛马以改善法国马的血统。他还在皮卡迪购买了一大片乡村,拥有了瓦兹省与索姆省之间几乎所有有价值的土地。
当财富如此迅速被聚敛,毫无疑问,劳本应该被这些善变的人歌功颂德。的确,没有哪一位君主向他这么被顶礼膜拜过。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小诗与文学作品都不遗余力地对他大加赞美。照他们所说,劳就是法国的救世主、法兰西的守护神,他所有的话都充满智慧,他看起来是如此迷人,他的每一次举动都是如此深谋远虑。无论何时他外出,马车后面都会跟着成群结队的人们,以至于摄政王送给他一队骑兵,为他永久护驾,在他,前面开路。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