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曾经在一个学校念书,劳燕分飞后竟都在北京落了脚。有一天,他们突然做出一个“疯狂”决定:重走中国红军长征之路!抱着对中国革命的景仰,他们一路风餐露宿,几度冲破身体与意志的极限,成为除共产国际的李德之外走过长征路全程的外国人。384天里,他们游走在历史典籍以外的空白地带,寻找与那段历史发生过关联的无名百姓。他们找到了最初想要的答案,还在历史的真相以外懂得弥足珍贵的人的意志。本书以李爱德、马普安的日记为主体,真实记录了两人不寻常的“新长征”之旅,值得一看。
代序 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赌注
采访摘录,曾少东,北京,2001年11月12日 现在,很少有人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人们只关心钱。再谈艰苦奋斗还有人会在意吗?谁还愿意听艰苦奋斗的事?你们也不会听我说的。即使你们问我这些关于艰苦奋斗的事,事实上也根本听不进去。
70年代还在英格兰上中学时,我们只知道一件有关中国的事情∶如果那些穿清一色蓝制服的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跳起来再落地,大海会掀起巨浪,会把我们这些住在西方的人统统淹没。如果老师那时问我们长征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认为那是一种寿命超长的电池。
当然老师从未问过我们长征的事情,因为那时我们从来不谈论中国。中国也从未出现在学校的考试中或者电视上,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去关注中国的事情。当我们1987年在大学里相识时,对拥有世界1/4人口的中国可以说一无所知。
在柯彻斯特的大学里,我们住邻居。柯彻斯特是英格兰东南部一座死气沉沉、充满暴力的军事基地。那时,爱德特别擅长板球和斯诺克台球,马普安则一心扑在足球上,连桌式足球 都很拿手。我们彼此很不服气,互相嘲笑对方,还一直和对方较劲儿。我们喋喋不休地争论另类摇滚、政治还有足球。我们还开始阅读严肃报纸,有时会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关共产主义,或有关中国那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我们看到图片中的中国人不再穿清一色的蓝衣服。
“长征”这个词对于我们也不再陌生,因为报纸上常会出现诸如“中国迈向繁荣的新长征”这样的标题。但我们对长征的起因依然无从知晓。因为学校里课程所涉及的内容仅限于欧洲和美洲。马普安对于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是个关于“中国学”的“无知硕士”。十年以后,爱德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对“长征”背后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也仍是一头雾水,尽管“长征 ”这个词他已经听过无数遍了。
离开柯彻斯特后,我们就各奔东西。马普安到了美国,在新泽西州成为报纸特写稿件的编辑;爱德转到了英国北方一座友好一点儿的城市,他在那里的一所大学里呆了九年,学习法语和俄语,然后留校任教并最终获得后苏联政治历史的博士学位。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一天,马普安在美国一本记者业内杂志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可以提供在中国工作一年的机会,为了解闷儿他投了简历应聘。一份录取信函很快发到他的手里,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而此时他意识到自己平淡的生活正需要一些全新的经历,于是他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给爱德打了电话,这位惺惺相惜的朋友也正期待着一种变化。在一个大学里呆了九年,他的生活日趋平淡,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一次次到苏联和俄罗斯(1992年苏联解体)的学习旅行更让他心情沮丧,因为在那里,他目睹了朋友和同事们的生活由于经济崩溃而变得一塌糊涂。于是一接到马普安的电话他便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他觉得他已经对俄罗斯的情况太了解了;或许那些他不曾了解的地方才是他真正需要的。他情绪低落,需要新的灵感。
马普安1997年第一次来到了北京。那时在西单地区,长安街两侧还是人群熙攘的胡同和四合院。天安门广场西不过几公里的地方,窄小的街道两侧种满了树,两旁挤满了人丁兴旺的四合院。四年后,这一片历史地区已经消失了。我们两人费力地在狂风中穿过“西单文化广场”,走过六条车道的马路,经过宏伟的购物中心和中国银行总部这样高大的水泥“怪物”。我们正在寻找一些历史的片断———一定要赶在西单所剩无几的历史景观消失之前。
一座有两层小楼的四合院挡住了房地产开发商咆哮的推土机。地方有关部门已经答应可以满足房子主人提出的所有条件,可他就是铁了心,不打算搬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普通老百姓肯定早就搬走了,而这个人显然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以及一种独特的态度。
曾少东将军刚刚出院,但思维依然敏捷,笑声高亢而富有感染力。他非常好客,“喝茶,吃水果。”他一个劲儿地让我们。
这位老将军穿着朴素的、军服样式的橄榄绿制服。他的屋子装修十分简单,桌子的玻璃板下压着他和妻子以及和其他老同志的合照。他的领导告诫他不要跟我们这两个外国人说话。但是83岁的曾少东却对他的领导说,他想跟外国人说话就说。
“我1934年5月参加的红军,”曾少东回忆说,“我很年轻,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件好事。由于太年轻我没有提升的可能,所以我一直活到现在。就算我只是一个连长,我可能也早死了。许多连长都牺牲在战场上。因为他们总是冲在前面保护其他人。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 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重要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并逐步占领那里。与共产党有牵连的人一旦被捕就会被处死。共产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86000名红军战士不得不在1934年10月16日背井离乡,离开江西的家开始长征。
“我的妈妈 在于都河等我回来。”曾少东说,“许多人家都在那里等待他们的亲人。我妈妈给了我两个银元和一袋盐。两个战士一直在旁边等着我,他们怕我当逃兵,一个劲儿地催我走。他们说:‘快走,要不我们就赶不上大部队了。’” 一年后,曾少东到了中国大西北的避难所,只有几千人 活着到了那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在战场上被杀戮,被活活饿死;他看到有人从山崖上跌下来,有人掉进河里;看着同志们被沼泽一点点吞噬,被野蛮部落的人杀害,误食不明植物和污水而中毒,或者因为体力耗尽而慢慢地死去。
“吃香蕉。”曾将军说。66年前他曾饥不择食,甚至在先头部队战友们的粪便中寻找未 消化的粮食来填饱肚子。
“当我们穿过草地的时候,很多战士都牺牲了。那些死去的战士被后边跟上的战士掩埋起来。有些人病得太重了,只能停下来等死。” 爱德问:“你只是一个孩子。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随身带了一些银元,但过草地时我把它们全扔到水里了。它们太沉了,况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根本没有什么好买的。
一些年纪大的士兵又把它们捡起来。我问,‘你要这有什么用?你可能走不出草地了,我大概还行。’出了草地以后,身无分文的我没有办法买粮食,就去找那些老兵想要回我的银元。他们问,‘你怎么又想要钱了?’我回答,‘我太饿了。’于是他们就把钱还给我。那时我们互相照顾。” 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掌握了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他告诉幸存者们,他们走了“25000里”。这样的成就将会鼓舞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他们的事业,推翻腐败的旧制度。他们是英雄之师。
我们的朋友李明霞是我们当天的翻译,她问这位老英雄最后一个问题: “这两个外国人想重走长征路,你认为他们能成功吗?” “不可能。”曾少东将军说,“太难了,他们不可能走完长征。” 2000年5月,重走长征路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头脑中。那时我们正在贵州黎平县旅游,偶然听说红军曾在1934年经过这里。这个地区没有平原,山上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成梯田,只是在山顶处有几棵孤零零的矮树 ———因为那里的土壤太贫瘠了,空间又十分有限。这样的风景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的壮举。农业仍然保持着工业革命前的状态,人们使用水牛和木犁在田间耕作。
我们想象着65年前红军战士在这里艰苦跋涉的情景,他们一边要在迷宫般的地形中寻找出路,一边还要在整个途中与敌人奋战。我们不知道这里经历了多少变化,我们意识到,如果那些长征的旧路还在,那些路以及路上发生的事情可能会给人们很多启示———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还有它的现在。
虽然重走长征路的想法只是一时兴起,但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根本无法摆脱。让我们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普通导游书籍都没有介绍过这些长征路线。这曾经是一条贯穿许多城镇、乡村和无人地带的史诗般壮丽的路径。这条路沿途的人和地点共同缔造了新中国成立的神话。那些曾经见证过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不久于人世,因此我们想尽快见到像曾将军这样的长征见证人。但是在北京,谁也不愿意和陌生的“老外”多说话。如果我们是认真的,就只能去做一件事:蹬上远足靴,沿着这条史诗般的路线,寻找它最原始的故事。
我们要重走这条路,必须靠我们的双腿。在贵州的旅游让我们知道,长征途中很多路都无法通汽车。我们不想坐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毫无意义地走马观花。仅仅从汽车的窗口向外看,不可能真正了解长征。
红军都遵守三大纪律: 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二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 我们也为新长征制定了自己的三大纪律: 第一条:不坐车 第二条: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坐车,事后必须回到坐车起始点继续步行前进。
第三条:不必两次走同一条路线。
还有第四条,也叫X纪律,我们希望它永远不要被实施。
X纪律:在别无选择时可以坐车,比如医疗救护、遇到警察或其他中国官方代表的阻拦时。
谈这些想法和理想时很有趣,但说服人们支持我们却不那么有趣。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经常进行这样的对话: “我们想重走长征路。” 对面的人扬起眉毛。
“我们全程都要步行。” 他们皱起了眉头。
“要一年的时间。从没有外国人这样做过。” 最后他们问:“你们有什么经验吗?” “哦,没有。” “你们已经找到赞助商了吗?” “哦,没有。” 沉默。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疯了?” 我们对这样的反应毫不介意。我们的信心仅仅来自一小群信任我们的朋友。我们也经常在庞国良和他的女友万欣家里寻求安慰,他们对我们非常支持。
庞国良是澳籍新加坡人,这个中年人把一门心思都铺在万欣和他们的两只叫“Happy”和“Lucky”的美洲哈叭狗身上。他是一个整天将各种职业的术语挂在嘴边的人,非常自信。遇到挫折时他总用自己的信念作支撑。他爱引用《约伯记(Book of Job)》上的句子,传达的最主要的意思是:不论上帝用怎样严苛的方式考验约伯,“他从来不诅咒上帝”。
2002年春天,通过我们的朋友Les Charlton的引见,我们结识了庞国良。
“这可不是小事,”他说,“你们必须要有全面的规划,需要专业的推销和包装。你们要拥有自己的品牌,伙计们。这就好比时尚品牌,要让人们觉得关注新长征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庞国良对于时尚也很有一套。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当时庞国良组织了一场时装表演,支持中国的首都申奥。但是他主要的筹钱方式 好像是在为“著名的体育艺术家”Charles Billich(比利奇)做代理。比利奇是一个被流放的克罗地亚人,后来加入澳大利亚国籍,他在全世界兜售自己的作品,赚了几百万。庞国良的家里到处都是比利奇的油画、素描、雕刻品,甚至还有根据比利奇的设计制成的衣服和手袋。
比利奇的中国作品主题是秦始皇兵马俑,他画的兵马俑都转化成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形象,这让他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名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2002 年夏天,当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10月16日的启程时,庞国良在西安的兵马俑博物馆举办了比利奇个人绘画作品展览。开幕式上当然少不了时装表演。
我们当时就确信他是一个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人。
一天,在庞国良的家里,他正为我们制定全面的新长征方案,万欣在一旁给我们包饺子。我们为庞国良的豪言壮语激动不已,也为那“200万美元 ”的天文数字目瞪口呆。遇到庞国良之前,我们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为我们掏钱的,因此我们必须用最少的预算来完成新长征。
贾霁,这个活泼的24岁北京女孩全面负责我们的组织工作,她是一个全能的人,从导游到营销助理无所不能。马普安和她曾经同在北京一家名为“ 塞翁”的媒体研究公司工作,他们在公司打乒乓球时成为朋友。那时贾霁一直不承认自己的乒乓球技是全办公室最差的。当贾霁认识爱德之后,马普安出主意把她挖来参与新长征。如果我们要冒生命危险来实现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们就需要一个高效率、忠实并且值得信赖的人来帮助我们。贾霁具备我们所期望的所有条件,甚至还要优秀。尤其重要的是,她还喜欢我们的猫。事无巨细她都要操持,既要照顾爱德的两只猫“小毛儿”、“李鬼”和马普安的猫“虎子”,还要在全中国跑来跑去,为我们提供补给,帮我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
庞国良察觉到,我们这样的准备太不切实际了。“对于这样的事情,你们不能指望一个远在北京的小姑娘。你们需要一个团队,伙计们。我们要出去考察路线,可能还需要直升飞机的帮助。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应该清楚这一点。” 但是在我们做这些事之前,庞国良又说,还有一件事必须解决:我们需要官方支持和商业赞助。
“在中国,没有官方的支持,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他说,“我们要让人们对此有信心,向人们保证你们能够完成这件事。” 开始做吧,庞国良,我们说。开始吧。
2002年8月15日,李明霞拨通了爱德的手机。
“你认识澳大利亚使馆的人吗?”她问,“庞先生被带走了!” 庞国良和查尔斯·比利奇卷入与他们以前的合作者的纠纷之中,他们说这个中国女人卷了钱跑了。这个女人在法庭上作的辩护却最终占了上风,庞国良非但没有拿回他的钱,还必须付给那个女人更多的钱。他说他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折衷的方法,但法院立即叫人把他带走。
庞国良失踪了。法院也拒绝透露他的下落。
我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想找到庞国良,然后我们又坐下来安慰万欣。十天后万欣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庞国良的一个刚被释放的狱友打来的,他说庞国良让万欣别担心也别做任何事情,他很快就会被放出来的。
马普安是个悲观的人。“现在让我们想想自己的处境。还有两个月我们就要出发了。
我们还没有钱,没有官方的支持,而我们将来的合作伙伴现在又被关进了监狱。” 爱德则比较乐观,他安慰马普安:“别那么泄气,他马上就出来了。还有一个消息,‘Gear Guy’刚打来电话,他下个周末有空。” 马普安的脸色更难看了。
杨肖,就是那个被我们称为Gear Guy(装备狂)的人,是我们最早在北京认识的朋友。他生于兰州,11岁之前一直住在青海。他的父亲也在那里工作,是一位工程师。儿时,他就在青海的大草原上纵马驰骋。他对户外运动的热爱从未改变过。
杨肖是我们认识的最有能力的人。他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天份,不论在野外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呆多长时间,他总是给人一种闲庭信步的感觉,看起来总是衣着光鲜,好像从户外装备销售手册上走出来的模特一样。他曾在全中国人迹罕至的地方徒步旅行,以协助外国游客徒步旅行为生,多数情况下活动在北京北部的长城地区。
和杨肖合作的是一个英国人,叫William Lindesay(威廉·林塞),他是第一个走完长城全程的外国人。走完长城后,威廉·林塞就建立了一个名为“国际长城之友”的组织,其宗旨是推动对这个伟大的古代奇迹的研究和保护。很巧,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也曾重走了几段长征路线。
是威廉·林塞首先给杨肖起了“Gear Guy”这个绰号,他以这个名字给当地的户外运动杂志撰写专栏文章。Gear Guy测试最新的户外装备,并向中国的远足者介绍适合他们的装备。一开始杨肖并不太适应这个称谓,但我们都这么用英文叫他,他也就慢慢适应了。
如果24小时的中央暖气系统、有线电视和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星巴克突然从生活中消失,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我们必须向Gear Guy求助。
他也认为我们有些自不量力。他太了解我们了,因此当马普安说“我讨厌远足”时,他知道马普安是认真的。但同时他也认为我们的新长征计划很不错,这是一个疯狂却让人兴奋的主意。
“我在上学时,课本上也有关于长征的内容,我也曾梦想去看看那些地方,”他说,“但我从没想过去重走长征路,如果有时间,我肯定跟你们一起去。” 马普安的右脚踝在2002年4月的一场足球赛中骨折了。我们因此只能进行两次远足训练(这就是贾霁对媒体所说的“一系列严酷的训练”)。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杨肖带我们到北京周边最高的两座山峰进行训练。
一座是河北省的小五台山,位于北京以北车程6小时的地方,有2700米高。
另一座是北京以西车程3小时、2100米高的东灵山。他告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装备,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装备。
杨肖给我们讲了他在偏远地区旅游的经验。他还记得许多在学校里学的革命诗篇,甚至还在篝火旁教了我们一句有关长征的打油诗:“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 他还向我们转达他的具有开拓精神的朋友威廉·林塞给我们的建议。
“威廉说你们一定要全心投入你们的计划。如果遇到警察 ,一定要镇静,想办法避开正面冲突,不要大惊小怪。你们肯定想取得100%的成功,但这么大的项目,成功80%也很了不起了。如果你们能成功90%,那就太棒了。
” 此时的杨肖既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很久以后,他甚至还成为了我们的救世主。
小五台山之行是我们那时所经历过的最艰巨的考验。回来后我们浑身都湿透了,非常痛苦。马普安问杨肖我们的表现如何。杨肖用外交辞令回避了这个问题:“与长征相比,这只能算是小菜一碟。”两天后我们的朋友Kath Naday找到爱德的家里,这个英国女人在中国给外国游客做导游。此前她已经找过马普安,要求看看她的帐篷———我们惟一一件别人资助的装备—— —经过我们的野外训练后成了什么样子。
“马普安一直在说你们的周末有如何的糟糕,”她说,“他说你们都湿透了,还说他恨透了远足和大山。像他这样怎么能受得了长征呢?” “别替他担心,”爱德说,“他就是说说而已。” 庞国良8月26日出狱回家了。对于这段遭遇,他却十分乐观,这也是他的典型性格。那里面还有一些别的外国人,而只有他会说中文,于是他很快便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庞国良说一切还好。
“我当过兵,伙计们,”他说,“我可以在壕沟里睡觉。” 庞国良又全身心地为我们的事情操劳起来。他有一个记录着各种阶层人的电话本,他给电话本里所有相关的人都打了电话。我们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开会,就要和感兴趣的人会面,就会得到“合作”的承诺。“合作”真是一个充满魔力的中国商业词汇。通常,“让我们合作吧”意味着“你做所有的工作,承担所有风险,而且最好还能掏腰包”等等。
有一个政府出版社想要给我们全程录像然后提供给电视台,爱德给李明霞看了出版社给我们的合同。
“这简直就是另一部《南京条约》。”她说。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把香港割让给了英国人。
我们本来以为我们的计划很好推销。但真到关键时刻,我们得到的仅仅是鼓励的话语,其它的话就是“这太危险了”。
“我们怎么保证你们的安全呢?”这种借口我们已经听了无数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感谢庞国良,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好机会。
李彬办公室里挂的邓小平书法作品是我们见过的最大的一幅,有6英尺长,2英尺高,几乎和李彬的办公桌一样大,但它与房顶之间还有很充裕的空间。这该不会是中国最大的办公室了吧?李彬坐在桌子前,整个身体向后靠,翘着二郎腿,右手夹着香烟好像夹着一支铅笔,小拇指很优雅地翘着。
“你们是……?”他问庞国良。庞国良立刻像上了发条,开始滔滔不绝地念他的生意经,他说我们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强调了自己为北京申奥成功所做的努力,还有他和政府的良好关系。
李彬冲他的秘书挥了挥香烟说:“给市长打个电话。” 李彬是中国之友研究协会的领导。中国之友是庞国良为我们找到的赞助者。他告诉我们他们就等着在合同上签字了,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市长不在。李彬轻轻地理着头顶上几缕从鬓角梳上来的头发,然后转向爱德和马普安,问:“你们知道怎么爬雪山吗?” 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那么答案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一点也不知道” ,这次会晤的开端对我们十分不利。来这里之前,我们可没做好接受询问的准备。我们想的是由庞国良来谈一切事情,我们两个就在一旁微笑,达成协议后再优雅地握手。但是李彬似乎另有想法。他接下来给我们恶补了长征的 “知识”,告诉我们一路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李彬终于讲完了,他最后叮嘱了一句:“也许你们应该再考虑一下。” 李彬的下属把我们送出来,他们很尴尬,因为签字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我不知道我是否听明白刚才发生什么了。”我们离开大楼时马普安说,“ 他好像根本看不起咱们,简直是浪费时间。” 中国之友是我们获得官方支持的最后机会,也是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
我们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会晤,全部无果而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如此沮丧过。
爱德有点气愤了:“那个人为什么还要请我们来?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 庞国良还是一如既往地富有哲理。
“司空见惯了,”他说,“没有长征精神。” 庞国良又有了新的主意,他建议我们推迟一年走长征,这样一来他可以制定全新的计划。在我们离开北京出发的那天,一位参与我们计划的好友恳求我们不要上火车。她说:“你们会遇到大麻烦的。” 我们似乎一无所有,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又从英国的银行以高额利息借了钱。我们不怕负债,不担心没有官方支持的问题。我们真正担心的是2500 0里征途的路线要穿过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我们担心自己的普通话太差,朋友们一再告诉我们,农民的方言根本听不懂。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在一天走过30公里的路,还要背着30公斤重的背包。而在我们的地图上,本应印着长征路线的地方却都是空白。这对两个男人、一个女孩还有三只猫来说,确实是非常值得担忧的。
我们坐火车到江西省的省会南昌,然后坐汽车到瑞金。从1931年到1934 年红军开始长征前,瑞金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贾霁的宣传使得江西最大的报纸《江南都市报》为我们提供了一辆吉普,带着我们转了很多地方。他们甚至在车身上喷上了“新长征”的标志,记者徐宏和摄影师刘正全程陪同。警方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但是我们保证不会触犯法律并一路上都住在安全、可靠的旅店中,这才让他们感到满意。
我们知道“安全”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国人也表现得很紧张,对外国人总是过分地关照。讨论徒步进入偏僻农村的计划时,即使是我们最亲近的中国朋友也会焦急地问:“你们难道不害怕吗?” 怕什么? 此时往往会出现一段尴尬的停顿,然后他们说:“可能会有劫匪吧。” 这些人脑子中总是隐隐感到中国的农村到处充满……嗯……险恶,他们觉得这对两个“疯狂的外国人”来说十分不安全。我们却不在意,尤其是当我们听说,那年夏天,在马普安家的楼外,一位妇女几乎被刺死之后,我们就更不把他们的话放在心里。我们在中国农村的经验表明,中国农村对外国人来说还是安全的,至少比城市安全。江西警方要求我们不要露营。我们担心他们会拿走我们的帐篷。如果不填写包括申请者身份、去过哪里以及将要去哪里等问题的登记表,中国警方是不会允许你露营的。而马普安也向所有人保证,绑在他背包上的那个2公斤重的帐篷只在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
马普安说:“同志们,安全第一!” 瑞金是红色中国的首都,那时候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包括江西省南部的几个县。虽然瑞金现在仍旧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县城,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政府一直都在拨款美化它的环境。中央广场周围满是新建的洁净的小楼,普遍有五到六层那么高。
入夜,广场的东侧挤满了小吃摊,商贩们搭起临时桌椅,并在摊子三面扯起红色帆布。各种食物就摆在台面上,吃饭的人可以选择烧烤或炒菜。一个当地的乞丐在小吃摊后面一座座垃圾堆间流连忘返。他穿了一件肮脏不堪的蓝白色校服上衣,那一定是一个中学生丢弃的。如果没穿这件衣服,这个乞丐的造型倒很像《荒岛余生》中的汤姆·汉克斯。
大多数人认为瑞金是长征的起始点。但我们到那儿只是为了参观革命景观,我们新长征的起点在瑞金西南40英里的小县城于都。瑞金人对我们把出发点选在那里非常不满。从外事局的领导到江西苏维埃政府博物馆的导游对我们的无知都相当不屑,并且一再坚持我们应该从他们的城市出发。很多红军战士确实是从瑞金开始长征的。另外,在中国人眼中更为重要的是,红军的主要领导从瑞金出发;而西方人所看重的是,普通的红军战士从于都出发。这才是我们去于都的决定性因素。1934年10月的上半月,原来分散在苏区各地的红军士兵都集结到于都河的北岸,从10月16日到20日,他们用四天的时间渡过了于都河 。因此,我们认为于都才是最符合逻辑的起始点。
于都人民应该很欣慰吧。
“当然了,”当地外事局的钟翠连说,“于都当然是长征开始的地方。
打个比方,如果你出去度假,你该说你是从哪儿出发的呢?你当然说是从北京机场,肯定不能说从家里。” 瑞金和于都没什么差别,唯一的不同是后者的旅馆肯定安全多了,因为它的对面就是公安局的大楼。我们到那儿时一位女警官还从三楼的窗户向我们招手。这真是一个好兆头。
李明霞也来了,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支由五位强悍女性组成的欢送队伍———李明霞、万欣、贾霁、马普安善解人意的女朋友焦蓓,以及爱德以前的同事白玉———她们从北京一直陪我们到这儿,还决定至少陪我们走一天长征路。
李明霞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地图还有厚厚的历史书籍,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新长征的第二天我们该往哪里走。明霞在丽华饭店爱德的床上铺开地图,不看还好,越看越着急,就是在最详细的地图上,也没有标记我们要去的地名和路线。
“你们应该走这条路。”她一边说一边指着于都南30英里的最大的一片空白区域两侧的两个城镇,“看,我们知道他们有些人穿过了盘古山,接着是祈禄山,因此路一定就在附近 。” “此外,”她说,“你们肯定不想沿大路走,那太无聊了。” 日记选摘,爱德,于都,2002年10月15日 ……我尽量不去想几天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看起来,那些历史上的地名并不曾出现在任何现代地图上。
未知性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许是好事,这样就可以不去考虑长征的全局。
在地图上那些空白的地方,究竟有没有路呢? 一座方尖石碑矗立在于都河畔,这是红军横渡于都河的八个下水点之一。中国人的说法是,“长征第一渡”很明显会选择在距离城市中央1公里的地方,因为毛主席1934年10月18日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但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人物。长征的最初阶段有三个人不能不提。
理论上讲,27岁的博古是下达最后命令的人。他那时是共产党的书记,曾在莫斯科呆了四年,是共产国际辅佐他掌管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共产国际通常执行斯大林的指示,以维护苏维埃共产党的利益。第二个人是36岁的周恩来,红军的政委。
第三个人,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34岁的德国人李德。他于1932年被苏联军队情报机关送到满洲里,紧接着转移到上海,代表共产国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68年以来,直到我们站在于都河北岸,李德是惟一一位走过长征的外国人。
在“长征第一渡”这里,河水水流徐缓,大约有70米宽。距岸边约50米的河面上,几条挖泥船在石头堆中忙碌着,引擎轰鸣。别处的水面都很平静。我们10月16日到达那里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太阳。来欢送我们的人包括一群当地的干部、当地电视台的摄像师、报纸的摄影记者刘正,还有几个好奇的早起的人。
我们的朋友在第一渡纪念碑下扯起一块红色条幅,上面用中英文写着“ 长征2002从这里开始”。他们都在条幅上签了名。白玉还写道:“Waiting 4 you guys 2 my place for Joels fucking food SOON.(我们等你们两个快回来尝尝Joel的手艺。)” Joel是白玉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很快回来?就算我们按时完成计划,我们也要等一年零四天才能尝到Joel为我们准备的饭。
日记选摘,马普安,利村,2002年10月16日 ……你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眼前一条6000英里的路。静下心来体味一会儿,你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想它。别往回看,也别往前看。什么都别看。
在于都这样一个平凡的小县城中,平凡的人们开始了平凡生活中又一个平凡的日子。在一刹那你会羡慕他们,因为这个不平凡的想法———重走长征路———这一刻突然显得有点儿荒唐起来。
现在只能想那些眼前的事情。你必须迈开步伐,走出去,从地图上的这一点,历史的这一瞬间,走到另外一点,另外一瞬间。你不要停下来思忖这个奇异事件的意义,否则你会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拖垮。把所有深邃的情感留给以后抒发吧,或者还可以写进书中? 这应该算是比较有意义的对话吧,至少我还记得它: “咱们出发吧。” 我说。
“好吧。”爱德回答。
在你面临重大转变的时刻千万不要期望过高,这非常重要。似乎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要发生,这一个时间,这一个地方将因此而不同。
经过16个月的计划和梦想,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里,会不会出现一个独一无二的、令人难忘的预示?它会告诉我们:我们的选择完全正确!这个预示好像在说:“伙计们,你们己经走上正轨!不要再担忧了。” 也许回想起来,的确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河边的小路邻着一所小学,学生们三五成群地从我们面前经过,不经意间见证了我们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有些站住了冲我们喊“hello”,有些则只是好奇地盯着我们这一班人马。一个害羞的学生对正向马普安走过来的刘正耳语了几句。
“你知道那个孩子说什么了吗?”刘正问。
“说什么了?” “他说,如果他以前努力学习英语的话,现在就可以跟你说话了。” 我们跨过“长征第一桥”,在这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看起来我们的前景并不比68年前的红军更乐观。
我们几乎不敢想象前面的路会是怎样:雪山的坚冰和高山病,有毒的沼泽,草地无人区,强盗,野兽还有25000里。这些只是历史典籍中的精彩章节。我们不知道,在这些精彩章节之外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马普安那时已经得了慢性病。我们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可以去长征沿途的所有地方。我们更没有听说过“非典”。
2002年10月16日,我们投下了生命中最大的赌注。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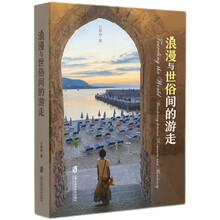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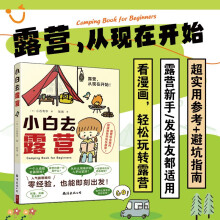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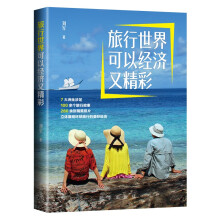
不知道是姜忠经过加工的翻译,还是原著就是如此,通篇都是用一种不带情绪、客观的有些过的感觉来叙事,甚至连马普安的愤怒都是那么的平实,没有外国人对中国,尤其是对落后地区的瞧不起,也没有那些对中国的刻意吹捧,是非常难得的。对两个英国勇士(我希望称他们为勇士)的尊敬之情不多言表,仅就书中的几个小花絮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是,书中多次提到的垃圾问题。我也是户外活动的爱好者,每次活动似乎都可以见到乱仍的垃圾,开始的时候非常的不满意,还经常捡起来,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甚至偶尔自己也扔过!我想大部分中国人对于乱扔垃圾,尤其是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扔似乎都已经慢慢习惯。可是两位新长征人又一次的提出了这个多次提出过的问题,还说这种垃圾随处可见的现象非常象英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也就是说是二战后的三十多年后,想想我们改革开放也是接近三十年了,经济飞速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物质文明的发展可以是跨越式的,可是整体的国民素质,尤其是一些长期习惯和文化的影响是可以跨越的吗?
二是,新长征途中老百姓的“看老外”现象。看老外的现象以及包含善意或者戏谑的“哈罗”从新长征的开始到结束一直伴随着李爱德和马普安,甚至让他们烦躁,这种感觉是可以想象的。可是,从各个地方的老百姓来看,又是如此的应该,毕竟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老外,加上又是步行走长征路的老外,再加上喜欢围观和看热闹的习惯,这就很正常了!边远的这些地区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也需要让外面的世界了解他们,两位英国人的重走长征路就是一种方式,希望尽快的能够有更多的,更好的方式来把这些落后地区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
又发感慨了,就写这么点吧。
全球化是越来越严重了。本来你以为对于那些老外来讲,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儿,他们开始将其当作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来看待。不可避免,误会和冲突随之产生了。
《两个人的长征》最值得佩服的就是马普安和爱德两个人的直率。他们毫不忌讳地把一路上因沟通不畅和习惯不同而和当地人产生地小矛盾和小冲突认认真真地摆在了纸面上。这些因误会而产生的故事有的时候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如果你很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不同的文明之间总会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一定要看看这本书。看看小矛盾是为什么产生的,你甚至能明白那些大问题,比如八国联军侵华,到底是为什么?
另外,遗憾,马普安没有执笔,大部分文字来自爱德。马普安是自由作家,从后记能看出他文笔更好。不过爱德能去写,功劳还是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