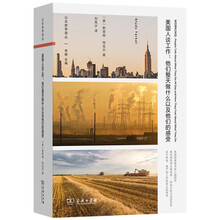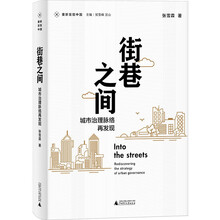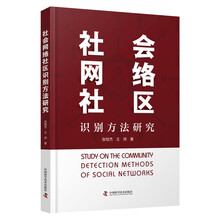从我自己的研究纲领的见解中,也无意中漏出了这类结论性的方法论和纲领性的题外话。不过,过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我可以肯定地说,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在他们的专著《实验室生活》中、诺尔一塞蒂纳在她的《制造知识》中,都独立地对在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进行了详细的人类文化学研究。在这两个事例中,这些研究都集中在科学研究和科学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的知识建构上。以后又有了一些不同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选择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在最初的观察和理论的取向方面是多种多样的。
即使实验室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的主题没有重新出现在我的著述中,科学论文作为一种变化着的惯例形式这一主题,也的确出现了。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指出:
……有关科学家会冷静、有条不紊并且准确无误地接近他们所报告的结果这种形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左右着科学论文写作的那些规则。我们知道,这种规则要求这些论文是经过很多删改的著作,要求在最终形成对任何事物的报道时删除一切复杂的事件和行为,而只把它们认识的实质内容保留下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