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锡华,中国安徽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1982年至1985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师从赵仲邑、潘允中教授学习古代汉语,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5年至1998年就读于四川大学,师从赵振铎教授专攻汉语史,1998年获博士学位。1985年起先后任教于中国、美国和加拿大高校,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和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000年移居加拿大。2001年应中国四川师范大学之聘,回国工作。主要专著有:《中国古代标签发展史》、《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史记〉单音词研究》、《尔雅研究》、《校堪学》。另于《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辞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汉学研究通讯》等刊物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六十余篇。1993年起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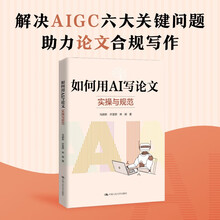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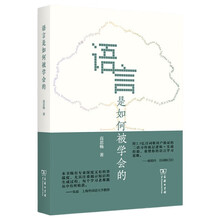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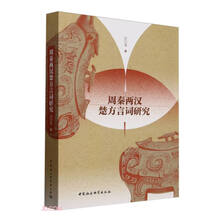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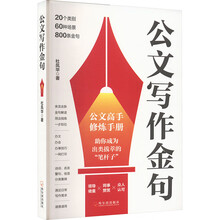
校勘之事,始於二刘,郑、章诸贤《校雠略》与《通义》之作遂言及校勘,余嘉锡先生因谓“目录、版本、校雠(即校勘)三者一家之学”;然揆之王氏《经义述闻》,俞氏《平议》,孙氏《札迻》,则训诂亦与校勘相表襄。余少从钱子泉、顾惕生、柳翼谋诸师获闾此义。虽才质驽下,老而无成,然知读古书,精通章句,犹得校勘之益。憶昔讲宋词,用某君《宋词选》,至于湖之“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十里秋江,江神留我看斜阳,吹起鳞鳞细浪”,诸生有以“明月”、“斜阳”矛盾为请者,余使检此书所本,盖出《六十家词》;又使检双照喽景宋《于湖词》,则“明月”作“秋色”,“秋江”作“湖光”。此生欣然曰:“先生屡言版本、校勘,今乃知确为学中要紧之事,而为教师者尤不可不知也。”
又忆60年代初,学校领导布置自订“红专规划”。有60老翁夜叩吾门,询之,则曰:“青年师生但云读某史、某集足矣!吾辈岂能复云读杜集、韩集乎?”余戏曰:“但於‘读’上加一‘校’字便可。”其人大喜曰:“得之矣。”盖著一“校”字,便由阅读而进入研究。由上两例可见:校勘为文史教学、研究中必不可少之知识与技能,即谓为治学之门,宜无不可。
虽然,欲通校勘,谈何容易!一要知方法,二要明类例,三要通积佐证。观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淮南》校例,王引之《经义述闻》之“讹字”条,俞樾至杨树达“古书疑义”中有关校勘诸例,皆就致讹之由反复示例,孙德廉、陈垣诸老言之尤详。类例既明,方法斯出,洵足以启人神思。苟能知此,则疑所当疑,正其可正,虽“己亥”误为“三豕”,亦不至望文误释,更不至以“锡”作药引矣。然仅诵义例,空言方法,亦未足以解决问题。盖对校必罗众本,而古本之存者不多,可资以为据者,多为他书。汇录徵引之异文,他校、理校则有赖於旁证者尤多。试观前人校勘之妙,每在曲证旁通,究其根源,皆由博览。不特《释文》《治要》及类书、古注所引,必须取资;而“读书记”、“藏书志”、“金石录”与诸家“校勘记”、“札记”中材料,亦为校书者所必用。否则,名为实学,实亦空谈而已。
300年来,实学莫盛於吾皖。戴君东原之“博徵於文,约守其例”,衣被海内,遂成皖学。其校算书、水经,亦为世重。然而旁搜善本,专事校勘如顾千里、卢召弓所为者则皖中尚少其人。故世谓版本、目录、校勘之学,皖不如吴。近世吴检斋、胡朴安诸先生颇有意焉,然亦未能专也。管君锡华盛年美才,雅志笃学,又从潘允中、趟仲邑、李新魁诸先生研究数载,得其薪传,用以探刘、班之微言,契郑、章之遐想,博览顾、卢、王、段之书,而会其妙用。由是提要鈎玄,细其义例,则庶几俞曲园、孙益庵之遣徽,有以补朴安之所未备,其所以裨益於教学与研究者岂鲜浅哉?余早从师友,略闻津梁;苦於形役,未能深往。今年近七十,旧学益荒,乃於病院之中,得见高才崛起,其为欣悦,岂可胜言!用是忘其荒陋,缀言简端,既以见校勘为治学之必需,复以见类例与博徵之关系,益以见通论得失,指陈方法者为不可少之书,至於君立意之美、编纂之勤、为学之善,读者当自得之,不待余之多言也。
1986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