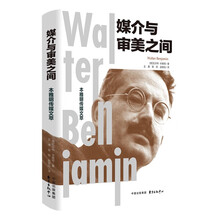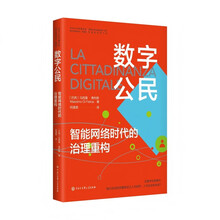第一章大众传媒的宪政地位<br> 民意是我们政府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是维护这一权利。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br> ——托马斯·杰弗逊<br> 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正式生效,这一法律条款奠定了新闻自由的宪政地位。200多年来,美国的政治家、学者和公民都把它看作是美国民主的重要保证和政治象征,新闻自由因此被认为是民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神圣不可侵犯。在政治家、学者和公民们看来,新闻自由一定程度上是民主的同义语,对新闻自由的破坏就是对人权的侵犯,对民主原则的破坏,对民主制度的破坏。但是,美国的第一修正案由宪法条文变成现实的政治准则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第一修正案正式生效的时候,美国的有色人种和大多数妇女还不能享受自由表达权,新闻自由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展,第一修正案只不过是为后来的新闻自由奠定了宪法基础。如果希望对美国的新闻自由作深入地了解,新闻自由所赖以成立的理论根据就必须予以说明。<br> 另外,新闻自由权利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还包含具体的内容,这些具体的权利究竟是什么?在这一部分,我们还将分析,什么是美国式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对于民主而言意味着什么?<br> 一、新闻自由的哲学维度<br> 民主社会中关于新闻自由一般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言论自由、批评现实世界的自由,媒体活动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Hutchins Commission)认同了新闻自由这两个方面的特质。委员会在当年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新闻自由意味着免于干预和自由行事的权利。媒体必须能够免于外部强制力的干涉,必须能够成为一个独立部门和调查机构,自由地传递不同的思想和观点①。新闻自由的这两个方面的特质与传统自由主义者关于传媒的作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哈钦斯委员会比起传统自由主义者更进了一步。它认为,传媒不仅应该享有上述自由权利,而且它们还要①对社会负责,必须为民众的利益尽心尽职;②为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提供表达的机会,并且为公开辩论创造机会。哈钦斯委员会关于新闻自由的定义,实际上涵盖了两种自由主义理念:一种是洛克式的,另一种是卢梭式的。<br> 自由的理论和学术思潮,是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一根主线,也是西方民主国家赖以立国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其核心思想仍然没有改变。<br>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是古典自由主义阐述“免于干预的自由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他们那里,人的权利是天赋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剥夺,权利高于一切,政府的权力不过是人民转让的,是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而让渡给他们信任的人和机构执掌,因此,当政府滥用权力的时候,人民有权收回自己让渡出去的权利,推翻腐败的政府,重新选举新的政府。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是社会的中心,政府不过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工具。<br> 卢梭关于自由和民主的解释显然有别于洛克等人。他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就指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了摆脱这种“枷锁式的自由”,人们有权打碎自己身上的桎梏,来恢复自己的自由。这种“打碎”有一个前提,即人们必须订立契约。契约的原则是,每个人必须将自己的权利全部让渡出来,委托给“集体”行使。在卢梭看来,当人们将权利全部转让给集体的时候,每个人作为集体的一员,又可以获得他所放弃的同样的权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卢梭的契约论可以简化为以下的内容: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这样的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为了使社会契约不致成为一纸空文,卢梭又规定:任何人必须服从公意,拒不服从者,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这等于迫使他自由。没有这一条件,社会契约便是荒谬的、暴政的,并会遭到最严重的滥用。<br> 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开始研究洛克和卢梭哲学之间的区别。1958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两种自由概念》,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概念。在伯林看来,所谓积极自由是指:“甚么东西或甚么人有权控制或干预,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而消极自由是指:“在甚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允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①简而言之,积极自由是指“去做……的目的”,而消极自由是指“免于他人干涉而强制的自由”。从政治自由史的角度来看,伯林的两种自由并不是什么创造,他只不过是对自由的谱系进行了富有思辨的梳理而已。实际上,他的两种自由分别对应着自由的两大派系和主要代表人物。积极自由对应着卢梭的政治哲学,而消极自由则对应着洛克的政治哲学。<br> 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不仅保护个人权利免遭其他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侵害,而且国家也应该保持不干涉个人自由。按照埃德加·弗里德伊伯格(Edgar Friendenberg)解释:这是因为,国家必须执行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功能,“保护”属于积极功能,而“自律”则属于消极功能②。<br> 受伯林的启发,冈塞·内林(Gunther Nenning)将两种自由观应用到传播学领域,提出了“积极新闻自由”和“消极新闻自由”。内林认为,积极新闻自由和消极新闻自由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两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传统的消极自由观主张,在新闻自由方面,国家不应该做什么,而积极自由观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应该做什么来促进新闻自由的发展。“过去的新闻自由定义已经过时了,而新的界定在不断出现,它们认为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有国家的身影,国家不应该是消极的,而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培养公民的自由习惯。”③<br> 内林将新闻自由区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来对应西方民主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似乎大多能为学者们接受,但是,他的关于两种新闻自由的观点却从未为美国传播理论家所认同,这可能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有关④。在美国社会,人们普遍认为,新闻自由对于民主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⑤媒介之所以在民主体制中发挥了有效的维护作用,这是因为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基础之上的。在美国人看来,所谓新闻自由,是一种消极的防范措施,用以保障新闻媒介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性。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