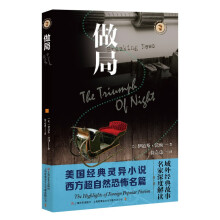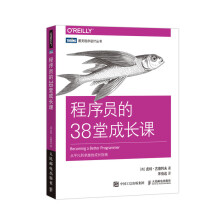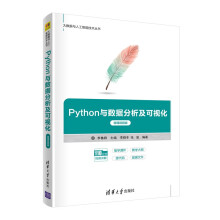书摘<br> 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他肯定“人欲”是合乎情理的,但满足这种欲望的方式要合乎“道”,反对为富不仁,反对用非正当的方法摆脱贫贱去获取富贵。这里,孔子的思想包含有人生处世,为求改善境遇,若方式不可取,须安贫乐道的意思,这也是对君子美德的要求之一。其它方面,孔子还有很多论述。<br> 而小人则适得其反,不必赘言。<br> 兰、莲,花草而已,又如何与君子攀附在一块了呢?古人却言之凿凿,颇具说服力。<br> 《家语》曰:“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文子》曰:“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止。”南朝周弘让《山兰赋》曰:“爰有奇特之草,产于空崖之地,挺自然之高介,岂众情之服媚,……入坦道而销声,屏山幽而静异。”原来,在兰花的习性上,人们看到的是它卓尔独立,坚忍不拔,身怀异香,却甘于寂寞,而这些正是君子难能可贵的品德。北宋周敦颐《爱莲说》曰:“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原来也是同样发现了莲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君子之风。<br> 誉之为君子者,又不止莲与兰。与兰并列者,梅兰竹菊,人称花中四君子,这梅、竹、菊,同样受到古人的推崇。梅花不畏严寒,开于初春,菊花迎着西风,于深秋吐蕊发荣,在人们看来,它们因不与百卉并盛衰,不求闻达于俗世,铁骨霜姿,高洁隽逸,倘非君子又是什么呢?<br> 花木的秉性与我们自身人格内涵的上述比照,并不是今天我们可以不加思索、轻描淡写地以为,那只是古人凭一些似是而非的形似而玩弄表面文章,只是心血来潮地自作多情,将自己的感受任性妄为地强嵌入所偶然面对的景观事物的身上。<br> 我们的先哲很早就认为,自然界的一切是由充斥宇宙的元气构成的,元气聚则成物,散则成气。元气可以凝结为大山巨川,可以凝结为风云雨露,也可以凝结为草木虫鱼。即使是人类,也是由元气构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既然万事万物都是秉受元气生成的,那么事物的种类不同,属性各异,都不过是元气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人无疑是万物之灵,“最为天下贵也”但并非唯人有灵性,在古人看来,动物、植物甚至无生命的自然之物也有灵性,人的灵性等级最高而已。我们在前一节中提到“钟灵毓秀”,就是古人一种饶有哲理的说法。花木尽管与人类乃至动物相比,灵性的等级虽然较低,却与我们人类同属于有生命的实体。所谓同气相求,同性相吸,花木的灵性又为何不能与人类的灵性息息交流、沟通呢?<br> 由于抱着这种深厚的信念,古人在对花木的观照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非同一般的情愫,其道理便不难明白了。既是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一面,那么所谓的在对象的身上发现自我,就不应再简单地认定那只是类同于镜子的反射,自我的影子在对象的身上仅仅是虚幻的投射之物,对象所担待的人性内涵不过是我们慷慨地赐予罢了。然而对象并非一无所有,我们在对象身上发现的也并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影子。正是同质同构,才能身与物化,物我为一,人在对象中发现的是自己的真身,而对象也即在这过程中得到了消解——说得通俗些,就是花木不再是原本的花木概念了——由此,人通过对象的消解又重新返回到自身,充实了自我,获得了对自身更完美的认识。正是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运动,人在花木的观赏中,最终陶冶了自己的性情。<br> 中国人的辩证法,曾为西方哲学的巨擘黑格尔所不屑。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是一位19世纪的辩证法大师,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许多经典的论点,却可以在我们古人的思维方式中找到印证。我们当然不会说他抄袭了我们先贤们的思想,而用“英雄所见略同”来解释,恐怕是比较恰当的。但因为正是他对中国哲学的无知,故在一些道听途说所拾得的皮毛里,他轻率地得出结论,不负责任地把中国哲学贬斥了一通。<br> 不谋而合的是,黑格尔关于主客体的辩证论述,他从第一部较成熟的著作《精神现象学》中便开始深刻地研究这一问题,直到他建立起一个庞大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为止。他多次表达着这样的观点:<br> 辩证的东西……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这是最重要的方面。<br> 既然两个对立面每一个都在自身那里包含着另一个,没有这一方也就不可能设想另一方,那末,其结果是:这些规定,单独看来都没有真理,唯有它们的统一才有真理。<br> 对象……是一种纯然否定的、自身扬弃的、向自我返回的内容,即是说,对象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或主体)这个形式时才有真理性。<br> 黑格尔的哲学立场不消说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他的辩证思想却熠熠生辉,恩格斯曾给予高度评价:“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br> 中国人在花木中看到了君子,看到了小人,这不仅仅是人性自我在对象身上的投影,因为,古人同时认为,花木本身是存在着质性高低之区别的。古代的辩证法是稚拙素朴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中国人是最早认识事物矛盾性的民族之一,著名的阴阳概念的提出,便是最好的证明。万事万物通过阴阳概念的诠释,就获得了特有的中国式的对世界矛盾性的认识。仔细阅读《易传·泰卦》彖言中这段话“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夕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不难明白,在古人那里,君子、小人与阴阳对应,同样可作为揭示事物矛盾性的工具。那么,在花木的世界中,君子小人之论,是否也存在这一哲理内涵呢?回答是肯定的。<br> 人与花木气类相投,生意相通,常常与花木相处,正可返璞归真,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人花相处,并不只是人对花木的护养施惠,表达爱意;花木对人亦有回报,对人亦有施惠。以现代科学的知识来看,我们都知道,植物在光合作用下,是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吐出氧气来的;而人恰恰相反,吸入肺中的是氧气,吐出来的则是二氧化碳。但是,当这一学说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却认为其理未出易学。《种树书》清代版本有署名渐西村人写于光绪丙申年(1896)的“叙”,里面就说,中国的易学是讲气的, “万物盗天地之气以生”,构成万物基础的元气孕育出草木来,而“元气毓草木”,又使“人得草木之滋以养”,人游于阴阳之气之“澹澹之中,淆天地之化”,这样,便是西人所说的草木得吸人之炭气(指二氧化碳),人得吸草木之生气(指氧气)而交相养,于是渐西村人的结论是: “泰西农家种植,医家摄生,为炭、养气之说,乃胚胎于此。”渐西村人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氧与二氧化碳的科学解释是建立在近代化学元素的发现以后,并依赖科学仪器的实验而证明的,中国古人的那类带有猜想推论的模糊说法实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中国古代的那类说法是出之于哲学的观点,哲学本来就不能取代具体的学科,解决具体的问题,它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力求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由于中国的哲学尤其是由易学阐发出来的哲学,特别强调世界的整体联系,讲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讲究气之升降飞扬,未尝止息,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讲究阴阳具于太虚絪缊气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气化流行,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生生不息。由此想来,人与植物,互相吐纳,各取所需,或为养气,或为炭气,其理的确已隐含在中国哲学的概念之中了。那么渐西村人之说似又并非全是虚妄之言,里面多少包含了真理。<br> 我们不应妄自菲薄。华夏民族的哲学有时就是那样显得非常早熟。当我们拨弄着我们祖先掩埋着的文明灰堆时,浑邃的智慧就像是磷遇空气那样,时不时会闪现出耀眼的光芒。<br> 人们把教育界称为“杏坛”,又把医学界称为“杏林”,皆出于古书上与杏花有关的传闻。杏坛,据说孔子聚众讲学之所。《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絃歌鼓琴。”《庄子》这里可能只是寓言,并非实指。后人因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真的为之筑坛,建亭,书碑,植杏。到了宋乾兴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石为坛,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以后历代相承。后来转移为凡是授徒讲学处,都可叫做杏坛。<br> 杏林,即三国时东吴的一个叫董奉的名医,为人治病素不收钱,只要求病人好了以后在地方上种杏树,病重者植五株,轻者植一株,作为回报。经过一些年,他治愈病人无数,得杏十余万株,蔚然成林。因他医术高明,功德无量,人称他为“董仙”,称当地杏林为“董仙杏林”。打那以后,世以“杏林春满”、 “誉满杏林”等等来作为称颂医家之美辞。<br> 明代园艺家王世懋认为:“杏花无奇,多种成林则佳”,是比较有道理的。在大型园林或风景区内,群植于山坡和水畔是较理想的方式。杏是抗旱耐寒的树种,它以黄河流域为分布中心,华北、西北、东北栽培尤盛。南方热带地区一般是见不到它的身影的。古代许多人不完全了解这一点,包括王世懋也是如此,所以当他在写《闽部疏》时,发觉福建没有杏花,感到非常惊奇:“闽地最饶花,独杏花绝产,亦一异也。”这可能同他是吴地人有关。农历二三月,杏花一树万蕊,与桃、李争芳斗艳,恰堪鼎足,它们共同渲染着欣欣向荣的春天,给人带来的是无限的融融春意。<br> ……插图<br>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