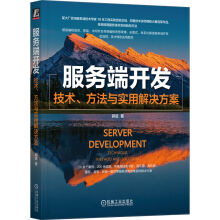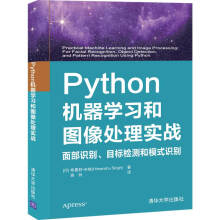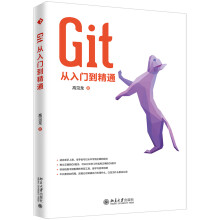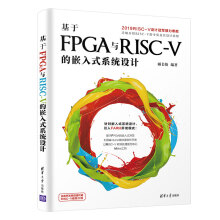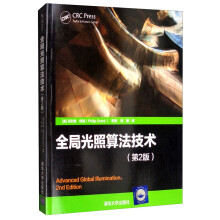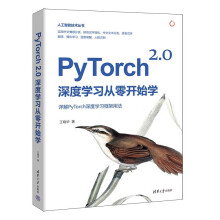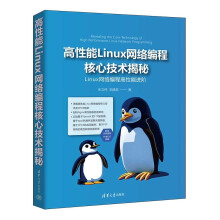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随着经济的货币化、金融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般认为,金融效率与经济发展是协调一致的。然而,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金融效率与经济发展严重背离的情况。一方面,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持续高增长;另一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金融效率低下。因此,经济高增长和金融“低”效率并存现实就成为理论上需要解释的悖论。<br> 《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效率:对转型期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金融“低”效率悖论的解释》将通过经济学研究和金融经济学研究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经济高增长背景下金融“低效率”如何形成及其实质;二是金融“低效率”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高增长;三是两者并存的合理性、冲突性以及发展趋势。<br> 《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效率:对转型期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金融“低”效率悖论的解释》始终以中国经济变迁为背景,以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发展金融理论、最新的金融与增长关系理论为依托,紧扣中国经济金融中的具体突出条件,重点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金融低效率之谜,最后以探讨改进中国金融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为落脚点。<br> 《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效率:对转型期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金融“低”效率悖论的解释》主要包括6章内容。第1章导论首先提出了《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效率:对转型期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金融“低”效率悖论的解释》研究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说明;然后介绍了《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效率:对转型期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金融“低”效率悖论的解释》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最后指出《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效率:对转型期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金融“低”效率悖论的解释》的主要创新之处和不足。<br> 第2章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增长中的金融效率研究进行综述。首先,对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他们的研究体现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发展金融理论、金融与增长关系理论之中。在经济增长因素理论中,帕加诺(1992)等将金融因素内化于经济增长模型做了很多开创性努力;发展金融理论重点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问题;金融与增长关系理论重点研究了两者相关性、因果性、作用机制等问题。其次,对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他们的研究沿两条路径进行:一是直接对有关中国金融效率的研究,主要研究了金融配置效率问题;二是对有关的金融与增长关系的研究,重点研究了中国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问题。最后,对国内外学者的上述研究做出评析,指出其研究贡献与研究不足。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对经济高增长与金融“低”效率并存问题给出系统、合理的解释。<br> 第3章提出了包含金融效率因素的经济增长分析新框架。首先对近年流行的包含金融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简单回顾和评析。结果发现,这些模型虽然已经区分了金融和非金融因素,但是对金融问题的研究没有从质和量(即金融效率)两个角度来分析,导致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金融总量扩张和金融效率改进间的不平衡性缺乏解释力。其次,本章明确提出了包含金融效率的经济增长分析新框架。该框架不仅包含了金融和非金融因素,而且明确提出金融因素要从总量和效率两个角度进行考察;进而概括了经济金融发展史上六种金融、金融效率与增长组合模式及条件。再次,本章还将分析新框架运用到转型经济中,提出了转型经济中的两个简易模型:第一,转型经济牺牲金融部门内在效率及金融配置效率获取宏观经济增长的模型。金融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需要严格的必要条件,即微观主体高效率。然而在转型经济中,微观主体的低效率特征决定了难以达到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而为了保证转型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刚性目标,中国选择了牺牲金融部门效率及金融初次配置效率。第二,金融漏损及“逆取顺守”增长效应与金融配置效率修正模型。转型经济时期,在生产和非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金融漏损,而这种金融漏损多数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最终进入生产过程,对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具有修正效应。<br> 第4章论述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动员效率与配置效率。首先,分析了我国经济高增长中的金融动员和金融转化高效率。转型时期,各种政治经济形势要求我国刚性的经济增长为宏观经济首要目标,为此在转型前期给予体制内企业大力资金支持非常重要。国家在财政支持无以为继的情形下,实施了强控制金融。强控制金融具有动员优势,连同低货币化水平等因素,成就了金融动员和金融转化的高效率,为体制内增长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其次,强控制金融内生了金融部门低效率和初次配置低效率。强控制金融下的金融体系由于具有商业性和政策性的双重目标,后者在转型初期是支配性的,因此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将动员和集中的金融资源主要配置给了效率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内生了金融部门低效率及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即西方意义上的金融低效率。此种金融低效率是符合国家战略的一种次优选择。再次,在我国转型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广泛存在着金融转移及其“顺守”,客观上对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有一定修正。一方面,我国转型经济生产过程中的金融转移被“直接顺守”。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改制中的金融转移和改制后的效益提升、体制外企业因获取体制内企业商业信用、投资资金而获得更好发展和体制外生产企业直接获得体制内金融支持而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我国转型经济非生产过程中的金融转移,多数最终“间接顺守”了。非生产性金融转移主要是转移到海外或转变为金融窖藏,窖藏的这部分金融转移一部分形成体制外直接投资,即“直接解封”了;另一部分进入民间金融及回到体制内金融,形成体制外其他投资主体生产性投资的重要源泉,即“间接解封”了。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扭曲的方式实现了转型期中国特色的二次配置效率。<br> 第5章论述我国转型时期金融效率与非金融要素的增长效应。首先,分析了金融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转型期中国金融配置效率包括金融初次配置效率及金融二次配置效率。金融的初次配置低效率支持了体制内企业产出的稳定增长,而二次配置效率则为体制外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br> 中国金融效率以富有特色的金融初次配置低效率和一定的二次配置效率共同支持了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其次,分析了与金融动员高效率相一致的金融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效应。我们分别从货币供给、金融资产及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及相关比率等来考察了我国金融总量扩张和经济增长情况对比,结果发现,我国金融总量的扩展与经济增长高度一致,反映了金融总量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再次,还分析了非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包括: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带来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劳动力转移、技术进步和引进外资等引起要素的变化带来的微观因素的变化、经济结构的改变等带来的中观因素的变化,它们都对我国经济增长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br> 第6章对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效率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改进金融效率的建议。首先,对前转型时期中国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问题做了总结。前转型时期我国选择了国家强控制金融支持增长的模式,该模式直接导致了我国富有特色的金融效率状况,即强控制金融具有动员优势,造就了较高的储蓄动员和转化效率,同时也内生了我国金融部门的低效率和初次配置效率低下,然而“逆取顺守”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初次配置低效率进行了修正。<br> 其次,指出前转型时期强金融控制与增长模式的合理边界及其不可持续性。<br> 随着转型进程的深入,强控制型金融的合理边界已经发生了变化,金融总量扩张约束增多,买方市场形成与“傻瓜投资”的增长效应终结,体制外经济贡献增强,国企格局发生较大变化,银行、证券市场市场化压力增大,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步入新阶段。原来的牺牲金融效率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和牺牲社会公平通过“逆取顺守”实现增长及配置效率修正的模式变得不可持续。<br> 最后,提出了后转型时期中国金融效率的目标、原则和措施。认为在后转型时期保证经济持续高增长与金融高效率相统一成为我国金融效率改进的总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遵循渐次放松国家强金融控制模式、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改革和发展金融的原则。具体举措包括:积极稳妥地推进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积极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尽快解决证券市场股权分割等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推进证券市场规范化、国际化;积极扶持民营金融及创业资本市场发展;充分运用金融业对外开放来促进国内金融效率的提高;完善财政税收体制;加强信用建设和规范政府行为等。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