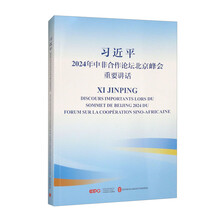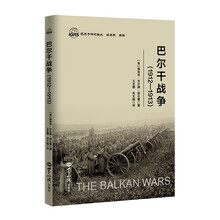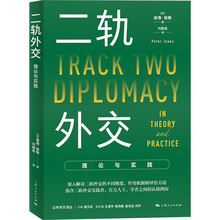书摘<br> 2000年5月,我突然反思:“怎么会在北京?怎么会为欧洲与中国谈判签订一个协议呢?”当职业生活演变为政治活动时,它会令你走上一些偶然和令人惊讶的道路,有时它还会将你带回到已离开了许久的地方,会带给你奇特的挑战,比方说,你会发现有一天你居然担任了以前自己曾严厉抨击过的要职。<br> 1984-1994年,我在欧洲委员会担任了10年雅克·德洛尔办公室的主任。在此期间,我几乎每天都会与欧洲委员会的委员们打交道。在里昂信贷银行工作了5年之后,1999年,由于法国诸位领导人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的提名,并经欧洲议会的投票选举,我也成为了欧洲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带着满腹的回忆,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布鲁塞尔。<br> 1994年的春天,我离开布鲁塞尔,此时的欧洲委员会在雅克·德洛尔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工作,尤其是开始义无反顾地建设无国界联盟。今天,这些已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当时,我们推出了许多加强合作与团结的新政策,并大致勾勒出欧元的面世之路。这是艰苦的10年,也是欧洲复兴的10年。在这10年中,我们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加上众多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努力,诸如弗朗索瓦·密特朗、赫尔穆特·科尔、费利佩·冈萨雷斯、让-吕克·德阿纳等,大大加快了西欧和东欧的历史进程。“布鲁塞尔”成为所有来欧洲国家或政府首脑的必经一站。<br> 我至今尚记得与戈尔巴乔夫、曼德拉、老布什、克林顿、瓦茨拉夫·哈维尔及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会面。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欧洲是建立一个更平衡的世界的希望,是建立更公正的国际关系的希望。欧洲委员会在铁幕出现倒塌的第一时刻,就能正确审时度势,在其领导人的推动下,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吸纳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成员的所有工作。尽管,作为10年的结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因巴尔干战争而变得四分五裂、犹豫不决的国际社会,以及一个软弱无力的欧洲。<br> 无尽的嘲笑<br> 在雅克·德洛尔身边工作了这些年后,在经历了25次欧洲议会及10次发达国家峰会(由于俄罗斯的加入,由G7变成了G8)后,我再次来到巴黎,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挽救里昂信贷银行——这家20世纪初全世界最大的银行!这个选择着实让一些朋友吃惊不小:为什么要离开一艘海军上将的先进船舶,跑到一艘已到处进水的货轮中去呢?更何况这艘货轮还处于由巴黎的讽刺和嘲笑所组成的海洋风暴的正中心!<br> 巴拉迪尔政府在解雇了让—伊夫·阿伯雷之后,任命让·佩尔勒瓦德为银行的负责人。此时,他向我发出了求救信号。我们的友谊建立于1982-1983年。当时他是皮埃尔·莫鲁瓦的办公室副主任,而我则担任当时的经济及金融部长雅克,德洛尔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我们都是“严厉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还包括菲利普·拉加耶特、埃尔韦·阿农、达尼埃尔·勒贝格、弗朗索瓦—格扎维埃·斯塔斯、伊莎贝尔·布约等。逆境考验了我们的友情与性格。一直到1983年3月,弗朗索瓦·密特朗采纳了皮埃尔,莫鲁瓦及雅克·德洛尔的意见,走上了我们认为是正确的道路,即欧洲的道路,并拒绝让法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1983年4月,在马提翁宫中正对花园的那间办公室里,我接替了调到苏伊士银行的让·佩尔勒瓦德的工作。他很清楚地告诉我,在里昂信贷银行的新冒险中,我们取胜的几率不超过50%,但金融危机也同样给了我们操作的空间。<br> 尽管这场战役是如此艰巨,如此紧张,如此不确定,我却一刻也未曾后悔过这个决定。当然,在布鲁塞尔,德洛尔领导的委员会内部,由《罗马条约》引起的矛盾也纷繁复杂,这种矛盾存在于诸多委员之间、委员与成员国之间、欧盟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而主席办公室主任的角色更让我屡屡招惹麻烦。“飞鱼”、“突击队”、“说废话的人”,这些不客气的绰号当时总是陪伴我出现在各类媒体报道中。然而政界远比金融界稳定,公务员与外交人员比银行职员受保护,干部更是如此,甚至享有某些特权。但它却锉平了一个人的锐气,使得各种危机也显得不那么尖锐。特别是当时有像雅克·德洛尔、弗朗索瓦·密特朗及赫尔穆特·科尔这样一群人的热情,当有困难出现时,它很少会带来危机。<br><br> 在粉尘与废气构成的灰蒙蒙的天空笼罩下,错落着一片用碎砖烂石堆起的房屋。我们称这里是“灰色之城”。就在2000年6月的一天,我们走遍了这里的大街小巷。路面凹凸不平,或是散碎的石子,或是印着深深车辙的泥泞小路。路边是一些简陋的建筑或是瓦隆铁的小木屋。垃圾遍地,禽舍猪圈随处可见。孩子们赖以玩耍的地方也不过就是几处杂草丛生的空地。在街的尽头,流淌着废水的阴沟也是疮痍满目破败不堪。年轻人凑在一起无所事事,老人趴在窗前打着手势大声吆喝着他们。<br> 但这一切就要改变,搬迁的消息带来了希望。推土机挖出一个个深深的壕沟,起重机一次又一次地将沉重的水泥构件和其他建材卸下来。亚历山大镇位于约翰内斯堡的郊区,是南非最早的种族隔离区之一,始建于20世纪初叶。当时那些黑人矿工由于贫穷和种族歧视被赶出城市来到这里。随着该地区金沙矿的开采,居民人数迅速增长。当时为解决单身工人的住宿而匆忙建起的宿舍,现在已挤满了一大家子人。在这个贫民窟里,生活着40万人,卫生条件极差。十几户人家合用一个水龙头,卫生间很少,而且极其简陋。从这个贫民窟的建立和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实行了种族隔离并充满了暴力。我们的汽车停在大学医院和健康中心的门前,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过后,我们进入该中心。<br> “我先领你们参观我们的妇产科。”卡特琳·穆沃拉兹——这位可敬而坚强的院长边说边领我们穿过了挤满人群的走廊。亚历山大镇,正如院长对我们讲的,是种族隔离的产物。这里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死伤。<br> 这所医院成为当时一个避难所。医院成为病人的救旱,做了大量的预防、教育和协助工作。而这里也是纳尔逊·曼德拉出狱后最先访问的地区之一,他此次访问的大幅照片被作为新时代新希望的标志印在医院的简介小册子上。<br> 当我们参观监护室时,院长女土带着一种充满自信的微笑向我们介绍这里的一切。她说:“这个医院几十年来一直在为满足巨大而日益增长的医护工作和控制各类传染病进行不懈的努力。这里是一个真正的细菌培养基地,各种流行病如脊髓灰质炎、天花、肺结核、艾滋病等在此肆虐流行。另外,在这个充满失业者和流浪汉的地方,暴力、抢劫、偷盗等犯罪行为经常发生。”<br> 穿过候诊室时,院长接着说:“我要告诉你们,这里1/3的妇女是艾滋病患者。如果不治疗,她们将会死去,但治疗费用太昂贵了!她们根本没能力支付……”<br> 我们走进一间长方形大厅,在白墙和不透明玻璃下,40来个妇女或是坐在黄塑料椅子上,或是坐在靠墙摆放的木凳上,静静地等待做产前检查。小孩子们或在地上玩耍,或爬上母亲的膝盖。当我们经过时,她们摆头或挥手向我们示意。我们也回以友好的问候,但很不自然。我们不想让她们发现我们眼神里流露出的忧虑和怜悯。<br> 我们观看了另几个科室,察看了门诊部、实验室和儿童病及职业病防治中心。他们无不向我们表示谢意,感谢我们提供的财政资助。所遗憾的是这次参观实在无法回避那些等待死亡妇女们的目光以及被传染儿童的诸多问题。这一切使我感到外界灰蒙蒙的雾霭更加浓重了。<br> 在这次访问中,我与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南非的代表格曼尔博士进行讨论。我告诉他,作为一名欧盟商务代表来南非考察公众健康可能让人感到很吃惊,但是,因为正和医药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进行谈判,所以我要亲自来了解这些大公司实施的价格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今后该由此吸取的教训。格曼尔博士对药价政策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对我说:“您可能已经看到了,在南非,我们有一些医疗基础设施和相应的初期诊治系统,也与医疗中心和媒体合作,一起进行防病治病宣传工作,如在亚历山大镇,我们和当地广播电台进行合作宣传。然而,其结果呢?如挥剑劈水!病毒仍在蔓延。人们并不重视预防措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没有后续的治疗手段。如果怀疑自己被感染了,被检查证实了也无法治疗,哪有什么必要去做检查呢?不进行检查,一旦在后期发现病情的时候,治疗也晚了!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医治措施。但这种病的医治却有赖于昂贵的药品,而医药公司拒绝销售基因药物,因为这类药的价格只是目前一般药物价格的1/15,我们可以发放这种药品,因为我们有发放药品的渠道。”<br> 我恳切地告诉格曼尔博土,欧盟已经着手重新审查它的政策策略,也会集中各方的力量面对这场噩运的挑战。分手时,他告诉我他完全知道我们在布鲁塞尔所做的努力,欧盟所做的一切他都很关注,但是,要快。<br><br> 禁止雇用童工,是国际劳工组织最早的主张之一,该组织第五号公约明确禁止企业雇用14岁以下的儿童,那时是1919年。此后这一禁令被扩展到各行各业。但是,1973年,国际劳工组织的173个成员国中只有一半多一点的国家批准了关于最小工作年龄的公约,这其中不包括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而统计表明,全球60%的童工在亚洲,约1.5亿。<br> 世界对童工视而不见,对镇压工会、强迫劳动和男女同工不同酬也充耳不闻。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如果工资很低,而父母又不能集体同资方谈判,孩子们就只能工作,只能在农场、矿场或非正式行业为他人出口赚汇。他们在印度编织地毯,在安第斯山制做瓦罐和土坯,然后搬到阳光下晾晒……他们一直为出口而工作……<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