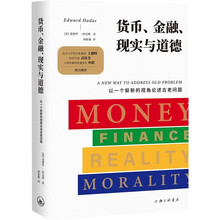但不知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有没有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与资格,所以,相应地,为各个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的声音都不
相伯仲,社会影响也都差不多,所以,各种声音都可以相互制衡。政府也可以兼听则明。而中国呢?中国是这样吗?“资本”与“权力”阶层有实力买得到经济学家为他们服务,但普通工人呢?普通农民呢?还有昨天街头的出租车司机呢?谁来为他们说话?当上千万下岗工人在为不知下一顿饭在哪里而发愁时,我们的经济学家却在说“计划经济下就业体制培养了千百万懒汉”,“要想提高效益还要再下岗一千六百万”;当普通人辛辛苦苦几十年干下来最后发现国家曾许诺过的“老有所养”不过是风雨中纸糊的房子时,我们的经济学家正忙于论证“福利社会的不
经济性”。这就是我们某些大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
稍稍说开一些去。这两年,不少经济学家鼓吹教育改革。其核心内容就一个:交钱上学!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启动教育消费,可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真正考虑我们国家的穷孩子如何上得起学。而如果贫穷家庭落后地区的穷孩子们都上不起学了,他们也曾经有过的赶上富裕家庭富裕地区的愿望将被完全相反的事实取代。更可怕的
是还不在于这些经济学家这样鼓吹,而在于我们一些政府官员也竟然信以为真了,并打算这样做。他们还振振有辞地说:“银行可以对穷孩子发放助学贷款!”而实际上,这一方面使本来应该完全是效率取向的银行不得不承担政府赋予的社会负担而无法做到彻底商业化;另一方面即使是穷孩子可以借款,也意味着出大学门的那天起,穷孩子已经背上了数万元的债务,又与富孩子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这里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即明星是如何产生的。我记得经济学家穆什·阿德勒作过这样的结论:“明星现象是在知识上进行节约的一种市场手段。”具体地说,人们进行任何一项
消费,是需求知识的。以听歌为例,我们是如何了解歌曲以及歌手的呢?为了节约知识的成本,我们大多只能是通过与那些听了更多音乐,更懂得音乐的人交谈,所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多数人相互通过交流接受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这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就成为流行歌曲以及歌星;而且更进一步,一旦当这些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进入多数人视野时,人们再在交流有关歌曲以及歌手的知识时,为了节约交流的成本,不得不对这少数歌曲以及少数歌手予以更深入的关注,少数歌曲以及歌手进一步被带入一种多元对话的格局之中,于是,这个过程反复下去,围绕这少数歌曲以及歌手,一种“知识谱系”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不断强化他们的明星地位,而后来的歌曲以及歌手要再进入明星行列,因为听歌者必须付出新的“学习成本”,而一般的听歌者不愿轻易付出这种新的“学习成本”,所以,后来者要成为明星,必定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这也是不少音乐经纪人抱怨“要包装一个新歌星,成本越来越高”的基本原因。
……
书摘1
选 择
一个多月前,我的朋友单庆老家一位乡长到北京,朋友请父母官的客,一定要我去作陪。不得已,我去了。一见面,郝位高姓乡长大声大气地说:“啊,你就是卢周来啊。单庆说你是搞经济的,还给我看了你那篇乡下姑姑来信。你也太厉害了吧。把我们乡村干部全都给否了。”我只有边向他点头哈腰,边解释说:“没那个意思。没那个意思。”
席间,这位高乡长再次向我发感慨:“小卢啊,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们乡村干部可不容易啊。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对。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还有龄事情,是村民们不晓理。”因为对于“不对”与“没有办法”的事我了解得比较多,所以我随口接了一句:“你说说村民们有什么不晓理的事吧。”
高姓乡长还真说了一件事,情况与央视《焦点访谈》某次播出的节目很类似。皖河边上有一片滩头地,分散在各农户手中。这几年因为年年都有或大或小的洪水,滩头地根本就没有什么收成。因此,农民也没有太在意这片地,有的农户例行性的春天播下种子,到秋天能收多少收多少,往往收下的粮食只够喂喂鸡;有的农户干脆撂荒了。后来,乡里将地全部收回,统一承包给外地过来的一个养河蟹的,并对农户进行了每亩地一百元的补偿。当时农民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种多少年也收不回一百元。但仅过了三年,河滩地出效益了,外地人开始赚钱了,农民们却红了眼。要求将已改造成池子的地收回。乡干部劝农民们说你们没有养蟹的技术,收回来也没用,农民们则说宁肯地荒掉也不能便宜了外地人。否则,要告到上面去。而承包者死活不同意,说合同期未满,如果乡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他要告到《焦点访谈》。乡里正为此事愁得不行。
其实,高乡长面临的这种两难选择,在经济学中还真研究过。这种两难选择可以抽象为这样一个选择过程:假设有一个方案,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是否通过。现在投票人是一百个人。
此方案通过以后,对一百个人中的九十九个人来说,每个人可以增加一美元的收入;而对于一百个人中的一个人来说,方案如果通过,则会造成其二百美元的损失。因为民主的原则是多数原则,所以,此方案一定会因为有九十九个人投赞成票而被通过。
但是,对于知识界人士,问题就来了:此方案通过后,给九十九个人每人增加了一美元的收入,社会总收入增加了九十九美元:而此方案通过后,因为给一个人损失了二百美元的损失,所以社会总收入因此损失了二百美元。两相抵,方案通过后,给这个社会不仅没有增加总收入,反倒使社会总收入减少了一百零一美元!而如果政府出于增加社会总收入的考虑,无视民主的原则,否决了此方案,那么,损失是九十九美元,增加二百美元,两相抵。社会总收入可增加一百零一美元。
因此。社会其实在此面临着一个选择是:你是遵守民主原则。还是追求效率原则?如果遵守民主原则,那么就以损失效率为代价;如果追求效率原则,那么就破坏了民主的原则。
高乡长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他照顾人数众多的农户的要求(民主的原则),那么,尽管农户可能因此受点小益,但承包人的损失更大;而如果他顶住农民们的要求,满足了承包人的愿望,那么,他显然又没有尊重民意。
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在经济学家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意见,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流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本身没有立场,只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从效率的角度,这个方案不应该被通过;一些同样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社会学者甚至在这里看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矛盾。他们说,这个例子形象地说明,民主有时候会造成多数人(九十九个人)对少数人(一个人)的压迫,所以,民主也不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当民主妨碍了自由的时候,民主应该为自由让路”,因此,这个方案也不应该被通过。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个例子说的还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民主的“一人一票”原则是体现了公平的原则。效率与公平不可兼得,所以,这种两难选择其实是无解的;或者说,通过民主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协调社会效用,要想有解,只有出现一个独裁的政府,能强行安排效用的优先秩序。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如果九十九个人每人增加一美元后增加的总体满足程度(即效用)超过二百美元给一个人增加的满足程度,那么,这个方案应该被通过,因为尽管社会总收入减少了,但用效用衡量的社会总福利还是增加了。
想到这蝗,我与高乡长说:“你可是真要为难了。你碰到的难题,也是我们经济学家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难题。”但高乡长显然不满意我的话,要我解释解释,我就按上面的思路给他解释了一通。显然,他听得云里雾里,有些不耐烦,最后对我说:“我就想要你自己的意见,不要管什么这个那个经济学家。”
这下轮到我为难了。因为我想,无论是收回还是不收回那片河滩地,其结果乡干部肯定考虑过,而且考虑得比我多,他们都不敢贸然决定,我一个刚了解了一些皮毛的局外人凭什么可
以做选择?
好在我的朋友单庆关键时刻插话补充了一个情况,他说他回家时了解过这个情况。其实乡亲们说只要每年再给他们补点钱,可以不要求收回地。但高乡长随即说到,当时说好了一次性
补偿,而且签了合同,再找承包人要钱,于法不通。 我不得不再详细地了解了合同情况。综合高乡长所说,还有以下事实:对农户一次性补偿每亩一百元是乡里与农户口头协商后经农户同意决定的;是乡里出的钱。而承包人只是与乡政府签了合同,每年按利润多少给乡里提成。乡里当然也不会乱用这笔钱,而是用这笔钱补了财政上的空缺。
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我心中有数了。从经济学上看,要满足农户与承包者双方的利益,只有一个“角解”——逼出来的惟一的办法——乡里从承包人上交的利润提成拿出一部分再补偿农户!我这么一说,高乡长不言不语了,喝了几口闷酒。我知道,这个办法他未必会采用,因为这涉及到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但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今天,单庆给我打电话,说高乡长解决了关于滩头地的问题。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继续由承包人承包,但承包人再给农户补偿点钱。据说承包人先不同意,说是法庭上见。高乡长劝他就别上法庭了,法庭也是讲民意,而且现在最讲民主了,肯定会听多数农民的意见;然后,高乡长与他算了一笔账:假设一百个人。方案不通过,其中九十九个每人损失一元钱,而另一个人因此赚两百元钱。如果按民主的原则,方案肯定要被通过,但那一个人吃亏大了;不按民主的原则,又不符合中央的精神。那么。惟一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我上面所谓的经济学上的“角解”)就是,与这九十九个人讲清楚,方案不要通过,那个因此得利两百元钱的人拿出其中九十九元,分给九十九个人每人一元,这样,九十九个人就不再坚持通过方案,而那个拿出小钱的人仍可以赚一百零一元,仍是吃小亏沾大便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