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中期,中国时尚风行整个大不列颠。在中国式装饰风格这一总标题下,“中国式风格”渗进花园设计、建筑及绘画等领域,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文学和道德哲学领域。在马嘎尔尼使团前20年,风行一时的中国式装饰风格达到高峰,其影口向直到19世纪早期仍可感到。马嘎尔尼本人就是通过这些“英国制造”的中国形象来认识中国的,但有时这些形象也会使他感到迷惑。
自16世纪起,有关中国的描述就开始渗人欧洲。描述者有耶稣会士、曾到过中国海岸的航海者和欧洲各国使团的成员。在这些描述中,浮现出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中国,一个由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充当官员、组成政府,并由仁慈的专制君主所领导的乌托邦。它财富充盈,农业发达,足可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正如法国重农主义者所说的,中国的长处与同时代欧洲社会的短处恰成对照(艾伦Allen,1937,1:182—183和阿普尔顿Apple-ton,1951:37—52)。
到18世纪中期,法国已经出现了十足的儒学热,中国圣贤成为一切中国古代智慧的代表。像魁奈(Quesnay)这样的道德哲学家对中国。的体制称赞不已,并敦促欧洲君主们仿效中国皇帝。在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看来也确实采纳了这些建议:有描绘他犁耕的图画,是模仿中国皇帝而来的(《欧洲与中国的皇帝》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 1985:304)。即使英格兰也未能免于受到对中国的赞扬性描述的影响。17世纪晚期,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爵士写了许多称赞儒学的著作,其他英国著者则将中国视力莫尔(More)的乌托邦的部分实现。这种情感到下个世纪依然盛行。在评论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为《绅土》杂志所写的小品文时,塞缪尔·约翰逊在笔下热情乐观地描述了儒学和中国(阿普尔顿Appleton,1951:42—51和范Fan,1945)。
随着中欧贸易的增长,中国的瓷器、漆器、家具、纺织品在英国自由流转,并激发工匠们设计新的样式。到18世纪50年代,威廉(William)和约翰·哈夫彭尼(John Halfpenny)的《中国式庙宇、凯旋门、花园坐椅、栅栏等的新设计》(1750—1752),查尔斯·奥韦尔(Charles Over)的《哥特式、中国式和现代派中的装饰建筑》 (1758)和保罗·德克尔(Paul Decker)的《中国式民用建筑与装饰》等等著作影响着建筑和花园设计。更进一步激起对中国式设计兴趣的是法国耶稣会士对圆明园的描述,它被译为英文,并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杂志中广泛流传。也许最有影响的当数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艺术设计著作。钱伯斯曾任东印度公司驻广东货载管理员,在《中国式建筑的设计》(1757,塞缪尔·约翰逊写了开头几段)、《论东方式花园》等书中,他大力倡导在更大型的建筑中运用中国式风格。
钱伯斯赞成中国式设计,但并不希望被划人“夸大中国优点的人”之列。他拒绝毫无保留地赞扬中国,这与英国艺术和道德哲学领域里日益增长的对中国影响力的抵制正相表里。攻击来自各个方面——愤怒的古典主义者捍卫希腊和罗马的“纯洁”,牧师和坚定忠诚的英国人赞美英国的价值和品位。对中国事物的指责——无论是以讽刺的口吻还是以敌对的方式——都有许多共同点。首先,批评者认为,被中国式风格吸引的都是暴发户和妇女。暴发户被认为是英国议院中政治腐败和权力贩卖的重要根源,而妇女则被认定缺乏美学鉴赏力。第二,一些人认为,中国式风格的形式因背离“自然与真理”而不符合艺术标准。虽然批评者在使用这些术语时所表达的含义大相径庭,但其核心观念则始终是简单、有序和对称。无论怎么看,中国式风格都没有这些核心观念。第三,一些批评者如威廉·怀特黑德(William White-head)认为,中国式风格根本不是中国的,而是欧洲设计家作品的拼凑(参见阿普尔顿,195l:103—119)。上述最后一种批评尤其有害,因为就美学而言,它意味着艺术被变成时尚,因而成为商品。
最后,对中国式风格的反对发展为对中国的整体批评。在《鉴赏家》、《绅士杂志》这样的期刊里,对中国模式的诋毁就如同下面几行文字中对中国画的攻击一样。这段文字出现在1755年的《世界》(The World)里:
绘画,就像建筑一样一直背叛事物的真理,不值得被称为典雅。不真实的光,不真实的影,不真实的透视法和比例,灰暗的色彩,没有层次,没有明物与暗物。总之,仅仅是形式的组合,没有内容,也没有意义,这就是中国画的实质。(引自阿普尔顿,1959:119)
失败的绘画,不真实的作品,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件事——中国人不能准确的再现自然界或社会生活的现实。
对中国艺术的态度的转变受到另一种现象的影响。整个18世纪,伴随着国民性的讨论,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它部分是通过新期刊传播开来。与希腊一罗马时代相比,它主要是一种世俗的修史方法,将民族视为主要分析对象。受已知的科学发展模式的影响,支配这种修史方法的叙述原则是质的进步这样一种观念。该观念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增长密切相关。一方面,进步是物质性的,它体现在市场商品的巨大增长上,体现在出现了足以代替人力的技术上,体现在从世界各地流人英国的财富上。但同时,进步也意味着另外的东西:它表明了在过去的基础上的快速发展,摆脱了教会、礼仪与典礼、迷信与魔幻、风俗与习惯等等的支配,有了飞跃。它还表明了一种转变:从前的世界,人们只了解了它的表象,而现在,正确的道德、美学和科学鉴赏力形成了彻底的男性也即理性的眼光。以此看待世界,则世界就是可以辨别、可以用语言予以描绘的。以此眼光观察世界,就会揭开从前被欺骗性外表所掩盖的秘密。在这种观念的转变中,中国的形象受到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对深受此类有关世界历史进步和现实的性质的观点影响的欧美知识分子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形象现在依然如此)。
马嘎尔尼认为,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可供参考的标准,无论一个地方的信仰,天性,经度或纬度或物产是什么,如果他必须对这个地方施加影响的话,他都能够驾驭有余。于是,他在谈判中就处于有利地位,不必耗费太多心力。他观察人微,却不再仅仅是个被动的接受者——他提出许多建议,并据理力争。这一切努力所围绕的焦点是觐见皇帝时他应遵守的礼仪。
8月15日,使团快到北京东郊通州码头时,觐见问题首次出现。徵瑞、王文雄、乔人杰来到马嘎尔尼的船上,向他说明各种各样合乎情理的安排和参加在热河举行的皇帝生日庆典的计划。他们介绍宫廷礼仪时的那种“精微,灵活和巧妙”,令马嘎尔尼不得不叹为观止。清廷官员注意到各国服饰不同,便说他们还是喜欢自己服装,因为它“宽松自由”,不会在给皇帝磕头时碍手碍脚。既然英国人的服装不甚方便(如膝扣和吊袜带),那么可以在见皇帝之前把这些服饰去掉。
马嘎尔尼不愿奉行汉人在皇帝面前的礼仪,他认定“皇帝更乐意接受我的鞠躬礼或屈膝礼,我向我自己的君主行的正是这种礼”。他的态度使官员们推测:也许英国礼仪与中国差不多,但是,在中国,礼仪形式是双膝下跪,三跪九叩。这项礼仪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被豁免。我告诉他们,我们的礼仪有所不同,尽管我愿意以最大的热忱去取悦中国皇帝,但我的首要职责是取悦于我的君主,如果他们确实非常反对我奉行英国礼仪的话,我一到北京,就会给他们进去我的书面答复。
那时徵瑞提出,马嘎尔尼的旅程既漫长又危险,他的君主可能非常盼望他的归去。马嘎尔尼答道,他必须等到见到皇帝,他必须完成他的君主交给他的使命。然后,他仿佛突然想到了“东方习俗和思想”,于是,他说,他的“目的在于向我的君主描绘皇帝的无上荣光和美德,帝国的权势与壮观、法律及道德组织的睿智,远播四方的赫赫威名”(《马嘎尔尼日记》,84—85)。这当然是阿谀奉承,但亦有它意。马嘎尔尼所奉上的阿谀之词,正是清皇帝希冀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听到的。
从8月21日到9月2日英国使团在北京为热河之行做准备。在这段时间里,围绕礼物产生了种种引入注目的问题。朝廷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了新的决定。在使团抵京的前一天,皇帝指示金简、伊龄阿和徵瑞,说既然礼物很快就可以放置到圆明园中,终于有机会见到礼物了。相应要做的头件事就是一件一件地看,并决定哪些留在北京,哪些运往热河。然后他又回忆起马嘎尔尼曾说过,天文仪器一旦装上就不能移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放置这些礼物就相当麻烦,尤其是准备用来放礼物的都是主要大殿(正殿),不便长期放置礼物。另一方面,既然对礼物的性质不甚了解,因此最重要的是要让宫廷里的能工巧匠们看着英国人拆箱和安装,以便在知情的基础上评价礼物。
评价礼物仅仅是朝廷面临的问题之一。皇帝想起马嘎尔尼宣称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装好天体仪,认为贡使此举旨在卖弄奇巧和聪明。贡使的傲慢使他与英王(英王看起来很真诚很恭顺)大有区别,贡使的炫耀也不可避免地误导了徵瑞。因此徵瑞要与金简和伊龄阿多多商量,确保钦天监的官员们能够从头至尾观察英国人处理礼物的方法,弘历认定对马嘎尔尼及礼物的评价应责有专属,方为妥善(《掌故丛编》,42b—43b)。
8月26日、28日,皇帝签发了两道上谕,有关英国礼物的放置与性质的问题暂放一边。弘历看了金简8月25日的奏折(《朱批奏折》,25.19),贡使被带到正大光明殿时的反应令皇帝
感到满意,金简报告说马嘎尔尼说那个地方足够展览礼物并且绰绰有余。弘历肯定马嘎尔尼的炫耀是出于无知(而不是出于傲慢),他得出结论说,事情再次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但关于礼物还有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皇帝认为徵瑞与马嘎尔尼的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皇帝忆起徵瑞有关马嘎尔尼描述礼物的报告,认为胆怯的徵瑞也许受到了英国贡使的威迫。在某种程度上,徵瑞的这些缺点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之前,徵瑞从未在广东海关任职,对欧洲人及其天文仪器知之甚少。换言之,马嘎尔尼之所以敢夸耀,部分原因正在于徵瑞的无知和胆怯。因为不熟悉英国人带来的礼物,所以他被马嘎尔尼的话吓倒了,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贡使的傲慢(《掌故丛编》,45b~46a)。一旦马嘎尔尼身临帝国大殿,他就会产生敬畏,就会变得本分,变得老实。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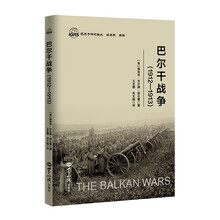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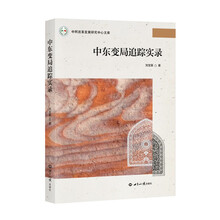

本书的题目源自一个在清廷记载里常常出现的习语。“怀柔远人”既是一种描述又是一种诫令。作为宇宙与尘世之间的枢纽,皇帝从道义上被赋予统治世界的责任。明智的君主应该对那些处在中心统治区以外的人们显示怜悯与仁慈,应该轸念那些长途跋涉来到他的宫廷的人们。这些观念是礼仪的核心,而清廷正是借礼仪来建立与其他强势统治者的关系。本书要研究的正是宾礼与帝国觐见,我所讨论的礼仪是清廷用以指导对外关系的习语。我关注的焦点是乔治·马嘎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率领的大英帝国使团,它于1793年到达乾隆皇帝的宫廷。
关于马嘎尔尼使团所受之接待,从前的学术界持有三种看法,本书正是对这些看法的回应。第一种是结构—功能学派的看法,这一学派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它的批判性的分析促进了对古典模式如“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和“朝贡体系”的再思考。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摒弃“朝贡体系”,那么,18世纪晚期以来的中西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
第二个问题部分也是由人类学的分析所激发,而与社会学的礼仪观有关。我确信,正是欧美世俗(非宗教的)学者对礼仪的特别的看法,才使中西冲突被构建为一种文化误解。我考虑的问题包括两部分:①形成这种阐释的文化观是什么?②倘若抛开文化因素,冲突会是什么样的?
第三个争议与我自己的态度有关。我不赞成中国中心主义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样的观念,尤其考虑到清朝的建立者是满人而非汉人。由此引向第三个问题: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看做生机勃勃的扩张性的西方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东方,而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和大英多民族帝国的相遇,那么,自马嘎尔尼使团之后的清英互动又该是什么样呢?这本书和我正在写的第二本书试图阐释这些问题。
本次研究中,我分别考察清与英对遣使事件的叙述,以便强调双方不同的实际操作模式与观念框架。在批判性地评介了其他有关清代外交关系的观点之后,第二章将提供一个对清帝国及其统治状况的全景式的考察,第五章还要谈到这个问题,并特别关注宾礼。第三章讨论18世纪大英帝国国内文化背景,展示在知识贵族中普遍流行的“外交、贸易及对中国的了解”。第四章重新检讨马嘎尔尼勋爵对觐见过程前前后后的叙述。第六章和第七章透过清的礼仪和统治权观念来审视清有关这次觐见的记载。第八章把双方的叙述列在一起,合而观之。第九章,在对这次清英相遇做出一些总结之后,回顾中西关系史中对使团的研讨。
这本书亦是由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一篇论文扩展而来。在撰写论文的日子里,我得到了诸多学术上的支持。在芝加哥大学的不同寻常的求学经历中,这些支持对我而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1980年到1985年,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们互为人师,这是一种近似玩笑和略带夸张的说法。在校园的咖啡馆里,每天都有非正式的讨论会,我总是定期参加。在参加者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罗杰·布拉德肖(Roger Bradshaw),杰夫·马尔蒂(Jeff Marti),拉斐尔·桑切斯(Rafael Sanchez),弗雷德·邱(Fred Chiu)和瑙基·萨凯[罗按,这是日本人,待核](Naoki Sakai),约翰·卡拉吉欧(John Calagione),丹·纽金特(Dan Nugent)和安娜·阿隆索(Ana Alonso)。他们有时参加讨沦会有时又去搞实地调查,但他们在场时,总是使我受益匪浅,那时就像现在一样,还有不少人只是偶尔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