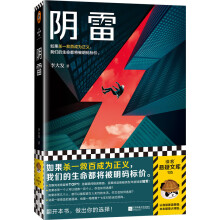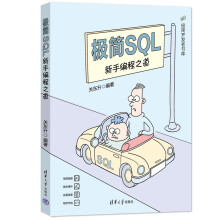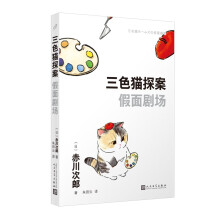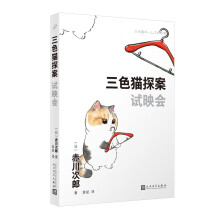尽管何如璋在朝鲜问题上与黄遵宪一起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但是,由于受琉球交涉一事的影响,李鸿章已对何氏产生了不良的印象,、认为他“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继续留在日本会影响对琉球之交涉,故而建议总理衙门将何如璋调离日本。于是,何如蹄离开东京,重返故都,又回到翰林院任职。
光绪几年(1883年)九月,何如璋以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办福建船政。次年当法国侵略军进攻马尾时,他以临阵仓皇出逃,被清廷革职,发往军台效力。期满之后,又为两广总督李翰章邀约,归广东主讲韩山书院。何氏一生真与李鸿章兄弟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期,我们又在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何如璋的两封亲笔密信。此信是何氏由日本归国后所写,其内容亦与李鸿章有关。
其一曰:“李爵相鸿章,由上海三次五百里陈奏越南事件,原折系皇太后存留宫中,除军机大臣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得以筹划商办外,其余臣工概不得与闻。漫云百余金,即数百金,亦无从得八底稿,厅难设法,有负委任,尚望原情格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土战备多,主和者少,至六部九卿科道等官,亦各有议论。如指定何人及如何立论,无从得知,不敢妄言。”
文后,驻北京的情报接受者又用红笔注明“右者系支那之某官,致渡部书记生的内报”。它由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直接寄送刘日本外务省。按照惯例,驻北京公使馆对此类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在呈交给它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时,只称“支那某官”、“某人”,而通常不明言情报提供者的姓名,即使对其亲朋好友,亦不能有任何泄露,
其二曰:“前日周炳麟来访何侍读,炳麟盖在越南数日前归京者也。侍读问彼访西贡、河内、东京等之事,其所答不甚分明,亦无奇闻可称。炳麟又问侍读曰:琉球之事如何?侍读曰:议论纷扰,总要打仗而决已。昨日又有人来问越南事。侍读曰:吾闻似归和议,左中堂不要起行,李中堂上书,书中所言,吾亦不得听之云云”。
此情报末尾,有红笔注明“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部书记生之内报也。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正是由于第二份情报的特殊文体,日本在北京的公使馆情报人员才特别注明系何如璋提供。
这两封密信紧密排列在一起。书写于“大清国日本公使馆”的信纸上,书写十分工整,字体完全相同,由于日本驻京公使馆已破例注明出自何如璋之手,且均注称之为“内报”,内报者,盖情报之谓也,所以,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此非常重视,几乎每个字都用假名注明读音,许多过目者都按惯例,在阅过后,于正文旁边签字或盖章。
这两份密信的收信人,均为渡部书记生,此人应为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中下级官员。信的末尾,均没有注明时间,而外务省按照收文先后,把它排列在明治十六年七月八日与九日之间,故可判断此文送到东京的时间应为光绪言九年六月初五日与初六日(1883年7月8日、9日)。
张之洞作为一个很有头脑的封疆大吏,很早就对日本予以注意。他看到日本经由明治维新之后,蒸蒸日上,一日千里,尤其是甲午战争中,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居然把清王朝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严酷的现实,使张之洞心灵受到子强烈的震撼,头脑受到深刻的刺激。穷则变,变则通。头脑灵活身处高位的张之洞,希望中国能借助日本经验,引进日本先进的经济技术、兴办日本式的企业,按照日本的军事训练方法来训练中国军队,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张之洞虽然早有取法日本的念头,而他所产生联日的冲动,则是由日本派参谋大佐神尾光臣访问湖北引起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德国出兵抢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列强虎视眈眈,调兵遣将,蓄势待发,瓜分豆剖之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而日本军方恰在此时亦开始在长江流域活动。参谋神尾光臣原在驻北京公使馆任事,后被参谋本部选中,专程前往武汉拜谒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张氏对日本军方代表之来访,开始颇有戒意。他不知道日本人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故而采取回避态度,只让他的亲信钱恂及海关道等与神尾光臣周旋。但是,当钱恂将同神尾光臣会谈的情形告知张氏之后,张之洞则大为振奋。据《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条下记载:
十七日出省勘京山唐心口堤工,二十八日回省。日将神尾光臣来,公方出省,令关道及知府钱恂接待。神尾密示修好之意,是时俄谋占大连、旅顺,德据胶州,英欲擅长江之利,各国军舰云集海口,日本怵于大势遣使来,嗣神尾又遣其参谋部员宇都宫太郎来密告,奉政府命,劝中国结好英日,派学生赴日学习陆军。派学生赴日起意于此。
年谱的上述记载太简略,使人几乎看不出神尾光臣之行,对张之洞产生了多大的刺激。而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却对此记载十分详细。
张之洞非常惋惜没有能见到神尾光臣,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一方面他草拟电报给神尾光臣,但张氏并不知神尾行抵何处,故只好发给上海道蔡钧,让蔡氏想方设法找到神尾,此电报保存于《清国兵制改革》刚开头部分。其文曰:
上海蔡道台,此电请探转苏杭宁波等处。日本参谋大佐神尾君光臣:台驾来鄂,适先期奏明,出省勘堤工,仅派江汉关道及知府钱守接待,深以为怅。回省后该两员禀告阁下来意,极为欣悦。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交谊远过他国,方能联为一气。现在极愿面商一切切实详细办法。但中国制度,督宪不能出所辖省分,而此等事非面谈不可,可否请台驾来鄂省,俾得面罄敝国真意。是关东方大关系事,不胜盼企之至。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情词恳切,急于面商神尾光臣的心情已跃然纸上。但蔡钧却不知神尾一行的行踪,无法直接代达,只好转交给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代理二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而小田切氏此时正在“苏州出张中”,他返回沪上见到电报时,亦感到十分兴奋。可惜,神尾一行已在归日途中。因此,小田切除将电报转神尾光臣外,还于明治三十一年一月四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将电报誊写一份转给他的上司,日本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并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介绍神尾在武汉与张之洞代表钱恂等会谈情形,以及他对张氏这份急电的处理意见。由此,可清楚看出,日本政府对张之洞的积极反应是十分重视的,而且,他们始终是把介入清国兵制改革作为与张之洞交往的中心内容。张之洞为了尽快与日本代表晤谈,还试图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设法找到神尾光臣。在《张之洞未刊电稿》中,尚保留着张氏之有关电文。张氏称:
致杭州{廖抚台,日本神尾、尾川两将来鄂,弟适出省勘堤工,予饬关道礼待。据述来意,重在修好联交,及派人就学,颇关大局。今拟邀伊等重来相见,伊等离鄂,见岘帅后,由苏
而杭,必谒台端,请达鄙意,代为劝驾来鄂,面谈商办为祷。丁酉十二月初四日,巳刻发。
张之洞联日冲动,还充分表现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1898年1月2日),一天之内,连续三次致电北京的总理衙门,反复阐述联日的重要。
第一封电报于是日辰刻发出。张氏在此电中详细分析了胶州湾事件之后的国际局势,表面上同意总理衙门不能轻易与外国结盟,“仅联一二国,适启争局”的方针,实际上却是在表述,当务之急是“首先迅速联英倭”。并称:“倭情甚急,自欲防害,必无奢望,落得联之。”
另外,北京的《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强学会》同日创刊)刊登了《中西纪年比较表》,其开头部分有如下内容:“神州以君纪年,海外以教纪年,义名有取也。万国既通,考据斯赜,沟而合之,而无眩焉。”反映出康党对纪年法的强烈兴趣,姑—且不论其中是否“寓有改元之义”(汤志钧),“神州以君纪年,海外以教纪年”等表述,与下文将要提到的《大同书》中的内容重复,实在意味深长。
《强学报》头期发表的“孔子卒后两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文字,果然耸江南土人之听闻。就连强学会的会员们也闻之变色,惧怕祸及自身,要求将康有为除名。十二月初,南京来电云“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命令查封强学会,《强学报》也被迫停刊。而发电人正是对康的孔子改制说一贯持反对态度的张之洞。《强学报》被迫停刊的理由,如上所引《申报》的消息,是因为擅自刊登了尚未公开的“廷寄”,以及事先未经商议使用了孔子纪年这两点。其中,特别是后者是促使张之洞翻然改变的直接原因,他认为使用孔子纪年是对清朝正朔的否定。
孔子纪年对当时的人们具有何等巨大的冲击,这从湖南“旧党”对康梁一派的猛烈批判和攻击中可窥见一斑。例如,在汇集了反变法言论的《翼教丛编》的序文中,编者苏舆有如下议论:
其(梁启超)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古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
值得注意的是,对孔子纪年的批判是和批判平等、民权等西方的新学说相提并论的。虽然同样敬奉“先师”“圣教”,但在当时守旧派看来,孔子纪年竟然和平等、民权同样是异端邪说。不过考虑到了L子纪年的构想来自基督生诞,倒也难怪这种批判了。另外,与苏舆联手攻击变法派的湖南“巨绅”叶德辉,在《正界篇序》中反对梁启超的《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攻击新党“以孔子纪年黜大清之统,则无古今之界”。他也和张之洞一样,从孔子纪年判断康梁一派具有否认清朝正朔的意图和叶德辉的头脑中,大概早已出现了“民权=平等-托古改制=孔子纪年=反清无君”这种等式。这是当时变法反对派的典型反应。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