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反全球化国际”向中国集结
“华盛顿共识”是否同时也是华盛顿的政治权力扩张,则是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华盛顿共识”的批评家们在批评这项共识时,就内在地把“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作为美国霸权之都联系起来了。例如,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就把“华盛顿共识”等同于美国强权的全球扩张。他指出,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国际商报》已经把那些经济组织看成是‘新帝国主义时期’的‘事实上的世界政府’的核心。”尽管这种新自由主义仍然具有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内容,但是,首先它已经有了某种国际扩张性政治权利的形式,因为现存的各种国际性经济组织不过是现实权利的分布状况的反映,甚至是权力放纵的结果。实际上,目前现存的国际组织是二战后世界结构的基础,确实反映着战后的权力现实。美国是这些制度形式的支撑,这些制度也是在美国的提议和安排下建立起来的,自然体现着美国的价值观。一位评论家指出,华盛顿之所以能够成为事实上的“世界政府”,在于美国拥有着世界财富的一半,而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秩序中,这种经济财富很自然地转化成了政治权利。其次,“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并不只是某种强制性的经济价值判断和价值决断,而且还有扩张性的政治价值判断和政治决断。在这里,经济与政治被一体化了。最后,“华盛顿共识”的意义并不是现代人所期待的那种“公共理性”或人类公共性,而是一国政治意志的普世化,因为美国政府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来推行其全球体系谋划的。作为世界的强者,美国意欲筹划的是如何运用这一强国地位及影响去建立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体系。。
把“华盛顿共识”视为美国政治强权的全球化扩张,是一股国际思潮。姑且把这股思潮或运动称做“反全球化国际”。在经济学家中,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批判者,也是这一思潮的一部分。在中国,“华盛顿共识”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好名誉。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组织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研究”课题组,这个课题组历时8个多月完成的新自由主义研究论文集《新自由主义评析》这样描述“华盛顿共识”: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他们给出的建议是:中国要警惕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华盛顿共识”设下的世界“一体化”陷阱。这些看法在各个国家的首都,都有不少的信奉者。
这些看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设在华盛顿和纽约的世界性组织,是二战后国际体制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作为强势的经济体,它们在思想市场中处在垄断地位。对这一体制不满的人,总是设想用新的体制代替这一体制,打破它们的垄断。但历史不免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寄予厚望的体制,在世界体制市场的竞争中,表现并不好。拉美曾经尝试过一些体制,前苏联集团也尝试过一些体制,印度、中国也尝试过一些体制,东亚那些曾经创造了奇迹的国家和地区也尝试过一些体制,但是,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体制纷纷崩溃或陷于危机。但是,反“华盛顿共识”的人不是把陷于危机的体制视做是本国试验的失败,而是视做华盛顿的失败,本来,这些实验都是为了探索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指出的道路的。他们不是把失败视做自己的制度的失败,而是看做别人制度的失败。他们不去检讨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贪婪、颟顸一再延误改革进程,而是责怪某个“共识”。正如在1998年印尼危机期间,一些集团不去谴责苏哈托及其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愚蠢,而是对前来救助的国际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的“姿势”愤愤不平(当苏哈托与IMF签署文件时,康德苏两条胳臂交叉着放在胸前,俯身看着正在签字的苏哈托,这一姿势成了IMF傲慢的标志。),并把印尼危机的原因,全算在这个组织身上。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塞迪略在评论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一再出现危机时也指出,在拉美,一场危机引发改革从而立即带来了成效,但是这些成效不久便导致人们自鸣得意,最终再次引发危机。而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将该地区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改革,而不是改革不彻底。此外,他们还乐于将自身的经济不景气归咎于外来者。
在这里提出的背景下看,“北京共识”提出的“让中国思想走向世界”,反映了国际反全球化力量向着中国集结的倾向。“北京共识”试图为实现这种集结架起一座桥梁。在这个设计中,中国被赋予了“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全球秩序”中心的地位。这是需要警惕的动向。“北京共识”为中国描述的形象,即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中心,一个对抗华盛顿的世界级领导者,更多的是这些反全球化国际的想象。用一个比喻,“北京共识”的提出者希望在北京举办一场同华盛顿竞逐舞伴的另一场舞会,按照逻辑,中国自然是不能出席华盛顿的舞会的,华盛顿也不能出席北京的舞会。中国和美国都不接受彼此的邀请。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战略当然不是自己举办一场舞会,而是接受邀请去参加舞会。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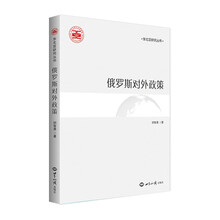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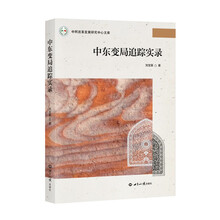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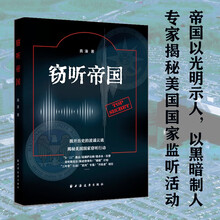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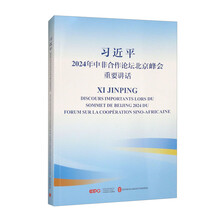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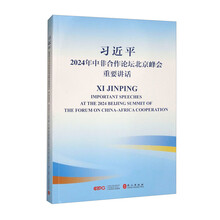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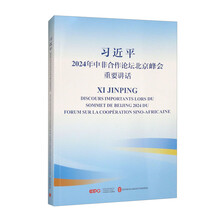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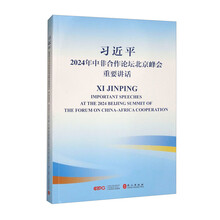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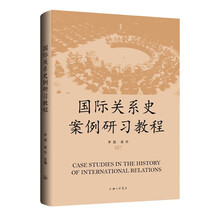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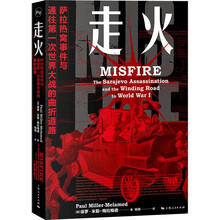
——著名经济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作者力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崛起道路上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中国将如何对待所获得的力量?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多极还是单极?是战争还是和平?中华文明在21世纪能不能提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国际秩序的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将会越来越现实地提到世人面前。作者看问题的视角,可以说是独辟蹊径,其结论,令人警醒。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 孙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