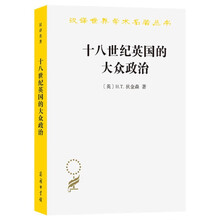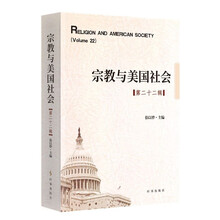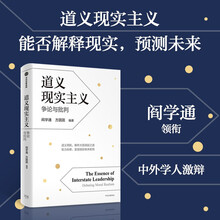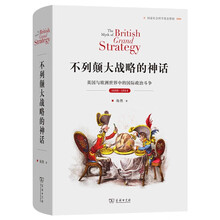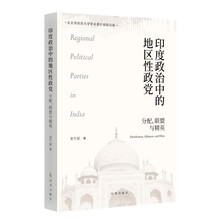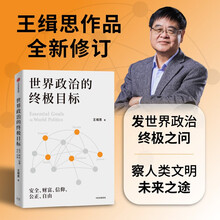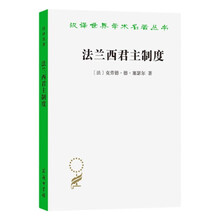今天在我们学术机构中占统治地位的许多学科都是在19世纪后期,特别是在70年代到90年代被界定,从大范围的知识中被圈出来,成为被称做系的学术结构的基础。(这一概念可追溯到1213年的巴黎大学)系主任向学院的教务长报告,标准化的课程要求、评分制度,本科生教育分成主修专业、副课、选修课,通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制度,这一切都是在一百年前才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开始的,大部分是直接从德国大学引进的。<br> 在这样一个被大卫·戴姆罗奇(David Damrosch)称为“大学的工业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原始材料“在模仿工业的新的劳动分工中”被重新组织了,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包括“知识的生产”这类新词,它的效率是靠借助工业领域的组织和管理模式来促进的。戴姆罗奇说:“这台工业机器的运作同19世纪后期完善的经济原则保持一致。自由市场竞争的规范充斥在这个体系的每个阶层,尤其是那些学科和系。在学科之内,达尔文式的斗争旨在获取思想的自由竞争,其胜者是由市场的消费者所决定的。”他们在专业化的同时也在进行排斥,新的学科人士创造了向学界之外的业余爱好者关闭的专业。从写历史到从医,妇女由此失去了许多职业培训的途径。在学界内部,新的专业人士对在他们划定的知识范围内的所有材料建立起专利权。这些垄断权力导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对学术地盘的争斗,比如在文学系和宗教学之间的争斗,在心理学和语言学之间、人类学或政治学同民族学之间、地理学和地质学之间的争斗。<br> 争斗的单位要争的不仅是思想成果,还有体制资源。我当了十二年的教务长和副校长,对学科间的争吵和恶斗体验丰富。我知道学者们是运用理论辩论和学术原则来掩盖个人利益的大师。同妇女学面对的许多的问题一样,对算不算学科的争论是大学里的流行病,不能仅仅归咎于我们事业的基石——女权主义。借用戴姆罗奇妥帖的比喻来说,到了20世纪,“学界的系变得像具有自控经济的一个个小国家”。早期大学的“质询的团体”已经变成了“质询的涣散”。随着学科身份权力的增长,“知识分子的社会交际能力”降低了。为跨越这些鸿沟而做的大量努力尚不成功。<br> 这一部体制的历史可以说明在处理学科和跨学科的问题上我们正面对何等困难的处境。就好比想对主权国家宣传国际主义!尽管许多系是亚学科之间的“便利婚姻”,那些亚学科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极深的差异,(例如像人类学、生物学和经典研究)它们可能同其他系的亚学科有更大的相同之处,但正是系使跨系的合作艰难无比。他们表现出民族主义、孤立主义,甚至是沙文主义的行为。体制的权力,包括分配资源、责任、奖励的权力,在各自的疆界之内得到捍卫。系构成了一位科学史学家所称的“动力结构”。这些结构“组装、安排和复制了对政治经济功能和使它运行的权力关系制度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技术操作”。它们也是“分配地位的工具”。大学里的知识,用女权主义理论术语来说,是具体位置和立场的知识,深深地植根在历史和政治经济以及个人的意识之中。<br> 这种情形并非全是弊病。学科为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学科也鼓励了同事间的分享、忠诚和自豪感。这些机构为学生和学者提供了体制中的家园,我们中的部分人还享受了作为这些机构成员的好处。我们寻求那些具有学科教授头衔掌管这类好处的精选人物的接纳。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如此大胆地质询“学科”这个概念?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