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昼的结构(自然要把伊斯兰教五次祷告纳入其中),是应用同一些原则的另一个尤为明晰的结果。湿季的白昼有一部分是在夜间:由于畜群进出仅一次,湿季的白昼就像干季里没有过完的白天。“热晌午归来”之日是干季的“门槛”,从这一天起,家庭主妇把炉灶移到院子里,生活节奏因畜群的两次外出而突然趋于复杂。畜群第一次外出是在凌晨,待署气开始逼人时,亦即傍晌午(doha)时就回圈;第二次外出正巧是正午(dohor)祷告的时间,到天黑时回来。
如同一年的走向是从秋季到夏季,从西向东,一天(as)是从傍晚到正午:晚餐(imensi)是一天里第一顿饭,也是主要的一顿。整个体系按照一种永恒回复的完美循环来组织,傍晚和秋
季——衰老和死亡——也是生育和播种的场合;尽管如此,但时间仍然朝向以正午、夏季或壮年为代表的至高点。在夜间最黑暗的时候,即在“半夜”的“黑暗”里,男女老少都处在住宅最隐秘的部分,牲畜边上,与坟墓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封闭、潮湿和阴冷的两性关系场所;这个最黑暗的部分与昼相对。确切说是与白昼的顶点即“热晌午”(a2al)相对,“热晌午”是日头当空、阳光最强、炎热最甚的时候。夜间的各种声响,如狗或豺的嗥叫、睡者挫牙的咯咯声——类似于将死之人的磨牙声——,使人将黑夜与死亡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显见于所有夜间禁忌。
夜间禁止沐浴,哪怕只是在水边游荡,尤其不准在死的、污黑的、有淤泥和发臭的的水边闲逛,禁止照镜子、往头发上抹油、接触灰烬:此类活动会带来严重后果,即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接触具有相同属性的物质(有些物质几乎可以置换,如头发、镜子、污黑的水)而加重夜间不祥的黑暗。
早晨是过渡和分离时刻,是一个门槛。在天亮之前几个小时内,当·白昼在与黑夜的搏斗中占上风时,人们就举行驱邪(as-fel)和净化仪式(例如,为治疗爱嫉妒的或失宠的孩子,早晨,人们在一棵孤立的荆棘下,把隔夜放在孩子头边的粗粉洒在孩子身上;同样,在某些驱邪仪式中,人们在晚间去一个地方,比如两块地的界线这样一个分离点,待天一亮就离开,把灾祸留在那里)。如同春季里举行的许许多多仪式,关键是要加紧脱离黑暗、邪恶和死亡,以“进入早晨”,也就是说向着与早晨联系在一起的光明、善良和运气敞开。开始和分离仪式,比如冬至去牛圈把牛唤醒、迎接初雪,元旦辞旧迎新、寻找夹竹桃枝并在“送别一月”(aazla)之日将其栽于地里、牧童于立春外出采集花草、“热晌午归来”之日畜群外出,等等,均具有过渡期特征,也都在黎明时分举行。每个早晨都是一次出生(naissance)。早晨是外出、开放(ouverture),是向着光明敞开(fatah’,意为“开放”,“绽开”,与sebah’即“进入早晨”同义)。这是白昼出生的时刻(thallalithwass,白昼的出生),是“光明之眼”张开的时刻,也是黑夜里自我关闭的住宅和村落把人和牲畜放向田野的时刻。早晨是作出决定和付诸行动的最佳时机。
若要阐明实践活动和作品的实际边贯性,大概只有构建一些生成模型和示意图:生成模型按其自身规则再现该严密性据以生成的逻辑,而示意图则依靠自身具有的同时化和总体化综合能力,无需语句和评述便能显示出实践的客观系统性,甚至能在适当利用空间特性(高/低、左/右)情况下,直接导致身体图解(凡需传递原动行为倾向者均深谙这一点)。无沦如何,人们必须明白,这些理论性书写游戏一旦被解释,就会使实践逻辑变 如果人们理解魔术和“参与”(participation)的逻辑与最平常的激情或情感体验(愤怒、嫉妒、憎恨,等等)有某种联系,就不会对列维—布留尔时代那些稀奇古怪的“原始心理”现象感到那么匪夷所思了;同样,如果出于一种颠倒的民族中心主义,人们不是无意识地把理智主义赋予任何“意识”的那种与世界的关系赋予“原始思维”;如果不回避致使在实践状态下被掌握的操作转为与其同构的形式操作的转换,从而不用再探究该转换的社会条件,那么,今天也就不会对澳大利亚土著的“逻辑”创举如此惊叹不已了。
婚姻虽然的保存、增加或减少(通过低就婚姻)高度整体化所赋予的权力资本和广泛的姻亲网(nesba)带来的名望资本的一个主要机会,但并非所有参与婚姻缔结的家庭成员都能从世系的集体利益中获得同等的个人利益。遗产继承传统将女性排除在财产继承之外;对世界的神话观注只赋予女性以屈辱的地位,且从不让女性完全参与其选择定居的世系的象征资本;男女劳动分工规定女性只从事家务劳动,而让男子担任撑场面的工作;凡此种种都有助于把男子的利益等同于世系之物质的、尤其是象征的利益,而且,男子在男系卑亲属集团中拥有的权力越大,他们的利益就被视为世系的利益。实际上,男人婚姻mariagedhonmla)——堂亲婚和政治婚姻——明白无误地证明,男子的利益更直接地被视为世系的正式利益,他们的策略也
更直接地服从于加强家庭单位整体性或家族姻亲网的需要。至于女性,决非偶然的是她们负责的婚姻属于平常婚姻,更确切地说,别人只让她们负责这类婚姻:妇女被排除在场面亲属关系
之外,被列为实践亲属关系,去发挥亲属关系的实际用途,与男子相比,她们在儿子娶亲或女儿出嫁问题上表现出更强烈的经济(就其狭义而言)现实主义。也许在女儿出嫁问题上,男性和女性利益最有可能发生冲突,因为母亲不像父亲那样容易服从“以家族利益为名的理由”,而在这一理由之下,女儿被当作加强男系卑亲属集团整体化的工具,或被用作与外部集团建立有
名望姻亲关系的象征性交换货币;此外,还因为母亲把女儿嫁到她的原属世系,以此加强集团之间的往来,从而巩固她在家庭中的地位。独生子的婚姻主要是向老主妇提出了她对家庭经济的支配权问题:无论是她走世系开辟老路,替儿子在她娘家那边选一个姑娘为妻,还是当选择造成女眷内部冲突,并最终威胁到男系卑亲属集团的统一,她的利益都只能是消极地服从世系的利益。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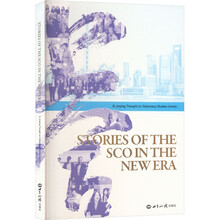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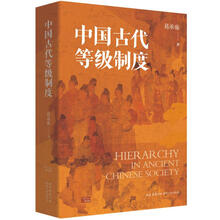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资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