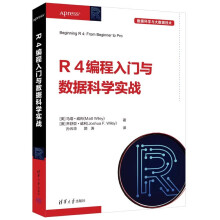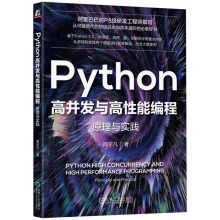目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物本身是不会创造历史的。所谓历史是人创造的,亦既是由人的目的所驱动的。人通过物的手段努力要达到人的目的。这就成其为历史。自然世界的物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而且与人无涉。而历史世界的物则是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它不是独立于人之外而是与人合为一体的。这样结合在一体的历史共同体就突出地表现为近代的科学与工业。也可以说,作为历史的主人妁人所追求的,乃是物(科学技术作为手段)与人文价值(目的)二者相结合的最佳值。一切人文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生命权、财产权与追求幸福之权以及英明远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乃至一切精神境界与道德情操,——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从科学里面推导出来的结论。它们是信念、是理想,而不是客观规定的事实和规律。但是没有这样最本质的一点,人就不成其为人,也就没有人文的历史而只有和其他一切物种一样的自然史了。因此要理解历史,我们就需要还有科学之外以至之上的某些东西:价值、目的、理想、信念。它们不属于科学实证的范围之内,是科学所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却又是人生和人的历史所非有不可的东西。我们之需要它们,丝毫不亚于我们之需要科学。<br> 展望现代化思想文化的前景,也许我们可以初步作这样两点设想:一是它将是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但并不是一个日益一元化的世界而是一个多元化或多极化的世界,统一性就要求并且包括最大限度地发展个性;二是除了科学的进步,它还必须努力保持人文学术的同步发展,没有人文学术的健全发展,科学(知识就是力量)一旦失控,很可能不但不是造福于人类,反而是可能为害于人类。<br> <br> 正如同分析哲学的那些分析研究,不管做出了多少进步,并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哲学问题一样,分析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历史哲学本身固有的问题。逻辑分析归根到底是不能提供、吏不能偷换对历史哲学具体内容的答案的。至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其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固然将取决于整个分析哲学的前途如何:但在更大程度上则将取决于历史科学本身的实践如何,即历史科学在吸收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中的合理成分并扬弃和批判其中不合理的成分的同时,怎样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确立它自己的科学的尊严。历史哲学并不是历史科学,它只能是对历史科学的哲学批判。这个哲学批判的工作怎样进行和进行得如何,都将随着历史科学本身的科学自觉而转移。<br> <br> 历史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意义是什么?答案是:“意义”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它并不叙述任何可能的历史事实。意义本身并不是历史事实,也不可能对历史事实做任何(真的或假的)陈述。但如果我们认为人生有其自身内在的价值,而不仅是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工具;那么我们可以说,历史的意义就是人生内在价值的实现。就此而论,历史就是自由的事业,这就是历史的意义所在。我们对历史所感兴趣的,总是和我们目前最为有关的东西。对历史的兴趣,更多地乃是对现在和未来的兴趣。历史已经被溶入于现在,我们的经验就包括过去的历史在内。因此,历史体系观或史学体系论就从根本上反对那种为历史而历史的学院派史学观。把历史学和哲学打成一片,也就是把历史学和人生打成一片。<br> 笛卡尔以来的思维模式,大抵上都是非历史的,虽则三个多世纪中间对世界、历史和人生也曾有过种种伟大的总结。他们的功绩不可全盘抹杀,然而这种占主流的非历史的真理观却有着如下两个难点:(一)假如它要具有立法权威,它就必须不能把任何事件委之于偶然;(二)假如它不是随意的,它就必须由推导得出,而不能从经验中得出,(但历史和历史知识却绝对是经验的。)这一两难局面如何统一,就成为有待解决的根本问题:一方面自然界是一致的,到处皆然的;另一方面历史则是完全个性化的、各不相同的。据说,真理予人自由。但予人自由的,可以是我们掌握真理的形式(科学推论),也可以是我们掌握真理的内容(历史认识与历史感)。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历史理性使非历史的真理转化为历史的真理。<br> 历史认识要靠直觉,体会,所以有其艺术性的一面。自然科学只需要纯粹理性,而历史学<br> 则需要柯勒律治所谓不同于幻想的那种想象力。刘知几要求史家三长,即才、学、识。章学诚在此之上再标史德。而奥特迦则仿佛是在此之上再标历史感,即历史的警觉性。自然科学家不需要这种历史感,他只需冷静客观地进行工作;而历史学家则需充满着历史感,他仿佛是满怀偏见(历史感有似于偏见)地在工作。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二者之不同就蕴涵着,对自然界的成功并不等于对人类生存的全面胜利。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功及其所带来的人类驾驭自然界的能力,是灼然无疑的;但它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量纲。部分的胜利并不排除全面失败的可能性。迷信科学就会导向“科学的空想主义”。困扰了奥特迦的是: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关心的都是物质享受,而不再是文明本身。工业化所造成的这种“群众社会”可以说是人道的堕落,因为人道(人的文化)的真正前提必须是把自己置身于自己之中,而不是单纯地追逐外在的物质享乐。<br> 并不是有了人,就有社会,而是有了人际(inter—individual),才有社会。但问题是:现代群众是在国家这部机器里运转着的,而国家又毁灭了人的独立、价值和尊严。一部现代史及其主人(群众)在他的心目之前,于是就呈现为一幅阴暗的画面。奥特迦惋惜国家已成为人类文明 “最大的危险”。他不信任现代群众,把群众看作有似于庸众或群氓。他本人生活于一个正值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双方“度蜜月”的时期。而他所目睹的这一可怕的群众化趋势,却由于近代人口增长的压力而增强了。他引桑巴特(W.Sombart)的研究,自1500年至1800年,欧洲人口从未超过一亿八千万,而从1800年至1914年猛增至四亿六千万。把群众释放到历史里来的,都是受近代科学之赐;而恰好也是它,是最能汩没人的性灵的。他往往带着一种贵族的偏见,以惊畏的心情看待群众或群众人(mass man)。近代人都是群众人,他们受到群众思想意识的专政。近代一切形式的暴政,都是采取群众专政形式,而到头来却是群众自己被专了政。今天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是文明的,但它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野蛮的。于是奥特迦就把希望放在少数觉醒了的文化精华或文化巨人的身上。按,恩格斯在论文艺复兴时也曾说过,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些文化巨人都不是“小心翼翼的庸人”。可见恩格斯也认为既有巨人,也有在巨人之外并与巨人相对而言的庸人。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看待双方的关系。<br> 奥特迦的以上看法,或许和他那重视个人而轻视集体的根深蒂固的倾向有关。他总是把集体看成是某种没有灵魂的生命,但是他并不全盘否定社会性。人总有其非社会性的一面,那是要靠社会性来制约的。(这使人想到康德的“非社会的社会性”的论点。)社会虽是由少数人创制,却须得到多数人的同意。然而他又始终免不了怀着一种浓厚的悲观心态观察当代的政治体制,这或许是出于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任何绝对权威在本能上的不信任。他的思想的出发点是原子式的个人;所以他的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从未受过原子式个人主义洗礼的中国读者并不同意他的态度。同时,他的态度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群众只是盲从权威的庸众;另一方面他又深深警惕到,一旦多数人起来反叛,就会势不可挡而导致整个社会政治的解体。他的群众形象,实际上是旧时代的。被扭曲了的人的形象。他没有感受到群众在革命中所进发出来的高贵品质;倒可以说,他本人在这方面是缺乏历史感的,缺乏理解历史上最根本的要素之一的能力。他所看到的现实,更多地是生活中暗淡的那一面,他没有很好地看到人(群众)同样有能力恢复自己的尊严。当代历史有许多令人沮丧的事例,但同时也有许多是令人鼓舞的。他本人已来不及很好地观察二次大战后一系列世界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固然有不少人可以怀疑人类是不是进步,是不是走向幸福;但我们同样可以找出大量与这种怀疑相反的例证。可以说,奥特迦“群众的反叛”这一根本论点,始终并没有博得人们普遍的同意。<br> 九 结束语<br> 奥特迦的理论,在技术上也并非无懈可击。首先,数理理性几个世纪以来已经铸就出一套行之极其有效的操作和符号,作为它自己几乎是无往而不利的工具。它已经取代了只适宜于表达日常生活的日常语言。倘若历史理性想要和数理理性分庭抗礼(旦不用说取而代之),它就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符号作为工具,而不能再局促于日常生活用语的低级作业状态。这一点即使能成功,也会是很遥远的事。而且即使历史学有朝一日研制出了一套新符号、新操作,从而使自己超越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性而达到、容纳或超越数理科学的精确性,我们也很难能看出它怎么能够解决如下两重严重的局限:(一)它怎么能很好地解决人生、历史的意义之类的永世问题;(二)它怎么能同时取消它自己立论的基础,即历史是人的创造,是自由的事业,因而就终究是不可预言的。作为历史学家的布罗代尔曾要求历史研究应该是长时段的(longue duree),而奥特迦所要求的简直是永恒的。历史学越是精确和定量化,它就会距离它原来由以出发的前提假设越远。历史理性的重建,看来还是困难重重的。现在所能声称的只是:历史既是生命的体现,它就只能是由历史理性去研究并解答。这或许就是当代生命派思潮对历史学的贡献所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