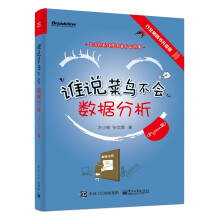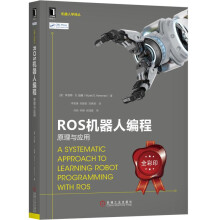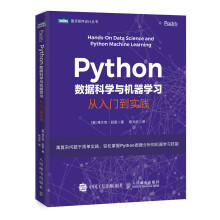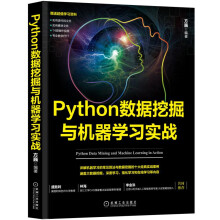中国是新自由主义全球政策陷入危机的历史关头,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狭路相逢的。有人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归结为“市场自由化”,或者“全球化”的结果,但是今天很少被人们提及的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近20年高速发展和进步,是建立在比较完善的交通、通讯设施、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教育、医疗体系,整体的人口素质和比较均衡的社会分配的基础上的。正是这一切,为80年代以来高效地利用资金和技术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些都与长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分不开。此外,高度的平等和自主意识深入人心,这些现代意识也可以看作长期的现代改革重建社会关系的结果。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一个在世界上居“主导力量”的大国,似乎必然要采用分配比较均衡的国内政策以贯彻国内的“平等意识”,因为只有这样,国民才不会感到“民族国家是外在于自己的”,才不会产生离心力,而所谓国内“向心力”对一个力图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则举足轻重,国内的平等意识和相对均衡的分配方式是达到这一切的必要条件,如果平等原则受到损害,那么国民就会越来越感到国家是外在于自己的,越来越拼命与国家作对,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导民族”。
这一切都说明,“改革开放”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当今世界既然大致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从而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中国这些“开放”条件之达成,甚至并不能与长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政策截然区分。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发展经济的条件和基础的确比较好,这既包括作为建立大规模市场的物质条件,也包括相对平等和均衡的社会政治条件。这决定了,经过40年的国家社会主义高积累,中国不但已经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庞大的人口具有如此强烈的社会合作、平等意识,实际上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劲——对解释中国近20年的快速进步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人们经常把自主、公正和平等意识看作80年代中国新启蒙思想的产物,但是,它实际上也是长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一个结果,时至今日,那些致力于鼓吹社会自主平等和均衡发展的人们,经常以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并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保护运动传统中汲取遗产和寻求合法性支持,就更加说明这一点。
“中国道路”存在着一些长处,但是,在复杂的现代传统中辨别出哪些是长处哪些是短处并不是简单的事。今天这一点经常被模糊。简单说:经济多元化乃至经济民主,多元经济、多种经营乃至区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处。因此,那种仿效前苏联实行彻底私有化,确立私有制度的一元性的方案之所以值得怀疑,是因为它足以终结中国经济的多样性生态,这首先也不是因为这样的路线是“自由主义”的,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路线与“自由主义”相去甚远,因为这是对经济生态的“休克式”严重强制,也是对哈耶克所谓“自生自发秩序”的绝妙讽刺。尽管人们以为只有以私有制的法理来保障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才能最终保证市场自由化,但是,前苏联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过程,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自然选择的结果,更不是一个“自生自发的秩序”,众所周知,那是一个政治结果,或者说,是一场“政变”的结果。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对经济的强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本,它深刻表明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一项强制性的政策,它甚至与“自由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对此人们绝对不应该忘记。
实际上,将所有社会关系简化为经济关系,进而把经济关系简化为“所有权”问题,这方面传统社会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并无区别,正如绝对私有制和绝对公有制都排斥多元经济和经济民主,这一点上它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改革的目的是开放多种经济生态还是确立一种所有制形式,这一点应该明确。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度被视为长处的绝对“公有制”或国家计划模式遭遇根本危机,苏东和中国的改革者从而致力于批评计划模式和绝对公有制的弊端,一开始这些批评具体在计划模式的丧失效率方面,随后,在哈耶克等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诱导下,这样的批评被简单导向对“绝对私有制”的肯定和宣扬,从而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离开并模糊了问题的实质。根据这样简单独断的说法,绝对公有制等于绝对专制,而绝对私有制代表绝对民主。但是,这样简单的论断完全无视了在苏东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中,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公有制”实际上从来没有实行过,它不过是一种仅仅具有字面意义的虚构罢了,那里的所谓“绝对公有制”,不过是国家垄断所有制,甚至就是国家官僚名义上不占有,实际上却支配和拥有公共财产的一种糟糕的形式,说穿了它不过是“绝对私有制”和垄断的一种高级的、也较隐蔽的形式而已,对此,马克斯·韦伯早已经通过对苏维埃政权的观察,得出过这个政权恰恰是“绝对私有制较为隐蔽的形式”的结论。“绝对公有制”和“绝对私有制”一样,作为一种呼吁单一所有制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号召,都足以对社会造成专制,在历史上看,绝对公有制不过是绝对私有制的国家和国家官僚所有制的变种,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区别。而这也就是中国自50年代末期脱离苏联“一长制”和尝试诸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营管理模式的原因。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实际上就在于推行“多种经营”和因地制宜等多元经济方式,从而避免单一的经济所有制形式垄断社会。历史已经证明,多元经济和多种经营模式乃至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保障,而确立单一的私有制度的主导作用,与社会民主和20年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把国家垄断和国家官僚名义上不拥有、实际上支配公共财富视为绝对私有制的一个变种,那么,由工人阶级的社会保护运动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所遭遇的挫
折和隐含的内部危机,实际上是从苏维埃政权这一特殊制度形式确立时就已经铸成。这里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但是,从历史上看,传统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为“所有权”问题,妄图通过对“所有权”的垄断来垄断经济、社会,在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之畅通无阻,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和私人垄断的简单取消,它仅仅意味着跨国公司取代了国家垄断的私有制和国家支持的私有制形式,垄断演变为跨国公司这种绝对私有制的新形式对全球经济的规划和垄断。根本上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毫无改变,改变的只不过是推行这些政策的主体,它已经不单是民族国家,而是跨国公司。这就是为什么三好将夫等学者坚持认为:诸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等貌似激进的学说,实际上转移了三百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略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一基本视线,而这个战略既没有被国家社会主义的方案所改变,也不可能被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说辞所掩盖。也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曾经关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全球民主的可能性,“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世界主义,不仅意味着马克思坚持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而且也意味着必须有一种全球民主化机制来应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与当今以资本开发为目标的“全球化”之间的对立所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