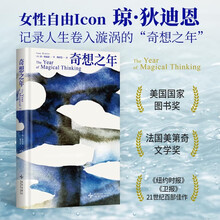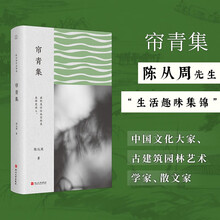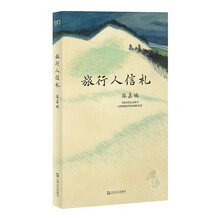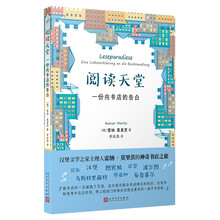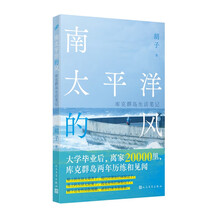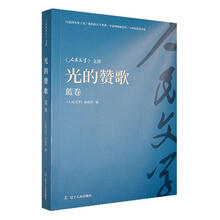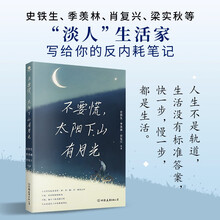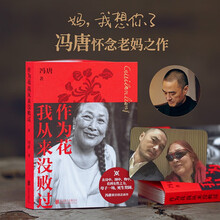读《自题小像》
鲁迅留存下来的诗计有六十一题七十八首,其中旧体诗四十八题六十三首。而真正和鲁迅一生命运和思想有深入关联的不过几首,《自题小像》就是其中之一。这首诗相关鲁迅一生的成就和志向,可以作为理解鲁迅一生实践的出发点之一。
1903年,鲁迅把《自题小像》题写在东京剪辫时的照片上,并把照片和诗题赠给了好友许寿裳。1931年,鲁迅又重新书写了这首诗,再赠许寿裳,并附记:“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相隔三十年题写同一首诗,是老来对少作的重新肯定,在鲁迅诗中是唯一的一例,有理由特别重视。三十年前,鲁迅初写此诗时,尚英俊年少;三十年后,鲁迅再写此诗时,已清峻成熟,渐臻深沉无比的境界。三十年风风雨雨,中国社会几经大变,鲁迅本人也几经大变,但这首诗所内含的思想根基却始终贯穿其中,屹立不变。《自题小像》和《自嘲》(1932)是鲁迅诗中的双璧,可作为鲁迅一生自认的思想写照。《自题小像》全诗如下:
这首诗的题旨,许寿裳有解说:“首句写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自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许氏是鲁迅老友,相知极深,其言精粹扼要,后来笺注者纷如,皆不能越此范围。今试从社会文化和鲁迅个人命运角度再作阐说。
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含中西两个不同来源的典故。“灵台”用中典,有二义:一指天文台,《诗经·大雅》有《灵台》,郑玄注:“天子有灵台者,所以祲象察气之妖祥也”;一指心,《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二义实可相成:灵台感觉到的气象变化,即相关国家兴亡变迁的大势。“神矢”用西典,即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神丘比特之箭,人一中此箭,终身再也无法逃脱。首句开启全诗,双关含有世界、国家大环境和个人思想状态两个层次。
次句“风雨如磐圈故园”是一种深重的难以改变的黑暗状态,承国家而来。三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正是鲁迅一生孤独之感的写照,承个人而来。风雨如磐,故园如是,虽经奋斗,能有多少改变?“寒星”是极长的时空数量级,相应于“星”而超时代,又相应于“寒”而甚感孤独,则与“荃不察”相关。论者指出鲁迅小说的最大特色在于写出了现代中国一群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如孔乙己、老栓、阿Q、祥林嫂等,正是“荃不察”意象的笺释。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此诗写于剪辫和满清决裂之时,1903年前后在日本反满已渐成风气,如投身反满决不乏同志,如此孤独感何来?于是不得不从较深层次寻求解释,即从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基本估计中寻求解释。
末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鲁迅一生直接为民族的危亡、民族的觉悟、民族的发展而服务的基本立场,即于此句表现之。这种直接服务于中华民族利益的基本立场,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无关,和具体政权的变化也无关,正是鲁迅可贵的品格。鲁迅一生有着极其鲜明的独立是非观,“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这一是非观的基本出发点,所以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而另一方面,鲁迅一生事业主要还偏重于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发展还不能有更深的关涉,似乎也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局限。比较欧洲近代学者康德、歌德、马克思等以“世界公民”(weltburger)自居的胸襟和气象,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以及鲁迅一生事业均有再进步的余地,也可以于此句见之。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