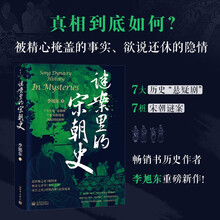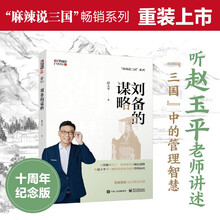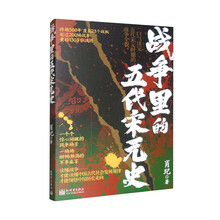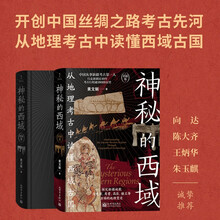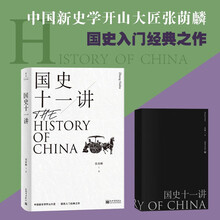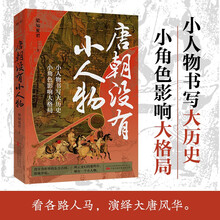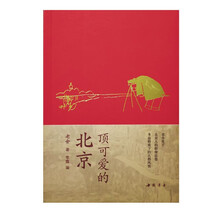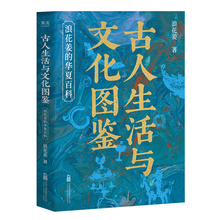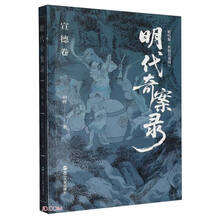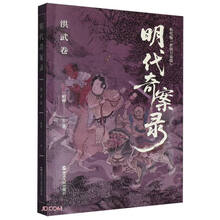都人习见官仪,多讲礼貌,周旋应对,往往中程,然其弊也伪。风气刚劲,不屈不挠,勇于赴义,重名知耻,然其弊也狠。顾本性多近质实,常见故家老辈,其接子弟后进,礼倨而词直,貌严而情亲,尚不先失民矩范,迨末季渐浇漓耳。
妇女见客,匪特旗族为然,上著亦有之。门生谒师,固无不见师母者,亲戚至,无不见家人者。余初北来,诣一远戚,乃其家闺中之人咸集,若者妗姨姑姊妹,固夙所未知也。然一片嘤咛问好之声,推本身以及南中之家人,一一都遍。实则余家人,固梦寐中不知有此戚也。彼辈亦不知余家究有何人,特臆想而遍询之,谓匪是弗亲耳。昔见笑剧,有不相识之人,乍见而呼曰:“赵”。答曰:“非赵。”“然则钱”。曰:“无钱”。曰:“若是,则孙三爷。”曰:“余无弟兄。”又有初会者,见面极亲,问其尊亲好,自家人以逮鸡犬,终则曰:“贵姓?”殆此礼作俑欤?
交际场中,亦多虚伪之风。昔于筵中晤一人,谈悉为世交。彼则极意周旋,坚约来日一饮。即而曰:“明日有内廷差,后日如何?”方逊谢,彼已呼笔书柬,议地议菜,碌乱不已。席将终,彼忽拍膝曰:“后日有家祭,奈何?”他客为解曰:“相见正长,何必亟亟。”余恶其扰,亦谢曰:“此月中鄙人方有俗冗,得暇再趋扰耳。”后终不晤。友人云:“彼之延饮,面子也。君应逊谢,亦面子也。君竟不坚辞,彼只有自觅台阶以下耳。”
贵族之家,文胜于情。新妇问安视膳,但有侍立。妾媵亦然。命坐但有矮几,弟跪于前,兄微引手而已。夫妻间礼貌亦隆。昔闻溥仲露尚书于其夫人生辰,恭具冠服,童仆持礼品先之。至夫人许,高唱曰:“老爷来拜寿,夫人出迎。”互请安道谢,肃坐进茗,寒暄而退。尚书生日,夫人礼亦如之。遇年节亦然。
亲臧获而远骨肉,讲过节而无真意,旧家之通病也。乐与仕宦交,好习官样,平民之通病也。至于好侠尚义,急人之急如其私,转在社会中之卑贱者,其殆古燕赵之遗风欤?
喜游览,妇女尤甚。正月最繁,所谓六部灯也,厂甸也,火神庙、白云观也,按时必至。春初,则出郊外,曰看青。六月,则南薰门外之南顶,永定门外之中顶,各有会。植旛、使叉、秧歌、花鼓。演者率为子弟,观者奔波远来,挥汗相属。大抵四时有会,每月有会。会则摊肆纷陈,士女竞集,谓之好游荡可,谓之升平景象亦可。
懒惰之习,亦所不免。《顺天府志》谓:民家开窗面街,炕在窗下。市食物者以时过,则自窗递入。人家妇女,匪特不操中馈,亦往往终日不下炕。今过城中曲巷,此制犹有存者。熟
食之叫卖,亦如故。
潘吴县生平精力,大半消磨于金石。尝见王莲生家藏名人手札,王得一铜器,潘借观不还,师弟龂龂相口角,亦名流之佳话也。
伯愚为长乐初将军善子傅文忠恒之孙也,其妹入宫为珍妃。将军镇广州时,颇提倡风雅。时文道羲之父任广州府,道羲与伯愚弟兄文字相结契,文之大考擢学士,伯愚与有力焉。或传道义常课珍妃读,语盖不确。志氏昆季皆有才调,喜与名士交,又世居戚里,于时文士之讲声气者,皆缔交焉。迨珍妃入永巷,伯愚外贬,名流冷落,时人为之诗曰:“今日清流尽可哀,
伯愚乌里雅苏台”云云,一时名士云散风流,亦朝土一变局也。
清流最负盛名而喜谈兵略者,南为吴清卿,北则张幼樵也。幼樵论兵事如掌上螺纹。清卿白谓精枪法,有百发百中之技,试之良信。与习者,或谓其枪上置望远镜云,两公皆主用兵以
张国威,清卿北辱于榆关,幼樵南败于闽峤,论者或谓用违其地矣。
自吴、张好谈兵而致愤覆,于是清流乃出其看家之学,以相号召而消磨日月。其目约分为五:曰三传三礼,曰金石碑版,曰考据目录,曰小学舆地,曰词章楷法。厥后道羲诸人出,始复有志于兵事。
当时名流文酒之会,率为诗钟,伯愚与弟仲鲁皆为能手。于时珍妃方得宠眷,余尝见仲鲁一联,题为分咏李延年瓦松,云:“可怜兄妹承新宠,未必风霜耐岁寒。”赏其浑成大雅,而窃讶其不祥。未几而妃贬,伯愚昆仲各窜逐矣。
清流中以李越缦为最淹雅,亦最兀傲,其自署所居门联曰:“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工部员外补缺一千年。”门内修竹数十竿,掩映窗户间,不恒病而好服药。过其居者,但闻讽咏与呻吟声相间作,时人戏比之林黛玉云。潘文勤伯瀛最礼敬之,亦恒烦其捉刀,至年节常馈赠焉,悯其贫亦惧其骂也。都中俗称马料曰喂养,潘值年节,辄嘱其仆曰:“速送李老爷喂养去,否则跳踉矣。”虽恶谑,亦见当时大老怜才之意。
清光绪初,满部员之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时有联云:“六部三司官大志小那端老四,九城五窑姐双红二翠万人迷。”皆喻其红也。
宫中三殿:太和、中和、保和,皆沿明旧制。太和为正殿,近世唯光绪亲政、大婚及宣统登极御焉。丹墀下列晶级石,百官分品序立殿阶,尊严莫敢仰视。中和殿则惟大祀看版、耕糟
田、陈农器、御驾一莅。余于光绪中与耕错田礼,往将事焉。保和殿则殿试、覆试、朝考、大考、考差皆於此,筵宴外藩亦在焉。 御正殿曰坐朝。其五日一常朝曰坐门。御门之典旧在太和门,后改御乾清门。至咸丰而中辍,迄同光朝皆未举行御门。仪物有二木箱,置乾清门左右,以至于亡,终未开也。
清之末代,不坐朝而但引见、召见。办事各衙门奏折以夜子时,由司员一人捧至东华门外,少俟,门启,随奏事官以入,至九卿朝房,折匣交奏事官录于簿。乾清门启,奏事官奉之入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呈览,时仅丑正。唯奏事官一灯置石栏上,视灯移至阶上,则事将下。俄而奏事官捧折出,呼接事,则群鹄立以俟。奏事官呼某衙门依议,曰“知道了”;曰:“另有旨”,口傅手授,百无一舛。盖视折上指痕为辨,横画曰“知”,竖画曰“议”。至光绪时,则移至西苑门,领事者咸俟于外侍卫处檐下。
天安门上旧有金凤一,凡恩诏皆从凤嘴系而下,殆所谓丹凤衔书也。臣工之接恩诏者,皆跪于金水桥下,曰听宣。宣诏官用满洲语于门上宣读,其音宛如牛鸣瓮中。
寿皇殿者,以供列祖御容,每御容前必供平果一大盘,四时弗撤也。月之朔望必祭,四时令节必祭,各祖忌辰必祭,故皇帝每晨赴寿皇殿之时为多,赴殿后,始诣慈宫问安也。
引见之制,外官及初发人员,由吏部带领,京官由各部自行带领,先具绿头签,曰膳牌,分缮衔名。由奏事处进呈。;吏部排班,班六员或八员,由部员二人领之,一日带班,一日押班。光绪时,值引见,则皇帝前坐,太后后方高坐如供佛然。引见人员奏报其简,但称某名某省人,若干岁而已。
外官监司以上及京员京察俸满者。引见后必有召见,俗谓之叫起。召见之制,在偏殿或暖阁中,宫监及帘而退,入屋而跽,先去帽,曾赏花翎者,必以翎向上,以示敬。
南书房之制,始自康熙朝之桐城张文端英。其时欲得文学之臣,讲颂经史,并备谘询,俾帝于退朝后,朝夕居左右。选于众,得文端,赐舍瀛台之西,大官给饮膳焉。盖于谈经论道之
余,兼亦商及时政得失,优礼儒臣,典至隆重。蹶后历代皆于词臣中选之,人数渐多,恩礼亦减,专供上方代笔,或书写春联、题咏书画,文学侍从而已。
上书房旧设于阿哥所,即皇帝之师傅也。亦于词臣中选拔充之。其恩赍体制亦如南书房,凡吃肉、昕戏诸典,皆得与焉。
帝师之尊无二,向于大学士中择一人任之,如李高阳、孙寿州、翁常熟皆是也。自帝以下,均尊之曰师傅,而不敢名。其殁也,例得谥文正。此外复于词林中选二人或四人以侍讲读。帝读书何殿,则称之曰某殿行走。宣统时,兼及西文,聘西人庄克敦为教授,其体制与某殿行走同,特俸给较多耳。
岁仲春,帝祀先农坛,行耕耩田礼,三王代三公,一品九人代九卿,帝四推,公卿九推。帝本三推,咸丰时四推,示重农意。作诗悬于更衣殿,后以为制。帝亲推毕,御观耕台,观公卿推。服端罩,黄缎为之,如外桂,而稍变其制。
有祀典,先期斋戒,或二日,或一日,视典之大小为差。宫中设牌于宫门外,外省官厅各于仪门外供之。内廷自帝后下及妃御、宫监、内廷行走官员,各以小牙牌一,上刻斋戒字,挂于胸前,口斋戒牌。
春秋,日月食,书灾异,以时无共主,诸侯放恣,孔子假神道以设教也。历世相沿不改,以为常仪。礼部通行各省派员救护。实则科学既明,钦天监已推算时刻,分秒无误,尚何灾异之足云?然奉行者莫敢废也。各署所派皆资浅闲散之员,届时诣太常寺,列跪于庭。庭中具钲鼓僧道,设坛唪经,金鼓梵贝之声,杂然并作。复有纠仪御史,监察其问,见有欹倚谈笑者,谓之不敬。此制至光绪末年始罢之。
衣服之制,四时更易,皆由宫中传出,登之邸抄而行。各部署引见时,冬裘不得用羊皮,恶其近丧服也。夏不用亮纱,嫌其透体也。遇万寿或年节皆蟒袍,谓之花衣期。逢斋戒、忌日,皆青外袿,渭之常服。国丧则入临皆反穿羊皮袿,余日元青袿,至奉安始止。德宗病革时,传各堂官入内,都御史张英麟以为帝已崩矣,遽反穿羊皮袿以入,为某王所诃而出,当时传以为笑。
花翎与古之貂蝉同,初唯近侍宿卫有之。康熙时皇子某欲之,求于上,特为制五眼花翎赐焉。自后虽福文襄有大功,仅得四眼而已。宗室子弟,年十二能试箭者,得赐翎冠上,但缀翎无顶戴,名之曰空花翎。余则以赏军功。昔日汉文臣赐翎者甚少。自捐例开始,人人可得。其极也,仅费二百金。故外省官员,几于无人不翎矣。六品以下官,如有赏赐,仅得戴蓝翎。其
用于花翎者,无眼而已。
自八分镇国公以上,均戴宝石顶,色正紫,无顶柱,故不穿眼,下钻二孔,以缀于冠。然三品之明蓝顶,亦曰蓝宝石顶,亦可不用顶柱也;又有红绒结顶者,向唯御用,间以赐臣工一二人而已。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