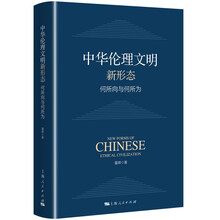哲学一再试图克服将世界分为主体性和客体事物,分为认识的实体和广延的实体的作法。这种划分不应当被僵化为截然寸明的一成不变的本体论的二元论。很可能应该把人类的主观化和自然的客观化看作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主体是历史。它被分化为人类主体和自然客体,但它仍然是差异中的统一。如果历史的辩证法代替本体论的二元论成为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差别的解释性框架,那么,我们应该问,是否可能有这样一种未来,那时,这一差别将被吸收到更高的统一体中,以致目前存在于反题中的张力和矛盾将被和平方案所代替。属于德国唯心主义派别的历史哲学曾着重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异的辩证概念只包括人同自然的关系,而不包括自然本身。即使是在历史辩证法中,自然也仅仅是作为人类的客体出现。通过知识与劳动,自然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受到重视。这种态度不允许根据自然的独立特徵来认识自然。
虚无”这个短语究竟否定了什么?莱布尼茨和海德格尔提出的基本本体论问题是:“为什么毕竟有某物,而不是虚无呢?”如果我们采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达到下面的歧义性。如果“虚无”这——短语是对“毕竟有某物”的否定,那么,精确的说法其实应该是:为什么有某些事物,而不是“没有某物”(nicht etwas)?但是在莱布尼茨的问题中,“虚无”中的否定显然超出了对毕竟有“某物”的否定。它的意思是对作为整体的存在(任何事物)的否定——“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但是,他的目的也可能是否定绝对的存在(des absolute Sein),这样,绝对虚无就是同绝对存在相反的术语。这样,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绝对存在的否定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从无中”这一用语就隐约地指向神(de Deo)。也为了排除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复归,自奥古斯丁以来,这一用语就成了:不是从上帝,而是从虚无中[创造](non de
Deo,sed ex nihilo)。后面我们将会回到神秘主义对“从无中”这一用语的解释。我们暂时只是先确定,这一用语柄述了《旧约》中用来表示创造的动词bara的独特含义。但是,在肯定的术语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世界既不是从预先存在的物质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从神的存在本身创造出来的。它是被上帝的自由意志创造出来的(creatio e libertate Dei)。如果它是通过上帝的自.由意志创造的,而不是从上帝本质中流溢出来的,那么,创造行为必须以神的创造意志的决定为基础。上帝决定要做世界的创造主,然后他才创造了事物。创造物不能被认为是从最高存在流溢出来的;但是也不应当把它看作是柏拉图哲学中武断的、反覆无常的巨匠创造主(Demiurgen)的“作品”。上帝有选择余地吗?上帝掷骰子吗?爱因斯坦怀疑地问,在他看来,这是对世界的合理性以及对他对世界的信赖的质疑。这种对武断的上帝的批评是合理的。所以,当我们说上帝“出
于自由”创造世界时,我们必须立即补充说“出于爱”。
人类历史本身并没有完全交付给当今人类的独裁专制主义。人们有能力去压迫、剥削和屠杀生活在当今的其他人,奴役他们的子女,可以蹂躏他们的后代的生命,可以毁灭未来一代人的未来。但是,他们却不可能毁灭死者已经经历过的生活以及往昔生存时的欢愉。怀特海称之为“死者的客观的不朽性”。我愿意采纳这一观念,并加以修改:我们的未来可以被剥夺,但我们的过去不能被剥夺。死者不受我们的威胁,尽管他们生活的目标和盼望的对象都取决于我们的决定,因为它们还没有实现。有待经历的生活仍面临着危险和虚无。但已经经历的生活却免除了毁灭的命运,并永远摆脱了时间的威胁。
伊里亚特说,“对于宗教信仰者来说,空间并不是同质的。”这是古代人的空间经验,我们仍能在宗教史上看到这一点。空间总是被特定的主体居住和支配的空间,不管这些主体是动物、人类、诸神、灵魂还是魔鬼。一个特定的空间是这种主体的环境和力场(Kraftfelder)——主体填充和支配的地方,它在这里寄居,这里因而就被当作这一特定生命的领域而受到尊重。当摩西赶着他岳父的羊进山时,他无意中进入了他所不知道的上帝的空间。因此有个声音对他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出3:5)。圣地总是一个被划定的空间。帐幕(Temenos)把它同具有渎神性质的空间分隔开来。神圣的土地通过魔法和仪式受到保护,免受世俗和敌对世界的危害。在进入圣地之前,在圣所门口要举行清洁礼。
尽管以这种方式与渎神的和混沌的世界隔绝,同时把它排除在外,神圣的空间仍然“向上”,对神的到来开放。雅各的梯子就是一个《圣经》例证(创28:12—19)。在梦中,雅各听见有个声音,“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雅各回应道:“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他就在这个神圣地方建立起伯特利神殿。由于这些空间把世界隔在外面,所以,这神圣的空间就是天国的门。它们是从世俗存在到天国存在的转折点,是从具有神圣性的存在的性质向具有人性的存在的性质的转折点。宗教的空间非同质性观念,以关于不同类型的存在的宗教经验为基础。因此,它认为现世是有限的和被决定的存在,而天国则相反,是不被决定的存在。只有当宗教关于“另一个”(即天国)的经验丧失其力量时,同质的空间的观念才能出现,这是一视同仁地向四面八方延伸的空间,其界限是不确定的,其内容
是不固定的和无限的。
关于神圣空间的宗教经验,是和世界起源的象征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世界的中心点联系在一起的。在古代,土地的占有和耕种总是被当作天体起源。有人居住和被开垦的土地必须用围墙或用壕沟围圈起来。这样,它就脱离未开垦的自然,并服从于人类文明的秩序。通过占有土地、瓜分和安置土地,人类重演和庆祝原初创造世界的行动。因此,人类文明的核心就是
崇拜仪式,它使人类在地上的活动合理化和神圣化。关于世界的中心有许多象征。地轴(axis mundi)可以用地球的帐杆或支柱、世界山脉或圣城来代表。它总是直立的,因为它符合人类在
地上站立的姿式和地球的引力。即使在今天,当教皇向罗马城及全球(urbi et orbi)发出祝福时,总是继续宣称罗马是世界的中心。
的确,每一座圣殿都代表世界的中心。它是上帝在天上寄居的反射。所罗门的圣殿可能是按照天国的蓝图设计的(代上28:19)。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地上的形象。基督教教堂、罗马式大教堂和哥特式大教堂都被认为是天堂和天国城市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天的形象(imago coeli)。
在时间的经验中,我们已经看到,相同事物的“永恒复归”的仪式把暂时性的事物之流安排得井然有序,并且驱除“历史的恐惧”。同样,在空间的经验中,神圣空间的秩序排除了自然界无序的、有害的混乱。人类生存的空间才有可能围绕神圣空间的中心,并且才能稳定。在神圣的事物以尘世的形式出现的地方,世界才能成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
人类不能生活在无边无际的空间。的确,和动物不一样,他们没有属于他们种群的固定环境。但是,即使是单个的人,也不能生活在纯粹开放的世界中。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都会创造自己的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中,他才能找到安静,感到“自在”。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人类的寓所。人类主体通过圈定空间来确定自己的空间。德语中表达篱笆围墙的词语是“围篱”(Umfriedung),它和“平静”的意思有关系。边界以内是称为家的领地;边界以外则是属于外国的和陌生人的地方。边界以内是家庭平静占统治地位;边界以外的生活可能是不友善的生活。边界以内就像在家一样,有一种“正当的感觉”,边界以外,是危险的。在寓所内是舒适的;外面则不舒适。今天,所有这些字眼都是感情的表达。但是实际上它们也表示人类有可能生存在其中的疆界。活着的人的空间总是被围圈起来的空间。被围圈起来的空间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身体的广延属于身体的定义一样。人类的最初空间就是身体。但是,人类生活所造成的空间的封闭性,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也不仅仅是为了驱逐异己。它同时也意味着同周围的存在和他们的环境进行交流的可能性,它造成睦邻关系。界限同时也总是交往和接触的机会。正是在这个边界上,生活的形式得以确定。因此人类环境的界限和其它生物的环境一样都不是排外性的。每一个把一种生物的生存空间封闭起来的边界都是开放的边界。如果它被封闭,则生物就会死亡。任何一个空间的所有权,同交往的普遍的结合中的生存共同体,都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恰恰是使彼此成为可能的条件。
“万物都有它的时间。”万物也创造和造就自己的空间。所有的生物都需要也都创造了属于自己并符合自己本性的环境。”生态学的空间概念和耶稣再来的时间概念(der kairologische Be-griff der Zeit)是一致的。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不是同质性的。它们都是个别的,都是由发生在它们“之内”的事件创造和决定的。没有发生的事件,它们就根本不存在。没有离开事件的虚空的时间,也没有离开客体的虚空的空间。但是,人们是如何得出无限宇宙中同质性空间的概念的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