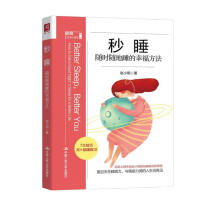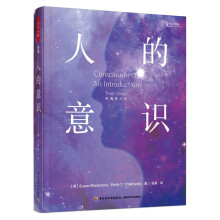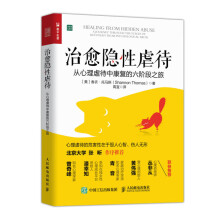我将在下文中讨论有关应用心理技巧来解析梦的可能性,并由此显示所有梦均充满特别意义,而与梦者白天的精神活动有所联系。然后,我拟再就各梦所隐藏的奇异暧昧做一番演绎,以期由此看出梦的形成过程中所含之冲突或吻合之处。为了使梦的问题变得更容易了解,我对这方面的努力使我不得不对有关梦的各方说法作一通盘整理。
本书中我拟对早期以及当代有关梦的理论先作一概括的介绍,因为在以后的推论中,我将无法再有机会谈到这些。尽管梦的存在早已在几千年前即令人困惑,但科学方面的了解其实仍是非常有限。因此所有有关这方面的t/e述,从来就没有人能引用一家说法涵盖一切现象。读者也许都自己有过不少奇异的经验或有关此类的丰富材料,但真正有关梦的本质或其根本的解释方法,相信也仍付之阙如。当然,受一般教育而非梦分析专家对这方面的知识,那是更加贫乏了。
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均深深影响他们对宇宙和灵魂的看法,而这些有兴趣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我只好推荐有心之人详读拉巴克(Sir John Lubbock,2pLord Avebury),史宾塞(Herbert Spencer),泰勒(E.B.Tylor)及其他作者之名作。在我们未能完成释梦工作以前,我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他们对这问题所作的玄思及推测将有多重要的贡献。
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对梦的看法迄今仍深深影响一般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所发的启示。也因此,它必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也就是说梦是在预、未来的。因此,梦内容的多彩多姿以及对梦者本身所遗留的特殊印象,使他们很难想像出一套有系统的观念,而需要以其个别的价值与可靠性作各种不同的分化与聚合。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也就完全取决于其个人对一般人文看法的差异。
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两部作品内容中曾提及梦,当时他们已认为梦是心理的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谕,而是一种由于精力过剩(diamonic)而来的产物。他所谓的“精力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仍是受制于人类精神力的法则,当然,这多少对某些人而言,也与神灵是有点关系的。梦是按梦者本身睡眠深度所产生的不同精神活动,亚里士多德曾提过一些梦中的特点;举例而言,他观察到梦能将
轻微的睡中知觉导出强烈的感官刺激(“一个睡觉中的人在他感到肉体上某部分较暖和时,他可能梦见自己走人火堆中”),由此他推论梦很容易告诉医师病人最先不易察觉的病兆。
由此,读者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以前的作者们并不以为梦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坚称神谕的存在。因此,自古以来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就一直无法妥协,古人曾谋略将梦分成两类,一种是真正有价值的梦,它能带给梦者警告,或预卜,而另一种无价值、空洞的梦只是带来困惑或引入歧途。
第二章 本书的开场白即已标明我在梦的观念上所受传统看法的影响。孙主要想让人们理解“梦是可以解释的”,而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对梦的解释所作的贡献,其实不过是我这份工作的附加物。在“梦是可以解释的”这一前提之下,我立即发现我完全不同于时下一般对梦的看法——因为要“解释梦”即是要给予梦有个“意义”,用某些具有确实性的,有价值的内容来作“梦”的解释。但就我所看得出的,梦的科学理论一点也帮不了梦的解释。因为,第一:根据这些理论,梦根本就不是一种心理活动,只是一种肉体的运作,透过符号以呈现于感官的成品。外行的意见一直是与此相反的。它们强调梦的运作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可是它们虽认为梦是不可理解的,是荒谬的,却又无法鼓足勇气地否认梦是有任何意义的。由本能的推断,我们可以说,梦一定有某种意义的,即使那是一种晦涩的“隐意”,用以取代某种思想的过程。因此我们只要能正确地找出此“取代物”(substitute),即可正确地找出梦的“隐意”。
非科学界一直在努力地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试图对梦作一番解释。第一种方法是将整个梦作一整体来看,而尝试以另一内容来取代,此法其实就某些方面看来,是利用“相似”(Analogous)的原则,而且有时相当高明。这即是“符号性的释梦”(symbolic dream-interpretation)。但这种方法在处理那些看上去极不合理、极端荒谬的梦时,一定是非常吃蹩的。圣经上约瑟(Joseph)对法老的梦所提出的解释,便是一个例子。“先出现七只健硕的牛,继之有七只瘦弱的牛出现,它们把前七只健硕的牛吞噬掉”,就被解释为暗示着“埃及将有七个饥荒的年头,并且预言这七年会将以前丰收的七年所盈余的一律耗光”。大多数富有想像力的文学作家们,所编造出来的梦多是应用此种“符号性的释梦”,因为他们就用我们一般人在梦里所发现的那份“相似”来把他们的想法表现出来削。 主张“梦是预言未来的观念”者,即利用“符号释梦法”来对梦作一番解释,由其内容、形式加以臆测未来。
要想介绍如何使用“符号释梦法”,那当然是不太可能的。解释之止确与否仍只是一种主观的推测及直觉的反应,也因此,释梦才被认为只是属于一些有着非凡天赋的佼佼者所具的专利注2。
而另一种释梦方法,却完全放弃以上那种观念。这种方法可称之为“密码法”(ciphermethod),因为这种方法是——视梦为一种密码,其中每一个符号,均可按密码册一般,用另一已具有意义的内容,一个个予以解释。举例而言,我梦到一封“信”和一个“丧礼”等等,于是我查了一下那“解梦天书”(Dreambook)于是我发现“信”是“懊悔”的代号,而“丧礼”是“订婚”,然后,我再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各意义间寻求其中联系,编织出对将来的预示。在Daldis的Artemidoros所作的释梦作品里,我们也可找出类似这种“密码法”的方法注3,但在释梦时,他不只注重梦的内容,连做梦者的人格、社会地位均列入考虑范围,因此同一个梦的内容,对一个富人、已婚的男人或演说家及穷人、独身者、贩夫走卒是完全不同意义的。此法的主要特点就在于视梦为一大堆片段的组合,而须就每片段个别处理。所谓纷乱的、矛盾的、怪诞离奇的梦,就只有用这方法来对付了。
以上所介绍这两种常用的释梦方法的不可靠性当然是明显的。就科学的处理来看,“符号法”在应用上有其限制,不能广泛适用于所有的梦。而“密码法”之可靠性又取决于每一件事物的“密码代号”是否可靠,而事实上密码的确实性又根本没有科学性的保证。因此,人们很容易同意一般哲学家与精神科医师的看法,而斥责这一套梦的解释为一种幻想。
然而,我本身却持另一种看法。我曾经不只一次地被迫承认:“的确,古代冥顽执拗的通俗看法竟比目前科学见解更能接近真理”,因此,我必需坚持梦的确具有某种意义;而一个科学的释梦方法是有可能的。我的探求方法即遵循以下途径:
几年来,我一直尝试着找寻,对几种精神病态——如歇斯底里性恐惧症(hystericalphobia(强迫意念)obsessi nal idea(等的根本疗法。事实上,当我听到约瑟夫·布劳耳(Joseph Breuer)那段意义深长的报导——“视此种病态观念为一种症状,而尽其可能地在病人的以往精神生活中,找出其根源,则症状即可消失,而病人可得复原”再加上以往我们其他各种疗法的失败,以及这些精神病态所显示的神秘性,才使得我不顾重重的困难,开始走上布劳耳所创的这条道路,而一直到我能在这条绝径上,拓展出一番新天地。将来我能在其他地方再另行详细补述我这套方法的技巧、形式及其成果。而就在这精神分析的探讨中,我接触到了“梦的解析”这问题。在我对病人要求将他有关某种主题所曾发生过的意念、想法通通告诉我 时,就牵涉到他们的梦,也因此使我联想到,梦应该可以将它利用来作为由某种病态意念追溯至昔日回忆间的桥梁。而第二步就演变成,将梦本身当作一种症状,而利用梦的解释来追溯梦者的 病源,并加以治疗。
为了这样做,病人方面需有某些心理准备。要再三地叮咛病人,注意自己心理上的感受,而尽量减少心理上习惯地对这些感受所会引起的批判,为了能达到这目的,最好能使病人轻松地休憩于榻上,闭上双眼,而严格地遵守决不容许任何心内所浮现出来的批判,来抹煞一丝一毫的感受,并且使他了解,精神分析之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他本身能否将所有涌上心头的感受,完全说出,而不因为自己觉得那是不重要、毫不相干、甚或愚蠢的、而不说出。他必须对自己的各种意念,保持绝对公平,毫无偏倚。因为一旦他的梦、强迫意念或其他病状,无法理想地被解决时,那就是因为他仍容许本身的批判阻滞了它的讲述。
我曾注意到,在我的精神分析工作中,一个人在“反省”(reflection)时的心里状态与他自己观察自己的心理运作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反省”通常较专心作“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所需的精神活动较大,当一个人在反省时,往往愁眉深锁、神色凝重,而当他作自我观察时,却往往仍保持那份悠闲飘逸。这两种情形,均须个人集中注意,然而一个正在反省的人,却须利用他的批判能力,用来拒斥某些一旦浮现到意识境界会使他感到不快的意念,以阻止它继续在其心理中进行,而其他有些观念,甚至在未达到意识境界,仍未为他本身所察觉前即已杜绝。但是,“自我观察”却只有一个工作——抑制本身的批判力。而如果他能成功地做到这点,那将有无数的意念想法,能丝毫不漏地浮现到意识里。借着这些本不为自我观察者所觉察的资料,我们就可能对这些精神病态意念作一解释,同样地,梦的形成也可由此作一合理的解释。可以看出来的,这样产生的精神状态,就精神能量(流动注意力mobil attention)的分布而言,颇似人们入睡前的状态,以及催眠状态(hypnotic state)。在入睡前,由于某种批判能力的松懈,使得不希望的意念,涌上心头,而影响了我们意念的变化,由于这种松懈,我们均习惯地称之为“疲乏”,而这涌现的不希望的意念,往往变化为视觉或听觉上的幻象注6。但在梦或病态意念的分析时,这些变化为幻象活动的,均被故意地或熟练地废弃,而将这些精神能量(或只是部分地(予以保留,用来专注于追溯这浮现到意识的不希望的意念,究竟来自何种意念。(在入睡前,这种意念已转为幻象,而在自我观察中,则仍以“意念”存在。因此不希望的意念可由此而蜕变成某种希望的意念。)
然而大多数人均发现对“自由浮现的意念”(free--rising idea)要采取这种态度,仍有相当困难,这种“批判”的扬弃,实在很难做到。不合希望的意念,往往很自然地会引起强大的阻力,而使这意念无法浮现到意识层。然而,如果参照我们伟大的诗人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所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的基本创作也正需此种类似的功夫。
在他与哥尔纳(KOrner)的通信中,席勒对一位抱怨着自己缺乏创作力的朋友,作如下的回答:“就我看来,你之所以会有这种抱怨,完全归咎于你的理智加在你的想像力之上的限制,这儿我将提出一份观察,并举一譬喻来说明。如果理智对那已经涌人大门的意念,仍要作太严格的检查,那便扼杀了心灵创作的一面。也许就单一个意念而言,它可能毫无意义,甚至极端荒唐的,但跟随着而来的几个意念,却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也许,然几个意念都是一样地荒谬,但合在一起,却成了一个甚具意义的联系。理智其实并无法批判所有意念,除非它能先把所有涌现心头的意念一一保留,然后再统筹作一比较批判,就我看来,一个充满创作力的心灵,是能把理智由大门的警卫哨撤回来,好让所
有意念自由地,毫无限制地涌人,而后再就整体作一检查。你的那份可贵的批判力(或者你自己要称他是什么(,就因为无法容忍所有创造者心灵的那股短暂的纷乱,而扼杀了灵感的泉涌。这份容忍功夫的深浅,也就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与一般梦者的分野。因此,你之所以发现毫无灵感,实在都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意念批判得太早、太严格。”(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一日的信)
其实,席勒所谓的将大门口的警卫哨撤回来所做到的非批判的自我观察,绝不是困难的。
大多数我的病人,多能在我第一次的指导后,即能做到,而我自己如果把闪过我心头的所有念头一一记下,我可以很轻易地完全作到。这种批判活动,所耗的精神能量日 减,自我观察的能量便能日增,当然,这情形尚待取决于人与物之间,所的注意力多少而定。
由这方法应用的第一步骤告诉我们,一个人法对整个梦,作为集中注意的对象只能够就每小部分逐一检释。如果我对一个毫无经验的病人发问:“这个梦究竟与你有甚关连?”十之八九,他根本无法看出什么眉目。首先,我必须替他把梦作一套剖析,然后再使他就各片断逐一地告诉我,在这一段里面究竟隐 藏着哪些有关的意念。在这最重 要的步骤里,我所采用的解梦YS法与通俗的、以前的、野史记载的那种“符号释梦法”不太一样,而与前述的第二种方法“密码法”较相近。与这相同的,我也是用片断、片断地,而非就整体地来研讨,同样的,我也视梦为一大堆心理元素的堆砌物注8。在我对“心理症”(neurosis)的精神分析所做的作品中,曾提出不下一千个梦的解释,但我在此介绍解梦的理论和技巧时,并不拟利用这些材料。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