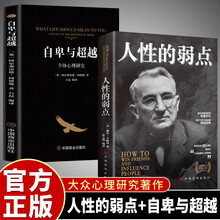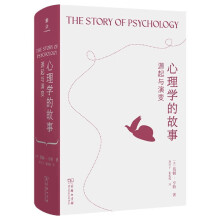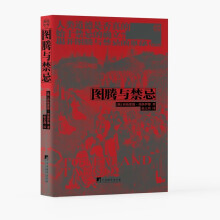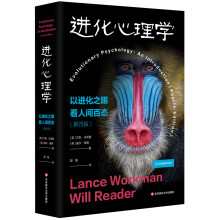死与个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从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中也能隐约感觉到。弗洛伊德把生本能与性欲相等同,实际也就是把生本能与那种保存物种之不朽的力量相等同。这也就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是死亡本能构成了物种中某个特殊成员必有一死的个体性。进一步讲,在弗洛伊德关于爱欲或生本能旨在通过寻求结合与统一来保存和丰富生命的定理中,含蓄地包含着这样一个定理:死亡本能的目的所在是分离(separation)。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也明确地把出生和死亡都说成是分离危机。[36]这样,弗洛伊德实际是在对有机生命进行一种结构分析,即将它视为由结合或相互依存与分离或相互独立之间的一种辩证运动所构成。结合或相互依存的原则维持了物种的不朽生命和个体的有限生命;分离或相互独立的原则则赋予个体以个体性并保证了他的死亡。
如果说死赋予生以个体性,如果说人是一种压抑了死亡的有机体,那么,人就是一种压抑了他自身个体性的有机体。这样,我们自豪地视人为天生禀有个体性的物种的观点,我们认为低级动物不具有个体性的观点,便都是站不住脚的。田野里的百合花有其个体性是因为它们根本不考虑明天,而我们却做不到这点。低等生物过着适合它们物种的生活;它们的个体性就在于它们是它们物种本质的具体化身,它们以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存在而最后则终止于死亡。
如果精神分析学的压抑理论确实包含着某种真理,那么,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展开过那适合于他这个物种并被赋予给他的肉体的那样一种存在方式。压抑作用使人本能般地被驱迫着要去改造人的内部自然和他生活于其中的外部世界,并因此而使人拥有了一部历史和把个人的生命附属于物种的历史性追求。历史不是由个体而是由群体创造的;而那些贩卖陈词滥调的人则令人厌烦地重复着人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这一说法。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要求指出人类社会性中的病态性,这种病态性不是与“原始”社会对立的“文明”社会才有的,也不是与“原始共产主义”对立的“阶级社会”才有的,而是所有人类社会性中所固有的。弗洛伊德“原始父亲”(Primal Father)和“原始部落”(Primal Horde)的说法(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无论是否对存在于群体组织中的病态作了充分的解释和阐明,其重要之处就在于它从临床的角度宣布了社会性就是一种疾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