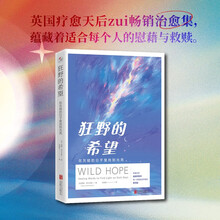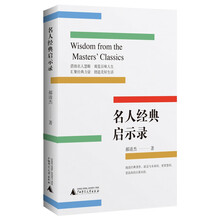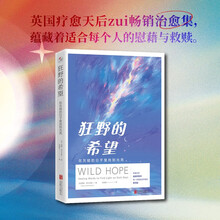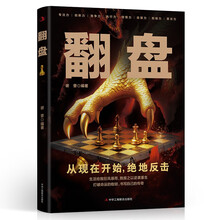美德是可以培育的,我相信这一点,而且榜样有着比书本更大的作用。那么一本美德论著会有什么用处呢?它的用处也许在于:试图理解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是什么或体验什么,这样至少在理智上,我们能够衡量和美德之间的距离。这件工作虽然微不足道并且做得很不够,却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家们是小学生(只有智者才是大师),而小学生需要书本:所以当手头的书使他们不能满足,或者不堪重负的时候,他们往往就写起_书来。然而对于每个人来说,有什么书比一本道德论著更为迫切的呢?在道德之中,又有什么比美德更值得关注呢?和斯宾诺莎一样,我不认为揭露坏事、邪恶、罪孽有什么用处。为什么总是指责、总是揭露呢?这是阴郁者的道德,是一种可悲的道德。至于善,它只存在于必然是数量众多的、超越了一切书本的善行之中,以及存在于同样不止一种但无疑不那么多的良好心态,即传统上所指的美德(这就是希腊语中arete一词的意义,拉丁文译为virtus),也就是优点之中。
一种美德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起作用的,或者能够起作用的力量。正如一种植物或一种药物的功效在于治疗,一把刀的功效是切割,或者一个人的美德是要使举止行为符合人道一样。这些来自希腊人的例子,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事物的本质:美德就是能力,而且是特有的能力。铁筷子属植物的功效不是毒芹的功效,刀的功效不是轮子的功效,人的美德不是老虎或蛇的美德。一种存在物的功效,就是发挥它的价值,换句话说是发挥它最特有的优点:好刀就是削铁如泥,好药就是药到病除,好的毒药就是使人一吃就死……
人们会注意到,从第一个,也是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功效与其用途无关,正如与它要达到的或为之服务的目的无关一样。刀在杀人犯手里的功效不比在厨师手里小,救命的植物也不比毒死人的植物更有功效。当然,这种看法并非无视一切规范的目的:无论在什么人的手里,对于大多数用途来说,最好的刀就是最锋利的刀。它特有的能力同样决定着它特有的优点。但是这种规范性始终是客观的,或者说在道德上是无关紧要的。刀只要实现其功能即可,用不着评论,正因为如此,它的功效才当然和我们不同。一把最锋利的刀落到坏人手里,不会因此就不那么锋利了。功效就是能力,而能力就可以产生功效。
然而对人来说并非如此。对道德来说并非如此。如果说一切存在物都有其特殊的能力,它以此与众不同或出类拔萃(例如一把最锋利的刀,一种最有效的药……),我们就要问什么是人的特有的优点。亚里士多德②的答复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换句话说是有理性的生活。然而仅有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欲望、教育、习俗、回忆……一个人的欲望与一匹马的欲望不同,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欲望与一个野蛮人或无知者的欲望也不同。因此像一切人性一样,一切美德都是历史的,两者不断地汇合在有道德的人的身上:一个人的美德,就是使他变得人道的一切,或者不如说是他在显示其特有的优点时的特殊能力,也就是(从词的标准意义上来说)他的人道主义。人道永远不会过分……美德是一种存在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这样解释,不过这种方式是后天获得的和持久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也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因为我们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么没有其他的人又会怎样呢?美德因此产生在人类化(作为生物学现象)和人道化(作为文化需要)的交叉点上:这是我们人道地存在和行动的方式,也就是(既然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 我们正确地行动的能力。蒙田说“再也没有比人行事的正确和妥善更动人和正当的了”。这就是美德。
希腊人和蒙田教给我们的这些道理,在斯宾诺莎的著作里也能看到:“ 我认为美德和能力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作为与人的关系而言,美德就是人的本质或本性,因为人有能力做某些仅从他本性的规律才可认识的事情。” 我要补充的是也可从他的历史的规律(不过对于斯宾诺莎来说,他的历史是他的本性的一部分)来认识。从广义上来说美德是能力,而从狭义上来说,美德是人道的能力,或者人道主义的能力。这也就是人们所称的精神美德,如蒙田所说,它们使一个人显得比另一个人更人道或更优秀;而没有它们,就如斯宾诺莎所说,我们将被看成是不人道的人。这必须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欲望为前提,这种欲望当然是历史的(没有天然的美德),没有它,一切道德都不可能存在。人道主义造就了自身,我们应该与它的目标相称。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就一再说,美德是一种后天获得的行善的心态。不过应该进一步说,它就是善的本身,的确如此。没有只需要认识和应用的绝对的善、自在的善。善不是冥想出来的,是要去做的。这就是美德:为人处世要尽力做好,这种努力本身就包含着善。这方面出现的某些理论问题,我已在其他地方加以分析。本书只是研究实用的道德,也就是美德。美德,或者说一切美德(因为美德有多种,人们不可能只把它们归结为一种,也不会满足于其中的一种)是我们的精神价值,人们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要尽可能使它们具体化,体验它们并化为行动:它们总是单数的,就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它们总是复数的,就像它们所反对或纠正的一切缺陷。这些美德就是我现在研究的对象。不过我的意图并非提及所有的美德,也不是对其中之一进行彻底的研究。我只想指出那些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美德,它们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是什么使它们变得永远是必不可少而又难以做到。正因为如此,这本论著才雄心勃勃地用书名指出了要研究的对象,而在内容方面则有种种局限。
我是如何进行的呢?我曾自问,一个人的身上有了什么样的心态、精神状态或性格倾向,就会使我在精神上更尊重他,而相反地没有这些,我对他的尊重就会减少。由此得出了一张共有30来种美德的清单,我删去了可能会与另一种重复的美德(如善行和慷慨,或者正直和正义),以及一切我通常不认为必须要研究的美德。这样剩下了18种,也就是说比我起初预料的多了不少,可是我无法再删了。因此我在研究每一种美德时不得不尽量简明扼要,这种限制也成了我的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始终支配着计划的实现。本书是面向广大读者的。专业的哲学家也可以阅读,但是不要在书中寻求渊博的学识或者彻底性。
书从还不属于道德的礼貌开始,以已经不再是道德的爱情结束,这当然是有意安排的。此外,选择的秩序并非纯属偶然,与其说是出于不知什么样的进行推论或划分等级的意愿,不如说更是出于一种时而是教育上的、时而是伦理或美学上的直觉或需要。一部美德论著,尤其是像本书这样的浅论,不是一个道德体系,这与其说是理论的,不如说是实用的道德,与其说是思辨的,不如说是活生生的、尽可能去做的道德。然而在道德里,有什么比实用和活力更为重要的呢?
像往常一样,我引用了许多别人的话,而且太多了。这是因为我想写一本有用的,而不是简明的著作。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得不列出所有的参考书目,以致使页面下方的注释大为增多。谁都没有义务去看这些注释,开始时甚至最好把它们丢在一边。把它们列出来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工作;不是给读者看,而是给不同年龄和专业的大学生看的。至于内容,是传统向我提供的,我只是重新使用,因此不想装出是我发明的样子。这并不是说在这部作品里我毫无自己的见解,相反!但是我们永远只能拥有在依靠别人或反对别人时所得到的、改造过的和变化了的东西。一本美德论著若是追求独特性或创新,不可能不成为笑柄。何况与大师们在他们的阵地上较量,与出于不知什么从未见过的意志而逃避一切相比较,要有更多的勇气和更多的价值。不用追溯更远,最优秀的头脑对美德的思考也已有2500年了。我只想以自己的方式和手段来继续他们的努力,并在必要的时候依靠他们。
某些人会认为我在做一件自高自大或天真的事情。后一种指责对于我是一种恭维。至于前一种,我担心是一种误解。就美德进行写作,对从事这一冒险的人来说,更是一种永久的、自恋的创伤,因为这会使他不断地,而且非常深刻地看到自身的平庸。每一种美德都是两种缺陷之间的一座顶峰,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条山脊:例如勇敢位于怯懦和鲁莽之间,自尊位于讨好和自私之间,或者温和位于愤怒和冷漠之间……可是谁能永远生活在顶峰上呢? 想想各种美德,就是衡量我们的差距。想想它们的优点,就是思考我们的不足或无能。这是第一步,也许是人们所能要求一本书做到的惟一的一步。其余的需要体验,一本书怎么能代人去做呢?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无用,或者在道德上没有意义。关于美德的思考不会造就有德行的人,无论如何都显然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然而这种思考毕竟培养了一种美德:这就是谦虚。它在面对丰富的物质和传统时是指精神而言,在面对我们几乎永远缺乏一切美德这个明显的事实时又是专指道德而言的。我们不可能甘心失去一切美德,但对于美德之少又无可奈何,因为这是我们造成的。
这本美德论著只对缺乏美德的人有用,这使它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也能使敢于写它的作者得到谅解,因为他并非不顾自己没有资格,而正是由于没有资格才来写这本书的。我在写作时感受到极度的快乐,我认为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至于读者们的快乐,如果它有的话,只会使我倍加快乐,这不再是写作而是感激了。所以我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