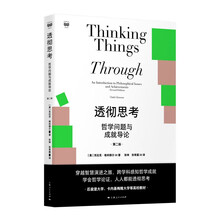斯特劳森的本体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代表性作品《个体》一书中。无论在写作风格、研究方法还是在总体目标方面,《个体》一书都不同于斯特劳森早期的著作。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占重要地位的那种对日常语言的分割式的研究,在这奉书中已不占主导地位,而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为解决重大的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服务,也就是说,《个体》一书体现着从零碎而又细致的语言分析向比较概括而全面的哲学推理转化的倾向。<br> 《意义的限制》可以说是与《个体》相平行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斯特劳森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结合康德对经验可能性的探讨研究了人类思想<br> 中最一般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或者也可以说试图从康德的思想中剥离出人类最普遍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其目标是和《个体》一书相通的。此外,《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是斯特劳森对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的某种总结,而《分析和形而上学》则集中表达了他对哲学的总体构想。<br> 尽管对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强调是斯特劳森后期思想的一贯特征,但在他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对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进行批判的《论指称》(On Referring,1950)一文和其他的哲学逻辑方面的著述中,已经提出了《个体》一书中的部分观点,至少包含了后来思想的萌芽。应该说,斯特劳森与罗素和奎因的沦争为他正面发展自己的思想作了某种直接的铺垫和准备。因此,为较充分地了解斯特劳森哲学的当代背景,本书将花较大的篇幅考察这两个论争。本绪论的重点则是简要地考察斯特劳森对哲学方法的思考、对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一般性说明以及对哲学的总体构想。<br> 一、哲学方法:分析与构造<br> 一般认为,日常语言学派和人工语言学派(亦称理想语言学派)在语言分析上的主要区别在于:人工语言学派在从事语言分析时强调的是逻辑分析,即以现代数理逻辑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从逻辑的角度去分析语言;而日常语言学派在从事语言分析时,则不把数理逻辑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他们也不是从逻辑的角度,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词的用法之间的某些细微差别。<br> 但对于牛津哲学家斯特劳森来说,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作为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同时亦是哲学逻辑这一学科分支在英国的倡导者之一,斯特劳森不但不排斥人工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方法,而且运用人工语言的方法来发展日常语言哲学,他主张把两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并将之纳入到他为哲学规定的任务的框架之中。斯特劳森关于日常语言的结构的独创性工作正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的。斯特劳森关于哲学方法的思考的一个重要文本是他的《构造和分析》(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1956)一文,此文原是他在英国广播电台举办的现代哲学介绍系列讲座的讲稿,后收入艾耶尔为这次演讲所编的《哲学中的变革》(The Revolution in Philo-sophy)一书。<br> 斯特劳森在此文中首先对两种语言分析方法进行了对比。他指出,人工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方法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美国哲学家所采用的,因此斯特劳森亦把它称作“美国学派”的方法。这个学派的主要灵感导源于弗雷格和罗素的新逻辑,因为这种逻辑提供了一种框架语言,其中每个元素的定义都是绝对精确的,并且元素之间的连结也是绝对清楚的,通过运用这种框架,这种基本的语言学工具,就可构造出其他的概念系统。这个人工构造的语言系统具有一种精确、严格的结构,它可以同松散、混乱、粗糙的自然语言联系起来,从而显示出隐藏在自然语言中的我们思想的结构。恰恰在这一事实中存在着系统构造的哲学优越性,它优于对日常语言的分析。因此,人工语言学派的语言分析方法实际上是“系统构造”的方法或简称为“构造”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给混乱和不精确的东西带来清晰和秩序。“它不仅吸引人,而且似乎还很有道理。有很多东西因为给它们的功能构造了一个简明模型后就变得更好理解。”<br> <br> 这就是说,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对日常使用的范畴和语词的规则作出解释,而在于揭示和探索作为整体的日常语言的基本结构。进而言之,描述的形而上学并不一定要局限于在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范畴,其准则应当是,排除对于什么样的概念在这样的结构中占据基础地位的任何先见,径直去研究我们所发现的日常语言的结构。在这样的研究中,自然要服从于被我们的功能性语言的语法所刻划的细微差别和在人们之间进行经验的交流的普遍需要的指导。<br> 在《个体》一书的开头,斯特劳森就扼要地给出了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我们认为,世界包括特殊事物,其中有些独立于我们;我们认为,世界的历史由我们可能参与过或可<br> 能没有参与过的特殊事件(episode)构成;我们认为,这些特殊事物和事件包含在我们日常议论的话题之中,它们是我们可以相互谈论的东西。这些就是关于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关于我们的概念图式的见解。如用一种更被认为是哲学性的尽管并不更清楚的方式来表达这些见解,那即是我们的本体论。”<br> 可见,斯特劳森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包括三个层次:世界的结构、思维的结构(概念图式)和语言的结构,而这三者在他的研究中,又是相互贯串、融为一体的,这和他在《分析和形而上学》上对于哲学的总体构想亦基本是一致的。<br> 关于世界的结构,斯特劳森认为,世界上存在的是特殊事物,这包括历史事件、物体、人及其影子,他称为殊相(par-ticulars),而质、性质、数和种则不是殊相。斯特劳森的本体论在根本上只承认个别事物存在,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但是斯特劳森作为本体论的化约论(the reductio-nist ontology)的反对者,也在从属的意义上承认普遍事物(传统哲学称为共相)的存在,如上面提到的“质和性质、数和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斯特劳森的工作理解作为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主张的特殊的和具体的事物在本体论上占据首要地位的观点提供新的理论依据。<br> 这样的世界结构表现在我们的思维结构中即是所谓的概念图式,对斯特劳森来说,基本殊相(Basic Particulars)、“殊相”和“共相。是概念图式的要件,我们运用这样的范畴来思考世界。基本殊相用来思考存在于可观察的公共参照框架即时空系统中的个体,即物体和人,殊相用来思考一切特殊事物,而共相则用来思考普遍事物。<br> 在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问题成为首要的问题,语言的角度成为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无论世界的结构还是思维的结构,都必须从语言的结构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描述的形而上学恰恰在其精神实质上是关于语言的结构的学说,而本体论也是我们的日常议论所承诺的。<br> 应当注意到,就哲学本体论的基本立场来看,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对个别事物是第一本体的思想的论证给斯特劳森以很大的启发。斯特劳森认为,亚里士多德主张存在于时空中的个体如个别的人或马是指称的基本对象和述谓的基本主词的思想实际上是正确的,而问题在于要回答为什么它是正确的及其意义何在。<br> 从斯特劳森提供的对这一点的论证来看,描述的形而上学遵循传统哲学在“殊相—共相”之间的区别与在“主词—谓词”之间的区别和“指称—述谓”之间的区别之间的联系,以殊相—共相这个区别作为基础考察了“主词—谓词”和“指称—述谓(predication)或描述(description)”这两个基本区别及其相互联系,并试图以此来把握日常语言的深层结构。<br> 作为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斯特劳森并不认为日常语言的语法就一定是误导的,与人工语言学派把语言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对立起来不同,斯特劳森认为语法表达的结构和形而上学所揭示的结构是一致的,后者只是对前者进行了重构。斯特劳森正是以“殊相—共相”的区别来重构语法所启示的“主词—谓词”和“指称—述谓”这两个区别,从而亦为他的本体论的基本倾向作了论证。<br> 与being一样,“对象”也是一个人工的术语。在日常语言中,我们惯于将这个词用于那些除人以外的物质对象。图根哈特指出,作为哲学术语的“对象”所意谓的恰恰不是我们平常称作对象的东西,而是建立在我们日常语言中的“某物”(something)所意谓的东西的基础上的。因此,“对象”所意谓的就是我们可称作某物的每个事物(by‘object’is eant everything that is something)。而这一形式在语言学上是有缺陷的。因为something不是谓词,而是不定代词。但在“语言学转向”之前,传统哲学中充斥着这种谈论,亚里士多德还为object创造了“a this”(tode is)这样一个表达式。图根哈特认为,要避免这种违背语法的表达式,就需要通过对语言学的背景的更加深入的探索,找到用来代表对象或某物的表达式,这类表达式就是那些在单称述谓陈述中充当句子主语的表达式,在逻辑上亦被称作“单称词项”(singu-lar term)。<br> 图根哈特根据达米特(M.Dummett)对弗雷格的解释,对何谓单称词项给出了这样的标准,一个表达式x与另一个表达式组成一个完全的断定句,而在从这个句子中推论出的另一个句子中,表达式x被“某物”(something)或“某人”(somebody)代替,则表达式x为单称词项。十分明显,单称词项的应用模式是与可以代替它们的代词表达式(some-thing,which,the same)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每一个这样的代词,我们都可以加上“对象”,对“哪一个”,有“哪一个对象”(which object),对“同样的”,有“同样的对象”(thesame Object),对“某物”,有“某些对象”(some Object)。而一旦“对象”这个术语得到如此宽泛的使用,即如果它的意义是由这些代词或者能够代替这些代词的单称词项的使用所产生的,那么,它就会在哲学中具有广泛的意义,甚至与“being”直接联系了起来,因为对每一事物或任何事物我们能够说“it is”就意味着“whatever something may be atany rate it is”。 因此,亚里士多德的“being”概念不但与“单一”(unity)而且与“某物”(something,ti)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每个being也是某物和单一的(one),反之亦然——在经院哲学的ens、unum、aliquid这些名称中得到了保留。”<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