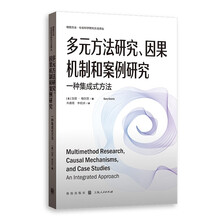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近代”这一概念,本来是地区性的欧洲的概念,至多不过是他们欧洲人内部对旧时代而言的自我歌颂的概念,可是随着欧洲自我膨胀到世界一样大,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世界性的概念,这时,“近代”一词甚至成了证明他们在世界史上的优越地位的指标。亚洲对此则或由抵抗而屈服,或由赞美而追随,结果是被迫接受了这个概念。由于经过这样的历程,所以对亚洲来说,“近代”一词不得不成为经历种种屈折的概念。
本书的意图就在于从不得不屈折转变为自由。对欧洲既不是抵抗也不是追随。既然接受了“近代”这个概念,那么索性使它扎根于亚洲。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
事到如今,既没有必要片面地规定近代是比前近代更进步或更优越的发展阶段而歌颂它,也没有必要否定近代是前近代在发展上的历史性成果。从亚洲的前近代中抽出亚洲固有的近代作为其历史的成果,并使它再生于现代,恐怕这不是无用的吧。我想,这是使世界成为真正的世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各个的自己,在这一点上,无宁说是有用的。
出自对“近代”的屈折感,我遂以中国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我的本心是希望由此亲自认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本书就是这种摸索或试验的一个过程。面对本书的校样,我为自己对问题的深入发掘还欠成熟而深感羞愧,不禁想到公开发表还为时过早,但事到如今,唯有希望读者鉴谅本书的拙稚意图,进而批判地超过它。我本人要是力所能及的话,也想这么作。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