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血”的“血”字,作何解释,在帛书《二三子》、《衷》中暂时还看不出。此字受“其”的修饰,只能是名词。以“血’’之本字作解,与帛书《二三子》、《衷》的“圣人…‘德义广大,渡物备具”、“圣人出灋教以道民”的“见文”说无论如何也挂不上钩。即使是比
喻,也难以理解。因此,只能以假借义解之。
破解“血”字之谜的线索也许就在上引孟子语中。“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这就是说以“玄黄”迎接“圣人”、“大人”的是“野…‘民”的“君子”,而“野’,“民”“箪食壶浆”迎接的是王师的一般战士——小人。依此说,“亓血玄黄”,是“野”“民”的“君子”以“玄黄”——币帛来迎接“圣人”,象征服从王化,归顺天朝。
从训诂上看,“血”与“恤”通。《周易》升、萃、晋、家人四卦的“勿恤”,帛书《易经》皆作“勿血”。如:
登:元亨;利见大人,勿血。
卒:……初六,有役不终,乃乳乃卒;若亓号,一屋于笑;
勿血,往无咎。
滑:……六五,*亡,失得勿血;往吉,无不利。
家人:……九五,亡艮有家,勿血,往吉。①而“恤”与“率”通。《尚书·多士》:“罔不明德恤祀。飞史记·鲁周公世家》作:“罔不率祀明德。”《吕氏春秋·权勋》:“是忘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淮南子·人间训》:“恤”作“率”。《广韵·质韵》:“率,领也。”《荀子·富国》:“将率不能则兵弱。”杨惊注:“率,与帅同。”《周易》师卦六五:“长子帅师。”马王堆帛书《易经》“帅”,作“衒”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可(何)谓‘衒敖’?‘衒敖’当里典谓殴(也)。”整理小组认为“衔”即“率”,通“帅”(o。“血”即“率”,指的是“野”“民”的首领,亦即孟子所谓“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的“君子”。“圣人”“广德而下绥”“野”“民”,“野”“民”的首领以币帛迎接“圣人”,这当是帛书《二三子》、《衷》对坤卦上六爻辞的理解。至于所谓“见文”等说,都是基于这一理解的发挥。
帛书《二三子》、《衷》的这些解说,虽然自称出于“孔子曰”,但符不符合《周易》经文的本义,也还值得考虑。
以周武王的吊民伐罪为背景,从王道政治的角度来解说坤卦上六爻辞,是这两篇帛书易传的特点。但是,从《周易》本经来看,这一解说也有问题。第一,解说丰富的政治内容从爻辞本身难以坐实。将“亓血玄黄”说成“德义广大,灋物备具”的“见文”,不增字为训难以说通。第二,坤卦的主旨是讲阴性的顺德,所谓“阴之为道,卑顺不盈”者即是;而“上六是阴之至极”,阴极必反,其时位当由吉转凶。如坤卦的反对卦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而至上九六爻皆九,“阳进亢极,将致灾害”,故云“亢龙有悔”。如坤卦至上六仍是“德义广大,灋物备具”的“见文”,则是“六五,黄裳元吉”的基础上吉上加吉,体现不出“物极必反”之理。所以,从易理上讲,帛书易传的说解也是不足取的。
从时位上看,《小象传》“‘龙战于野’,其道穷也”的说解是正确的。上六为坤卦六爻的尽头,故言“野”。“龙战”至于“野”,故云“道穷”。如果是“言大人之亡德而下绥民也”,又怎能说“道穷”呢?《文言》说“阴疑于阳必战”,“疑”当训“拟”,比拟也。阴
盛极则与阳争锋,比试高低短长,“战于野”势必难免。由此可知,以“战”为“绥”或:接”不足为训。“龙战于野”当是指群龙打到了天边野外。
如上所述,“亓血玄黄”的“血”当读作·率”。“率”即首领。“率”与“龙”都是指“大人”、“君子”,所以《文言说“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玄黄”不是指颜色,更不是指眼从王化的币帛,而是一双声连绵词,其义为病貌。《诗经·卷耳》:“我马虺隤
……我马玄黄。”王引之曰:“《尔雅》曰:‘虺隤、玄黄.病也。’凡物皆得称之。孙炎属之马,郭璞属之人,皆非也。”其说是,爻辞也当如是解。龙战至野,耗日持久,故云病矣:三六五“元吉”转至上六病矣,正是“物极必反”,与乾卦情形同.干以.坤卦上六爻辞的本义,既不是“天玄地黄”,也不是“阴阳交合”,更不是“言大人之广德而下绥民也”、“见文也”,而是说群龙争战至天边野外,它们的首领已领劳瘁不堪了。阴与阳争胜则病,这才是坤卦上六爻辞的主旨。
同一个卦名,上面每一例点出了两次。很明显,这些话是从两种不同来源的资料中摘录而成的。“蒙,山下有险”是一种,“险而止,蒙”应又是一种。因为是取两种资料而成,所以它们明显是两段话,并没有完全融合为一体。这里对卦象的分析,如与《大象传》比较,应该说是取自《大象传》一类的书。
《彖传》释象有与《大象传》全同的。如《大象传·晋》:“明出地上,晋。”《彖传》作:“晋,进也,明出地上。”《大象传》是通过分析上下卦卦象来解释卦名之义;而《彖传》则是解释了卦名的意思为“进”之后,再引卦象分析为证。很明显,《大象传》是本,《彖传》是流。此外,明夷卦的“明入地中,明夷”也全同,泰卦的“天地交”、否卦的“天地不交”、噬嗑卦的“雷电”、恒卦的“雷风”、解卦的“雷雨作”等两《传》也同。从两《传》的性质来看,与其说《大象传》取自《彖传》,不如说《彖传》取自《大象传》。
刘大钧先生有一些独到的论述,很值得我们注意。他说:
先看鼎卦《大象》:“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而《彖·鼎》:“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囚鼎卦的《大象》说“木上有火”,而其《彖》则曰“鼎,象也;以木巽火”,《彖》见《大象》而发,明矣!
再看剥卦的《大象》:“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其《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文中‘观象也’,所观者何象?自然是《大象》中的“山附于地”。所谓“山附于地”者,坤为地为顺,而艮为山为止,故《象》称:“顺而止之,观象也”。
特别是坤卦,其《大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彖》则望文生义,拆开“厚德载物”四字而发挥出“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的妙论,很清楚地露出了其抄《大象》的马脚。还有巽卦《大象》:“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其《彖》曰:“重巽以申命,刚乎中正而志行。”此则《彖》望《大象》而生论,亦甚明了!刘先生的论证,与上文的分析,完全一致。
对卦体的分析,《大象传》专释上下经卦之象,而《彖传》虽释象,但其主要倾向在释上下经卦之德。它们的逻辑关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卦德是从众多卦象中综合抽象出来的,是较卦象更高一级的理论思维。应是先有卦象,后有卦德。不可能先有卦德,后有卦象。《大象传》只释卦象不及卦德,只释卦名不释卦爻辞,应是较早时期的产物。《彖传》释卦德,兼及卦象;既释卦名,又释卦爻辞,应是晚一时期的作品。从卦象与卦德的逻辑关系来看,我们只能得出这一结论。
《昭力》篇共三段,都是以昭力问《易》,“先生”作答的形式出现的。第1段是阐发师卦六四爻辞、大畜九三爻辞及六五爻辞的“君卿大夫之义”,第2段阐发师卦九二爻辞、比卦九五爻辞、泰卦上六爻辞的“国君之义”,第3段阐述“四勿之卦”之义。与《缪和》等比较,《昭力》解《易》综合性强。《缪和》与《二三子》等,一般是就具体的一卦一爻之义进行讨论,而《昭力》则糅合数卦数爻之辞,阐发它们的共同意蕴。
关于帛书《系辞》的篇幅问题,学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帛书《系辞》应包括帛书《易之义》,篇幅比今本《系辞》要大,共有6700余字。这是早期的认识。一种后起的观点则认为帛书《系辞》下分上、下篇,只有3000余字,而所谓“下篇”实际上是另一篇佚书(即《衷》)。从帛书《系辞》存有尾题的痕迹以及《衷》篇首的墨钉来看,应以后说为是。
如前所述,帛书《系辞》与今本比较,缺少今本《系辞上》的第九章,今本下篇第五章的一部分、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的一部分、第十、第十一章也不见于帛书《系辞》。这些不见于帛书《系辞》的部分,除今本上篇第九章(即“大衍之数”章)不见于帛书《易传》外,其中大部分皆见于帛书《易传》的《衷》和《要》篇。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呢?人们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这些不见于帛书《系辞》的章节,是汉人塞进今本《系辞》中的,今本《系辞》是汉人糅合帛书《系辞》、《易之义》(即《衷》)、《要》之说而成的。因此,今本《系辞》的写成要晚于帛书《系辞》,不会早于汉代。一是认为帛书《系辞》是今本《系辞》的删节本,今本《系辞》的写成应在战国。帛书《衷》、(《易之义》)、《要》与今本《系辞》相同的部分属于援引。其证据是:第一,帛书《衷》末尾一段是今本《系辞下》的第九章的一些句子,《衷》对这些句子多称为“《易》曰”或“子曰”。而在当时,既能被称为“《易》曰”,又能被称为“子曰”的,只能是传说孔子所作、其地位相当于“经”的《易传》,很难说是别的什么书。第二,《易之义》所载《系辞》文,也有见于帛书《系辞》的。因此,事实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见于帛书《系辞》的,就不见于《衷》、《要》。第三,帛书《系辞》所缺少的一些章节,从上下文来看,删节的痕迹很明显;而《衷》、《要》所载《系辞》文,引用的痕迹也很明显。这一争论的是非,我们只要细心读读帛书《易传》的原文,就会清楚。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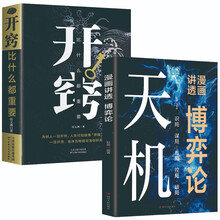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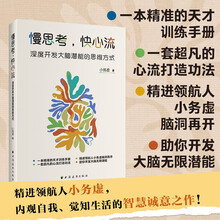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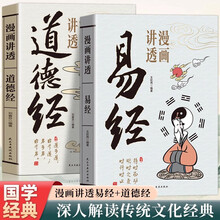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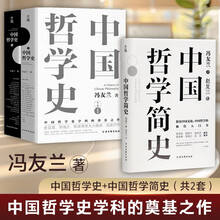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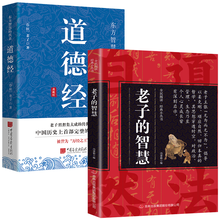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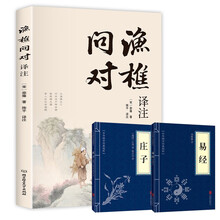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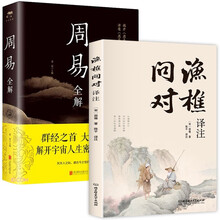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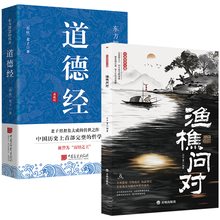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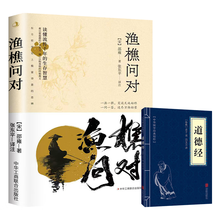
廖君名春是当今著名的青年易学家。天资聪颖,读书勤奋,是他的突出特点,但不是他的专利。他的长处在于方法高明。他治易善于独立思考,认准的东西不放弃,可疑的观点不苟同,凡属学问的事情一概较真,是朋友也不例外。往往因此惹人,惹人不免生隙。生隙也无妨,时间一久,友情会更深更淳。这很像金师景芳先生。他跟金先生念博士,金先生为人治学的精神给他耳濡目染学到手,是他最重要的收获。我最佩服他的也是这一点。
廖君易学底子打得很宽。先是易学史,然后是经、传;先是传世文献,然后是出土简帛;先是音韵、训诂、文字、考据、文献,然后是史学、哲学。几方面融汇起来,形成他坚实的学问根基。根基之上突出筒帛易学。筒帛易学重点在经、传。筒帛只是他研究易学的手段,他的目标是解决问题。他认为《周易》的问题既不是早巳解决完毕,也不是根本不能解决。他想的做的,和金先生一样:《周易》的问题只能一个个地一层层地逐步接近全部解决。廖君把这叫做“逼近法”,“逼近法”是正确的,这部《{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就是按“逼近法”解决问题的书。书分经、传、史、外四编,计17章。每章都有新见解。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能不赞成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在今年5月《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审稿会上,十几位专家异口同声肯定这书写得好,有学术价值,一致通过纳入《文库》出版。
廖君这书看不出有“主角”、“配角”之分,章章都有足够分量。开宗第一章就令我叫绝。章题叫《(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新解》。敢给乾坤两卦经文作新解,这就不简单。古今解释《周易》经文的书数以千计,敢称“新解”者绝少。廖君敢称“新解”,是不是讲大话呢?看了书就知道,真是新解。而且不但新,还正。没有标新立异之嫌。
乾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王弼注说:“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孔颖达疏说:“故‘终日乾乾’,言每恒终竟此日,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夕惕’者,谓终竟此日后至向夕之时,犹怀忧惕……言寻常忧惕恒如倾危。乃得无咎。”后之学者大体因循注疏讲,即上句下句都讲成忧患意识。上句“终日乾乾”,是说白天自强不息,拼命干。下句“夕惕若厉无咎”,是说到晚上仍然心怀忧虑,提心吊胆,不敢休息。白天晚上都干,如此则有危也无咎。至现代,人们仍然顺着古人立的竿往上爬,不管竿立得住立不住。我也这样。廖君则望竿止步问究竟。《文言传》:“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帛书《易传·二三子》:“孔子曰:此言君子务时,时至而动……君子之务时犹驰驱也,故日‘君子终日键键’。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静。故日‘夕沂若,厉无咎’。”帛书《易传·衷》:“子曰‘君子冬日键键’,用也。夕沂若,厉无咎,息也。《易》曰‘君子冬日键键。夕沂若,厉无咎’。子曰:‘知息也。”’廖君仔细推敲这三段话的意思,指出九三爻辞原来是强调君子要因时行止。该动、作时动、作,该静、息时静、息。动静作息依时而定。其中压根儿没有讲忧患意识。《淮南子·人间训》说:“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而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廖君用这条材料作佐证。证明他对《文言传》和帛书《易传》的理解,正确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