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对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对词组一样,我们同样也需要确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涵义范围。它们的相同之处是两者都处于文化之中心。从最为严格的意义上讲,现代主义指的是,出现于世纪之交、并直到目前还主宰了多种艺术的艺术运动和艺术风格。在这里,经常被引用的人物有:小说领域的乔伊斯、叶芝、纪德、普鲁斯特、里尔克、卡夫卡、曼、穆齐尔、劳伦斯和科尔纳,诗歌领域的里尔克、庞德、艾略特、洛卡和瓦莱里,戏剧领域的斯廷伯格和皮兰德罗,绘画领域的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塞尚及未来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运动;音乐领域的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和伯格(见布拉德伯格和麦克法兰,1976)。不过,现代主义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哪个年代,还曾经有过许多争论,有人就曾想追溯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豪放不羁的艺术先锋那里。至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总结为:审美的自我意识与反思;对喜好声像同步与蒙太奇的叙述结构的拒斥;对实在的自相矛盾、模糊不清和开放的不确定性特征的探索;对喜欢强调解构、消解人性化主体的整合人格观念的拒斥。(见伦恩,1985:34f1)但问题是,试图从艺术来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我们会发现现代主义的这许多方面的特征,大都浸入到了种种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之中了。那么这个术语带来的问题,连同上述与之有关的其它术语带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围绕着它何时被反向定义、何时开始用一个既定的术语来指涉某种有实质性差异的事物等问题确立起来的。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指的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就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及潜在的艺术家、知识分子来说,这一谋划的诱人之处是,它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例如,在世纪之交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就可找到这样的谋划。其中,摩尔论述道,生活中最伟大的商品是由个人的情感与审美受构成的。在十九世纪后期帕特和维尔德的作品中,也类似地小活伦理当作艺术作品。维尔德的假设是,对理想的审美应是“以多种形式、及千万种不同方式来实现自己,并对一切新鲜感怀有好奇”。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理论)早已带来了审美方面的问题。很清楚,在维尔德、摩尔及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及罗蒂(其认为善的生活标准是欲望的实现、自我的扩张,对新品味、新感觉的追求,探索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沙斯特蔓,1988)的著作之间,存在一种审美探索的连续性。如沃林所论(1986),福科揭示了生活的审美方法的核心。福科(198641-2)颇为赞同地提到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现代人的典型形象就是“花花公子,他把自己的身体,把他的行为,把他的感觉与激情,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的作品。”事实上,现代人就是“使自己头脚倒置的人。”最早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格兰由博·布鲁梅尔发展起来的浮华主义(Dandyism),通过对无可争辩的示范性的生活方式的建构,来强调自己的特殊优越地位。他们这些精神贵族,通过对大众的轻蔑,并骄之以高贵的出身、以及在服饰、行为举止、个人嗜好甚至家俱陈设等方面的优越性,总之,所有这些今天我们称之为生活方式的东西,来煊赫显耀自己(见R.H.威廉斯,1982:107ff)。在艺术反文化(artistic countercultures)的发展中,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巴黎豪放派与先锋派艺术中,生活方式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孔德·奥雷赛,直到后来的厄邓德·得,龚古尔、孟德斯鸠及于斯曼等人的作品与生活中,人们都感觉到了它们的神奇与吸引力。这种既关注审美消费的生活、又关注如何把生活融入到(以及把生活塑造为)艺术与知识反文化的审美愉悦之整体中的双重性,应该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对新品味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建构(它构成了消费文化之核心)联系起来。(费瑟斯通,1987a)
很明显,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但是,对一般大众而言,能够消费的范围是不同的。消费绝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阿多诺,1967;詹明信,1979;莱斯,1983)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采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所以,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这点我们已在前面关于后现代文化的·章节中提到过),就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固有趋势。因此,消费;文化中的趋势就是将文化推至社会生活的中心,不过它是片断的、不断重复再生产的文化,难以凝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当然,在此我们务必小心,对待文化,不要仅停留在记号与影像的系统层次上,要进一步考虑到它们在日常实践中是如何被运用的?是谁在从事文化生产和传播工作?要回答后一个问题,则又需要讨论专家在符号生产中的作用,讨论从事经销、发行和供应文化产品的各种文化媒介人。这是我们马上要讨论的问题。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势必要表明通过所有的消费文化影
来积极培育某种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即:个人被鼓励去采用一种对商品的非效用性态度,以精心选择、安排、改用和展示自己的物品(无论是装饰品、房子、汽车、衣服、身体,还是闲暇消遣),从而用独特的风格来显示出物品所有者的个性。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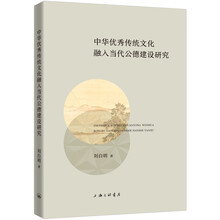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Telos)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1976),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1982)。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1982),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①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