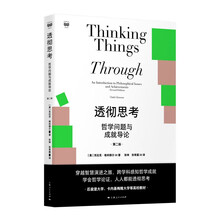我们必须不断从头开始。最重要的难题不能由别人替你解决。没有哪种解决方案是一经确定便一成不变的。我们大家都必须同样思考同一个问题,对同一个谜同样感到惊讶。正如我不得不经历童年、青春期和成年一样,我也必须经历危机、窘迫、心灵的痛苦以及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苦苦思索。
在提出关于人的问题时,我想到的不仅是关于本质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具体处境,这处境给人的难题带来了新的启示。争论是古老的,但观点却是急迫的。我们空前地认识到人的处境的无比严重性,这在我们的时代是新出现的。我们今天严肃地提出的问题在20年前可能完全是荒谬的。例如,我们是最后一代人吗?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最后一小时吗?
奥斯威辛事件①和广岛事件②之后,哲学再不能依然故我。某些关于人性的断言被证明是虚有其表,被打得粉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常识的,到头来是乌托邦主义。
哲学要想切合时宜,就必须给我们提供生存的智慧——不仅在我们孤寂的书房里切合时宜,而且在我们面临令人发指的酷行和大灾难的威胁时也切合时宜。不仅应该在学术报告厅里,而且应该在看到死亡集中营的囚徒时,在看到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时,考虑到人的问题。
人的生活中正发生着什么?我们如何理解它?我们如此询问为的是了解如何生存。
我们的探究与其他探究的性质截然相反。我们探究其他问题是出于好奇;我们探究人的问题是由于这关涉到自己。在其他争论中,探究者与问题是分开的:我知道落基山脉,但我不是落基山脉。然而谈到对我自己的认识,我想知道的正是我自己;存在与认识、主体与客体是合一的。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对人的人性进行反思时不可能保持完全超脱的关系,因为对人的所有认识都源于自我认识,人永远不能远离他自己的自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