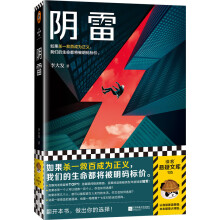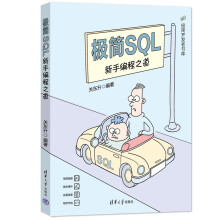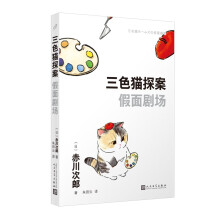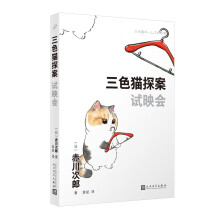综合篇
(一)怎样看待中国先秦古史
1964年春,毛泽东填写了一首很别致的词作《贺新郎·读史》。全词如下: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屏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写这首词时,正在读《史记》和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在这首词中,毛泽东抒发了“读史”过程中的强烈感受,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历程,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演进规律的基本观点。下面,我们结合这首词,作一些相关的介绍。
汉代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开头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纪》,以“五帝”作为中国历史可以上溯的最早记录。所谓“五帝”,在司马迁之前、之后,都有不同的说法,人们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司马迁记载的“五帝”,是指黄帝、颛顼(音zhudn xū专需)、帝喾(音kù库)、尧、舜这五大圣王。黄帝是在打败了原先统领诸侯的神农氏炎帝,平定了诸侯中反叛作乱的蚩尤以后,才居尊为天子的。黄帝之后其他帝王,包括后来的夏、商、周朝的统治者,都是黄帝的后代。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以黄帝及先前的炎帝作为源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自豪地以炎黄子孙相称,说明几千年来这一记载的深远影响。
其实,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对传说中的“五帝”乃至更古远的“三皇”事迹,一开始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文不雅驯”,连缙神先生、学者虽“多称之”却都“难言之”,因此很难据以书史;只是后来他跟随汉武帝巡游四方,听到各地“长老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才相信传说中的“五帝”实有其人,而他看到的有关记载“不虚”而“近是”,并决定将《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书首”加以记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结尾专门有一段文字,就是交代他对“五帝”始疑终信的情形的。至于“三皇”,司马迁只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通过君臣议论帝号时提及过,指的是天皇、地皇、泰皇,但他并没有为“三皇”专门立一篇本纪,也没有具体说明他相信不相信“三皇”的文字,大概是有疑问的。而关于“三皇”所指,也有各种传说,到底是哪三“皇”,人各言殊,仍是叫人“难言之”的。
还有更奇特的,司马迁以后,人们又编造出一个盘古,说他是开天地的始祖,又出现在“三皇”之前。因此,中国历史就被说成是:盘古开天辟地,“三皇”接踵其后,“五帝”相继禅位,然后才出现夏、商、周朝,不断沿袭下来。一句话,历史是神仙圣帝创造的。
怎么认识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中国史前史的面目呢?上述种种传说或记载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192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山洞里,发现了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中国猿人的化石;在山顶洞穴里,发掘出大约10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等。这一考古发现震惊中外,以致人们在论及人类起源时,都不得不提及中国猿人的事实。因此,所谓盘古开天地的传说,就显然成了无稽之谈,毫无根据了。同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关于女娲用黄土造人的文字记载,更属荒诞不经的内容,我们今天读了感到很可笑,不会信以为真。
1933年前后,我国学者顾颉刚等人,写了大量文章,疑古辨伪,层层剥去了古代“经书”关于史前史记载的神圣外衣。这些文章全都收集到了《古史辨》这套书中,共计八巨册,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这套书,其中第一、第七两册所收文章,主要就是针对“三皇五帝”而论的。顾颉刚先生在清代学者姚际恒、崔述的疑古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很有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论点。他指出,周朝时人们只把大禹当成最古的人,到孔子在世时冒出了尧、舜,战国时加上了黄帝、炎帝,秦代增添了“三皇”,汉代以后捅到盘古。也就是说,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地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不少的古代圣哲先皇。而这些古史的传说,除了自然演变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例如禅让之说、五行之说,后世的篡位者常常利用它,把自己装扮成合法的帝王,总要想方设法将自己算人“三皇五帝”后裔的行列里,以愚弄老百姓。顾颉刚等撰写了大量论文,仔细探讨,廓清了中国史前史的面目,戳穿了古史记载玩弄的把戏。这样一来,“三皇五帝”的神圣性也就动摇了。
考古发现和疑古辨伪相先后,从根本上推翻了古史系统的记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要真正认识中国史前史,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中间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劳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而不是神仙皇帝创造的。历史的前进,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
毛泽东这次读史填词,就是运用唯物史观,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中国历史的演变情形的。他讲,“人猿揖别”,即人类是从动物不断演变进化而来的。中国远古时代始开天地的是类人猿这种高级动物,不是盘古;从猿到人的进化是通过劳动实现的,而不是女娲的功劳。早在1943年,毛泽东就对人类进化史方面的著作特别留意,读过苏联作家写的有关著作(如郭烈夫的《从猿到人》,赖也夫斯基的《唯物的社会学》、《社会进化简史》等),曾通俗表达为“猴子变人”(《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7页《致胡乔木》)的意思,并热情推荐给刘少奇阅读,说写得“十分精彩”(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9页《致刘少奇》)。人类的历史,当然也包括中国远古史在内,首先从原始社会开篇,经过旧石器(即打制石头作为工具)时代、新石器(即磨制石头作为工具)时代,这几十万年的漫长时间在人类发展史上,不过是“小儿时节”;而接下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过几千寒热”,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只是一瞬间,但生产力发展了,先是青铜器时代,后是铁器时代,因此有“铜铁炉中翻火焰”这一形象化的比喻。这种大写意的笔法,将中国历史演进的轮廓勾勒了出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不能仅仅满足于熟悉那些“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的记载,而必须把握它的特点,掌握它的规律,认识它的真面目。
第一,是劳动创造了人,也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不是神仙上帝起作用。“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三皇五帝”这说法靠不住,不能去相信它。
第二,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也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社会里奴隶对奴隶主、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春秋末期盗跖(音zhf职)领导的奴隶暴动,“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庄子·盗跖篇》),引起大太小小奴隶主的极大恐慌。战国后期庄屦(音juē噘)在楚国境内起兵,“楚分而为三四”(《荀子·议兵篇》)。《荀子·不苟篇》称盗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即便统治阶级将他们蔑称为“盗”,也无法掩盖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名誉流传千古不衰。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敲响了秦帝国的丧钟,《史记》里专门有一篇《陈涉世家》记载这次起义的详细经过,这是人们很熟悉的。因此,毛泽东强调说,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毛泽东以诗词论历史,其基本思想跟他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表述的内容完全一致。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顺便说说。
一是毛泽东有时也在自己的诗文作品里引用一些典故,涉及到上古的神话传说。例如:他在1935年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谈及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就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传统说法;在七律诗《送瘟神》里,有句“六亿神州尽舜尧”;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末句“不周山下红旗乱”下,专门作了自注,引用各处记载,说明传说中的共工与颛顼争帝,共工是胜利的英雄;在七律诗《答友人》里,化用传说中舜帝二妃至苍梧(今湖南宁远县南)寻找舜帝的典故,写下了“斑竹一枝千滴泪”的诗句。像这样的一些例子,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其实,很简单:引用神话传说,是出于修辞的需要,是形象思维驱使的产物;否定“五帝三皇神圣事”的存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史前史的科学结论。因此,这是两回事,当然不应该混为一谈。
二是毛泽东对于古代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先后作过思考,观点也有相应的变化。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赞同中国封建制度自周秦算起的提法,至今“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早于春秋时期的西周社会,就已经是封建制度了。这其实是范文澜先生一直坚持的观点。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绪言》中,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内容。但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应该从什么时间算起,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分歧很大,有好几种说法;而且,同一位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前后的意见也会有改变。比如,郭沫若在他的《奴隶制时代》一书的序言里,就承认自己在奴隶制的下限问题上,有过三种不同的说法:最早提出在西周、东周之交(公元前770年左右),接着改定到秦、汉之际(公元前206年左右),1952年又“断然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公元前475年)。郭沫若强调指出,他之所以作出第三次改变,是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基本观点,研究社会形态后,得出的最终结论。1973年,毛泽东在晚年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换句话说,毛泽东原先是采用范文澜的提法,后来又接受郭沫若的意见。而如果按春秋、战国之交计算,则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延续的时间,就应该相应地改变成:二千多年。
总之,毛泽东在这首词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他认为:被历代统治阶级捧为“神圣”的“五帝三皇”,不过是欺骗人们的鬼话;被正史记载诬为“盗匪”的奴隶起义领袖、农民起义领袖(盗跖、庄屏、陈涉,以及毛泽东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的历次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风流人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