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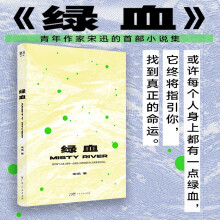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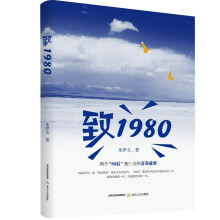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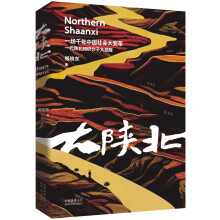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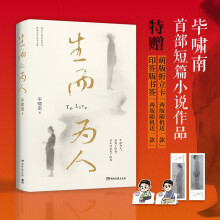

1、 他在张爱玲心中,“永远是沈从文*好的故事里的小兵”——文学史上的一页传奇、*后一位民国小说家朱西甯先生作品大陆首次出版。书中附赠张爱玲致作者的首封信件手稿,原版复刻,首次曝光。
2、 “居然在台湾发现了鲁迅的传人”,白先勇、莫言、王德威激赏的短篇小说经典——《铁浆》复活了战国时代的血性,和我们不大知道的民族性(张爱玲语),收录九部短篇小说,还原一百年前北方农村集镇的传奇人物与古老事件,无不是震慑心魂的悲剧,却比鲁迅先生多了谦冲温和的淑世精神。
3、 阿城专文赏读——从《诗经》到《金瓶梅词话》,从汪曾祺、李劼人到朱西甯,《铁浆》接续自然主义的文学传统,是现代汉语文学中强悍的代表作。
“胭脂的化石,泪的化石,一个古老的世界,一点点的永恒;依样照出一个朦胧的现代,和后世”。
《铁浆》是台湾文学家朱西甯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九部短篇经典,首次在大陆出版。作品写于台湾的六〇年代,接续五四的白话小说传统,还原民国初年北方农村集镇的传奇人物与古老事件。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冲突的时刻,乡土成为勘探人性善恶的舞台:争盐运生意而灌下铁浆自戕的孟昭有、在酒楼上吃炒人心的屠夫傅二畜、自学医书而接连害死家人的能爷……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人物复活了战国时代的血性,和我们不大知道的民族性,演绎着仇杀与救赎、侠义与温情,愚昧与文明,无不是震慑心魂的悲剧。阿城先生作跋:《铁浆》是现代汉语文学中强悍的代表作。
《刽子手》(节选)
盘子里五味俱全的炒心片儿,就这样静静地听让围着它的家伙是是非非着。
“大师父,”买锅的伙计提着炒过人心的新锅子问道,“摔啦?”摔锅对于顾客是个交代,对于这个贪玩的伙计则是件很有趣的消遣——公然地带点儿挥霍却不必疼惜的快意。他提到门前,摔在大街的青石板上,意外的那锅子没有料想的那么粉碎,于是捡起来,又作了一次消遣。
尤胖子回转脸来 :“大伙儿都传着,这汉子是冤枉了。”
从肩膀上抽下手巾擦了擦油腻的鼻子。那鼻头红红的,把人弄成很伤心的样子。
“也难说。”年轻的士子老是有什么顾忌似的,不敢苟同死者是冤枉的。
杨五道 :“俗语说是 :杀人偿命。更别说杀的是个乡董!试问,哪个乡董老爷不是有财有势的地头蛇?你说我这话呢?”瘦脸送到青年士子的脸上,仿佛征询后者有否异议。
因为座中只有这么一个乡下来的,知道实情。后者却像受了栽诬似的道 :“说是那样说,也不罕定,就拿舍下说,家祖父就……”
“都没好的,我说!”傅二畜是有意扫农家士子的兴了,
“就说我家小孩子他三姨呗,吃尽了乡董的讹诈。你到县里来喊冤告状嘛,娘的个 × !官官相护!就说今天这个死者呗,亲娘让人打死了,报仇杀人是不错,可人家提着血刀来投案啦!还判人家砍脑袋?王法离了皇城就另个样了。说起来不错似的,乡董老爷—也是一乡之主,掌管的也是王法。可那是幌子!不来钱儿,谁干?就说他娘的我这份差事呗,朝廷不给粮饷养活我这一大家人家,我傅二畜疯了?我砍了二十年的人头?还招徒弟传手艺?啊?”也不知是质问谁的,两眼睛瞪着盘子里的菜肴,一直这么追问下去。那神情仿佛要找盘子里剁得那么碎的心给他评评理,又像是说 :“这一大盘子菜,我还没动几筷,怎么就完了?这是谁偷嘴的?谁这么下三儿?啊?”最后把筷子啪的一声放下了。
瘦老头却道 :“来钱儿呢,不错的。不过听说那位挨杀了的乡董,这次可并没捞着钱。”
“那—这条命是白贴了?”掌锅的很感兴趣。
“也说不上那个,话得说远了,当初是两家地邻闹事儿,一家是今儿出决的这个囚犯—”
“姓陆的。他老子在世的时候,是个穷讼师。”年轻的士子一旁下注脚,“那一家姓聂,是个小财主。”
“为着河堤不是吗?”那位跑堂的也知道一点。
“就为的是河堤,弄得出了人命案子。”杨五道,“河堤原从那位小财主聂家地里起土,可聂家硬把河堤歪到人家姓陆的田里。听说聂家儿子是给县大老爷递干帖子的,这里头就有文章。那位乡董出面调停,怎么说也得买买父母官的账,你说这话可是?啊?胖爷?”
“这么一说,倒是有个影儿;他乡董出来调停,少不得偏向着县老爷门下的干少爷。”
“着啊!”杨五拍了下桌子,“当初钦差大人领的人,划的河堤,也没挡住这位干亲家找到堂上,又私下里往西弯了十弓子地。他乡董有濞子也不能冲着堂上擤,不是吗?”
“所以啦,这话又说回来。”年轻士子道,“他陆家孤儿寡妇的,武大郎挑空挑子——人没人,货没货,还跟人家聂家碰个什么劲儿!依我说,哪儿不是忍口气就过去了!”
“这口气不是好忍的,小老弟,人家那是陵地啊!”瘦老头把袖子卷得更高了,好像又出了一个新的不平让他们来打了。年轻的读书人却道:“也难说。这位县太爷的干亲家,家里头—不说挂千顷牌罢,总是个殷实户,照说也不在乎河堤占去的那点儿田地,别的不说,就是赶集的人畜牲口硬踩也踩出那么宽的路。可是人家请来阴阳先生把那块地来回走了三四遭儿,怎么看,怎么不宜动土。各人家的土脉风水,不能不让着,老先生你说呢?”傅二畜抢过去道:“这叫啥话?他县太爷干亲家护风水,人家姓陆的地里就没风水?人家姓陆的娘儿俩就全靠那点田地收成的呗!”
“还不光止这个,二爷!”杨五手指骨节敲着桌子道,“仗着给县大老爷递过干帖子,这就不得了啦?讹了人家田产,还打死了人?”
“二位光景还不大清楚这里边详情。”农家士子说,“也不是讹诈陆寡妇田地;开河堤的事儿吆呼一两年了,到钦差领着人下来量地,也才把河堤划定。这一划可就把聂家西边地头给划进去了。看风水的说什么呢?说是马头上万万动不得土,若是犯了忌,小则家畜不利,大则人口不宁。姓聂的跟陆寡妇两家是地邻,中间隔着土垄子—那是公地—河堤往西弯一点呢,也占不了陆寡妇多少田,聂家也言明占多少地,给多少钱……”
“可那是人家祖陵哪!人家那里头葬着祖宗骨殖呀!谁个为子孙的,这点不护喏?”瘦老头的袖子再卷就要卷到肩膀上了。其实傅二畜就知道,他杨家的祖陵是让他五老头这个贤孝子孙一夜之间押给人,抵了赌账的。不过也许正为着那个,瘦老头痛定思痛,才分外着重一个人家的陵地。
……
多年前收到您一封信,所说的背包里带着我的书的话,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在流徙中常引以自慰。……《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的错过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欢《新坟》。——张爱玲致朱西甯
朱西甯是台湾的一个文化界奇人,因为在中国现代作家之中,很少有像他这样,把基督教义及中国传统两者都看得这般认真。——夏志清
朱西宁的《铁浆》,我认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主题宏大: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形式完整:以象征手法,干净严谨的文字,将主题意义表达得天衣无缝。这真是一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杰作。——白先勇
居然在台湾发现了鲁迅与吴组缃的传人。——刘大任
朱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写出来这样优秀的作品,可惜我读得太晚。若能早些读到他这几本书,我的《檀香刑》将更加丰富,甚至会是另外一番气象……——莫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喷薄,现在想起来还是不可思议。但是总结下来,还是有一层膜,几十年形成的膜,借用文物贩子的行话,有一层“包浆”。包浆也是种积累,积累的却是灰尘,痰涎,粘秽。以前过年之前,家家户户是要用热碱水将器物擦洗干净的,对包浆毫不痛惜。相比之下,在我看来,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是能穿透包浆看到的透明。另一个奇迹是李娟的写作,没有包浆的写作。我要说的是,这之前,朱西甯先生的写作,早已是透明,而且是以没有包浆的状态来写包浆。再之前,是沈从文先生的写作。汪曾祺当年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先生的班上,写成习作《老鲁》,沈先生认可,推荐出去发表。现实是有包浆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自然是对包浆与透明的担当。——阿城
我以为朱西甯*大的成就,在于使他的乡土成为探勘人性善恶风景的舞台。朱西甯的小说可以上接鲁迅,乃至三、四〇年代沈从文、吴组缃等人的原乡视野;而下接王祯和、黄春明的本土情怀……甚至对照八〇年代大陆寻根作家,从郑万隆到贾平凹,从莫言到刘恒……实为寻根作家亟应寻回的海外根源之一。——王德威
朱老师从来就不是素人式的小说书写者,他的文学自觉和文学教养源于五四和三○年代,推动他小说书写的并非怀乡式的慰藉,而是文学自有的书写传统。一生温柔事事留余地的老师,他血气*盛的小说反倒是被视为怀乡之作的“铁浆时期”,我们并没看到游子美化故乡、遍地传奇且人人良善的典型追忆,相反的,这几篇小说无一不是令人震慑的悲剧,用深浓墨黑的笔调刻画不仁的天地和其中的人们,大致已是当时政治力所能容忍限度的强烈概念性批判;老师一辈子倾慕张爱玲、谈张爱玲,但刘大任讲得对,老师的小说,尤其是“铁浆时期”,却是鲁迅的。——唐诺
这就是他,写过吞吃铁浆而争霸道的民族灵性,写过为生存而助恶的民族弱质,写过横扫中原的战乱腥风。我总认为他是个刚烈汉子,至少是见过太多流血和残酷的硬心人。可是,此刻坐在我身旁,却是睿智、自然,而令我倾服的是他的安宁慈祥: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世上尚存极少数极少数的大慈悲者,是我多少年来都在苦苦寻找的那种人。——虹影
朱家成为文坛著名的文学巴赫家庭,成为文坛的美谈。朱西甯更以古代书院的授徒方式,培养了更多的文艺幼苗,他这方面的贡献极大。——痖弦
八〇年代以后,父亲与其作为小说创作者,他选择了去做一名供养人。敦煌壁画里一列列擎花持宝的供养人,妙目天然。父亲供养“三三”,供养胡兰成的讲学,供养自个儿念兹在兹的福音中国化,供养他认为创作能量已经超过他了的两个小说同业兼女儿——朱天文
我有一点愿意……我们读《红楼梦》,可以知道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如果我们把当代人生活细微地留下来,让后代子孙知道祖先们曾在这片土地上怎样地生活,也许就很够意思了。我们再不写,这些二三十年前的东西也就丢掉了。——朱西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