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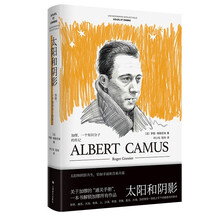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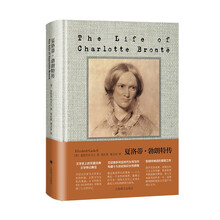






纪念托马斯·曼诞辰150周年、逝世70周年,
中文世界首译插图版“曼的前半生”
曼的前半生是一条逆袭之路,作为现代德国文学史上的“头号丑小鸭,他经历了从后进生、留级生、肄业生、大学旁听到大作家、大部头作家和大学问家的巨大转变。鉴于他对自我的兴趣超出常人,热衷于分析和谈论自我,这些非虚构文字可供我们一窥有关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的答案,把它们与他的非虚构文字进行比对,有助于我们了解真实而完整的托马斯·曼。
《我的人生速写》是托马斯·曼的一部自传,是托马斯·曼对自己前半生人生轨迹的概述。最早于1930年以“Lebensabriss”为名发表在德国费舍尔出版社旗下的Neue Rundscbau杂志上——就在前一年,曼刚刚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后经H.T. Lowe-Porter译成英文,英文版图书先后由巴黎哈里森出版社、美国克诺夫出版社出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把它看作曼向公众展示“诺奖作家是怎样炼成的”第一手资料。自传基本上按时间顺序,以曼的写作为核心展开,由曼娓娓道来他的前半生:在吕贝克度过美好散漫的童年时光,在卡塔林恩学校度日如年,毕业后在保险公司摸鱼搞创作,被举报离职后跟哥哥海因里希奔赴罗马,并着手创作《布登勃洛克一家》,小说大获成功后成为上层知识分子圈子的座上宾,在某次聚会上邂逅犹太富商之女,与她结婚并陆续育有六子,两个妹妹相继自杀,跟家人去威尼斯度假时创作了《死于威尼斯》,根据妻子在达沃斯疗养院治病的亲身经历创作了《魔山》,与哥哥因为一战立场不同失和,在1929年欧洲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最后以即将到来的埃及和巴勒斯坦之旅收尾。
对于生活,我始终抱着一种懒散的态度,缺乏一些公民应有的责任感,但我坚信自己身上有着未被发掘的潜能。
多亏了他们,我才真正领略到了友谊的快乐,这是我先前从未体验过的:他们温柔而巧妙地化解了我心头的重负、羞涩和易怒,坦率地接受了我的这些性格,把它们当作我身上令他们推崇的天赋的附属品。那段日子对我而言弥足珍贵。
我也不会忽视在我现在这个年纪,阅读给我带来的那些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我指的是叔本华和尼采带给我的感受。或许,我最初得以见刊的散文作品,在思想和风格上显然都深受尼采的影响。
与尼采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一个仍处于智识形成阶段的人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要想改变我们的本质,把我们塑造成截然不同的个体,依靠任何文化力量都是无法做到的;文化成长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必须预设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必须具备本能的意志和能力,能够做出个人选择、吸收所接受的东西并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其特殊需要。歌德说,要有所为,必须有所是。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要想有所学,也必须有所是。
在二十岁时,我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位伟大道德家的“不道德主义”的相对性。我目睹了他对基督教的憎恨,同时看到他对帕斯卡尔的兄弟般的爱,也就能理解他这种出于道德而非心理的仇恨。
简而言之,我在尼采身上看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战胜自我。我没有把他的话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而且我几乎完全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但这也恰恰使我对他的热爱有了双重层面的含义——换句话说,这也赋予了这种热爱更多的层次和深度。
托尼奥•克勒格尔说,有一种东西叫做“知识的病”。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我年轻时的病态。
但突然有一天,我终于决定去读一读,于是我夜以继日地阅读,那种感觉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当然,我之所以这么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用强有力的智识和道德,否定了生命和世界,而这种否定又隐藏于一种可以和我内心深处产生共鸣的思想体系之中。但我的喜爱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陶醉,它与新生的、勃发的性息息相关,更偏向于激情和神秘主义,而非哲学。我并不关心“智慧”,也不关心他那种通过转变意志来救赎的理论——对我来说,这种苦行僧式的佛教附属品,除了引起批判和论战之外毫无价值。我真正关心的是,这种哲学中的色情主义和神秘统一元素,它以一种感性和超感性的方式吸引着我——这种元素也使我对《特里斯坦》禁欲主义音乐的理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时,我在情感上接近崩溃,甚至想过自杀,但我还是意识到自杀绝非“明智之举”。
啊,青春真是充满各种强烈的情感和冲动,有时感觉一切都乱糟糟的!
军营嘈杂的环境、无所事事的苦闷以及强制要求整理内务的铁律,都让我备受煎熬。
托马斯·曼以坦率而优雅的笔触,回顾了一位孤独的青年如何成名于世、成名之后如何获得个人幸福,以及一个艺术家在时代召唤与个人命运之间的思考与抉择。——亚马逊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