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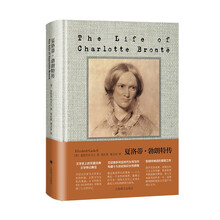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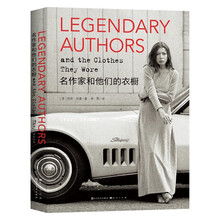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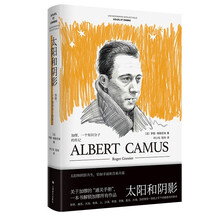

1.一本书讲透大文豪苏轼与弟弟苏辙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传奇人生。
2.资深传记作家纪云裳新作,用诗意的语言深情解读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与诗词创作,还原真实、立体的二苏形象。
3.赠送苏轼与苏辙的人生轨迹图,生动展示文坛双子星的重要人生切面。
4.封面及装帧设计精美,独具匠心,内文版式大方,阅读不伤眼。
5.苏轼乐观通透,苏辙沉稳靠谱,兄弟二人虽性格不同,但在人生中互相激励、相互扶持,读者也能从中获得启迪。
苏轼和苏辙是亲兄弟,一个是为人熟知的乐天派诗人,一个是高登庙堂的政治家。苏轼只比苏辙大两岁,他们少时共读、青年同仕、中年扶持、暮年投老,既是兄弟,也是知己,一生相知相勉、手足情深。
《宋史》中这样评价兄弟二人:“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苏轼一生不是被流放就是在被流放的路上, 苏辙一生不是在救哥哥就是在救哥哥的路上。
苏轼的仕途坎坷,被卷入“乌台诗案”,锒铛下狱。弟弟苏辙在南京做官,冒死给皇帝写信求情,愿意用自己的官职换哥哥一命。
苏轼去世时,回望一生,悔恨的不是一身才华无处施展,而是临死前没能见到弟弟最后一面。
人生起起落落,他们携手同行。
与君世世为兄弟
元丰二年(公元 1079 年)十月,苏轼在御史台监狱里写下《狱中寄子由二首》时,他曾以为,那是他生命中的绝笔,以为自己与苏辙的缘分尽了,与人世的缘分也尽了。
御史台,又称乌台,因四周种满柏树,树上栖满乌鸦而得名。
关押苏轼的牢房,是一口百尺深井,井底阴冷潮湿,一举一动都会触碰到墙壁,就像一个微小的地狱。
阳光好的时候,井口会漏下一束巨大的光柱,无数浮尘游动其间,让人想到人生如蜉蝣,过往历历在目。
这一年春,苏轼收到了调任湖州的诏书:“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
去湖州,是他自己争取的。徐州任期将满时,他写了好几封信到汴京,让朝中的老友们帮忙斡旋,说他实在不想回京,如果可以调到江淮之间就更好了。
但诏书到来的那一刻,对徐州的不舍还是盖过了求仁得仁的喜悦。临行前,徐州父老夹道相送,扯着他的马镫不让他走,惹得他泣涕如雨。
他那浪漫多情的诗人本质也从官员的身份里跳脱了出来,在词中写道:“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三月底,苏轼从徐州出发,四月二十日到达湖州,中间还到南京与苏辙相聚了半个月,两兄弟一起拜访了张方平。
这一次的同行者除家眷外,还有一对叫作王适、王遹的兄弟。王氏兄弟是徐州官宦之后,仰慕苏轼声名已久,便跟随苏轼学习作文。苏轼特别喜欢王适,说对方“喜怒不见,得丧若一”,有苏辙少年时的风采。后来王适成了苏辙的女婿。
路过高邮时,秦观追随而来,大家一起欣赏沿途风光,心情都很不错。
在无锡惠山,诗僧参寥作陪,苏轼与亲友们以山泉烹茶,看白鹤飞过青山,闻茶盏里尘世之外的香气,内心觉得十分满足。他在《游惠山》里记录了那段美好的回忆:“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眠食耳,一饱万想灭。”
到湖州后,苏轼又找到了昔日在杭州当通判的感觉。再次回归生命的中隐状态,尽情享受湖山之美,友情之美,远离朝堂,在地方做一个合格的官员。虽然与当初致君尧舜的理想有所差距,但想着就这般诗酒度日,终老江南,也算是弥补了一些遗憾。
可到底是低估了人性的恶。
这一年六月,京城已有风声传来。有人检举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对皇帝不敬:“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难道朝堂上的新进官员都是惹是生非之辈?这不是讽刺皇帝无能吗?
苏轼不以为然,心想不过是小人故技重施罢了。
数年前,也是在江南,一位叫沈括的官员以故友的身份找到苏轼,让苏轼送他一本诗集,怎知他一回到京城,就将诗集呈给了皇帝,检举苏轼在诗中讽刺新法,愚弄朝廷。不过沈括没有想到,皇帝竟对苏轼的诗集爱不释手。
所以苏轼听说又有人检举他的时候,他还开玩笑说自己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当然那句话的背后是他对皇帝判断力的高度信任。
但这一次,朝堂政局几经变幻,王安石离去后,变法派的核心人物已经换成了宰相王珪和御史中丞李定。在他们眼里,苏轼虽不在京城,文名却如日中天,皇帝喜爱他,百姓拥戴他,读书人崇拜他,他随时都可能被任职高位,司马光也随时可能回朝当政。他们要打击苏轼,让苏轼背负杀头的重罪,更要让整个保守派元气大伤。
很快,第二份、第三份检举状又送到了皇帝的手中。
那些苏轼在杭州为农民写下的诗句,再一次成了所谓的罪证——“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这是要挑起民怨,让百姓痛恨新法;《灵璧张氏园亭记》中“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则是乱取士之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
最后,李定在第四份检举状中向皇帝指出,苏轼至少犯有四项杀头大罪,都属于“大不恭”:不悔其过,狂悖自大,伤教败俗,蛊惑民心——在民间,人人都会背苏轼的诗词。
皇帝的脸色渐渐变了,随即下了一道圣旨,让御史台查明此事。
御史是连夜出发的。据当地百姓说,御史对苏轼的态度很粗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路过扬子江时,因不堪侮辱,苏轼一度想投江,是苏迈拉住了他。苏迈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苏家其他人则由王氏兄弟护送,仓皇投奔苏辙,路上遇到官兵搜查,王闰之崩溃大哭,烧掉了丈夫许多诗稿。
苏轼心知肚明,那些人就是想让沿途的百姓看一看,昔日的文章太守沦为阶下囚的样子,所谓“乌台诗案”,也不过是儒家礼法再一次被政治与野心利用。
打击苏轼,他们用的是“不恭”,就像昔日嵇康含冤入狱,罪名用的是“不孝”。嵇康是在闹市被处死的。古代行刑又称 “弃市”,选择闹市,即“天子与臣民共弃之”,可见对欲置他们于死地的人来说,杀人不够,还要诛心。
苏轼长叹一声,流下了悲伤的泪水。
他又想起御史到湖州来之前,七月初七那天,阳光大好,他在院子里晒书画,看到朋友文同赠给他的《筼筜谷偃竹》,突然悲从中来,失声痛哭。
当时文同去世已有半年了。文同最擅画竹,人称“胸有成竹”,性格也是虚怀若谷,清正不阿,却奈何生前处处遭人排挤,死后家中清贫,妻儿竟无力扶柩还乡。
直到去汴京的路上,苏轼才明白,原来那一日的眼泪,是为文同而流,也是为自己而流。
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没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
——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节选)
苏辙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得知苏轼被捕后,苏辙忧心如焚,连夜上疏宋神宗,为兄长求情。
苏辙先是动之以情,写自己与兄长相依为命,手足情深,自兄长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
再表明苏轼性格狂狷,虽言谈有失,但已悔过自新:“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不可救止。”
然后转述苏轼被捕时的留言。苏轼认为自己必死无疑,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
最后引出“缇萦救父”的典故——汉文帝时期,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女缇萦随父至长安,请入身为官婢以赎父罪,借以表达他也愿意用自己的官职,来赎兄长的死罪。
然而苏辙的上疏并未收到任何回音。
宋神宗自然知道苏轼的狂狷,他就是有意要治一治这匹 “野马”。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关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受尽凌辱。
御史们对他通宵辱骂,软硬兼施,试图在他身上找出更多与保守派有关的“罪证”。
苏轼自始至终只承认自己写了讽刺新法的诗。
他把一粒毒药埋在牢房里,但终究没有吃下去。
那么在幽暗的深井之中,在那些痛苦的、屈辱的、孤寒的漫漫长夜里,是什么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熬下去呢?
在寒凉的秋夜,他写御史台的榆树,笔下还透露着坚韧与希望:“谁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风至,飞英覆空屋。”
或许是儿子苏迈送来的每一餐热饭,是狱卒梁成为他打的洗脚水,是与苏辙“风雨对床”的心灵契约,是对家人们的牵挂,是亲友为他求情的消息,也是身处深渊依旧仰望星空的士大夫风骨。
直到有一天,苏轼打开食盒,双手忍不住颤抖起来。
食盒里是一条鱼。
他不知道,那天送饭的并不是苏迈。
他们父子之间有一个“平安蔬菜杀头鱼”的暗号。但那天苏迈要出城借钱,便托亲戚去给父亲送饭,送鱼,只是巧合而已。
那顿饭,苏轼一口都没有吃。
寒鸦在柏树上不断盘旋,叫声格外凄厉,他枯坐了许久,依旧抓不住笔杆。末了,他还是写了两首绝命诗,拜托狱卒梁成交给苏辙。
雪泥鸿爪 001
世间所有的名字都不是秘密 013
有风来自少年时 027
出四川记 045
四海一子由 059
两地书 077
彩云易散 097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111
我兄东南游,我亦梦中去 129
寂寞山城 149
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165
与君世世为兄弟 185
千里快哉风 201
双璧 229
倾杯不能饮,留待卯君来 245
人生如逆旅 263
不系之舟 279
手足之爱,平生一人 297
参考文献 321
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宋史·苏辙传》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清]张鹏翮
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清]蔡嵩云《柯亭词论》
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宋]苏轼《答张文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