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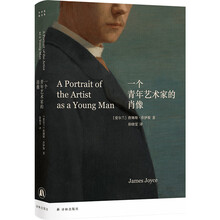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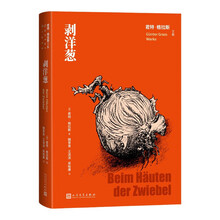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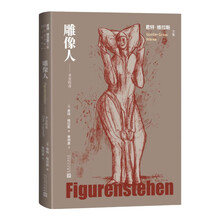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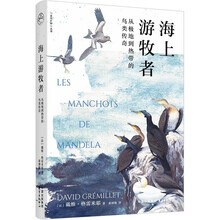

巴斯妇向我们展示了文学形式和活生生的生活经验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艾莉森既不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中世纪女性,也不是一个完全由文本刻板印象构造的人物。我们想象她,就需要考虑表征与现实之间的棘手关系,还要考虑有关女性的看法和意识形态观念如何影响社会中真实女性的待遇——反之亦然。正如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所写的那样:“人类的行为并不是以真实的事件和环境为导向,而是基于他们对这些事件和环境的印象。”艾莉森作为一个角色,在被创造的过程中,经验和权威发生了冲突,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一探艾莉森自己是如何生动地暗示那些书上有关女性的观念与家暴中的身体体验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直到《巴斯妇的引子》的第635行,那本“恶妻之书”(the“book of wikked wyves”,685行)才第一次出现,当时,艾莉森在向我们讲述她那暴力、厌女、年轻的第五任丈夫。艾莉森简要地讲述了詹金(Jankyn)因为她撕掉他书中的一页而揍了她,并且那一击让她耳朵聋了(634—636行)。接着,她又补充了一些细节:她在婚后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她丈夫会向她宣讲罗马的婚姻、《圣经》故事和各种谚语(637—665行)。当艾莉森讲述书中的压迫性内容——哲罗姆、德尔图良(Tertullian)和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666—681行)撰写的反女性、反婚姻的短文——时,这本书就成了焦点。詹金沉迷于书中的厌女书写,并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他“为了消遣”而“高兴地”阅读它,在阅读时也总是捧腹大笑。他一有“闲暇”(669、670、672、683行),就总会阅读它。说到此处,艾莉森岔开话题,发表了她关于制度性厌女和经典(canon)的偏见的著名演说(688—696行),质问众人“是谁画的狮子?”(692行)并以此指出艺术是带有偏见的——人类讲述的故事与狮子讲述的故事可能会截然不同,正如男人与女人看待生活的方式完全不同。而女人,像狮子一样,根本没有机会去书写故事。如果她们能写,艾莉森说,她们将会写尽男人的所有邪恶(693—696行)。艾莉森声称,在教堂执事们年老体衰时,他们就会坐下来写下各种有关女性的可怕故事(707—710行)。说完,艾莉森再次回到她自己的故事中,接着讲述詹金是如何每天晚上坐着大声朗读那些针对女性的充满侮辱性和攻击性的故事(711—785行)。最终,当她看到他没完没了地读下去时,她撕下了三页书并一拳打在他脸上,他向后跌入壁炉中(788—793行)。接着,他气急败坏地跳起来,朝着她的头狠命暴击,她被打得躺倒在地,仿佛死了一样——而且,她确实被这一击打聋了(794—796行)。
尽管这本书在《引子》的后半部分才出现,而且也是比较晚才出现在艾莉森的生活中,但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是,她本人也是由这类书的刻板印象构建而成,这些书往往聚焦于艾莉森乐于展示的许多品质(她爱八卦!她喝酒!她告诉别人她丈夫的秘密!她在前夫的葬礼上寻觅下一任丈夫!)。在某种程度上,她简直是这本书的前身(avant la lettre)。同样清楚的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她在根据哲罗姆等男性的论点来构建自己的论点。那本“恶妻之书”不是詹金的某本书,而是反女权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它压迫的既是书中的女性角色,也是真实存在的女性。正如艾莉森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笔杆子一直牢牢掌握在男人而非女人手中,所以,不管是在文学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没有一个合乎情理的女性榜样。而艾莉森自己,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形象,也是由男性的刻板印象塑造的。中世纪的反女权主义者可能会说,她的存在证明了他们对女性的看法是多么正确;而一些现代女权主义者会同意,乔叟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她的声音,是为了展示女性固有的不足之处。但是,当她在一个元文本的时刻(metatextual moment)宣布自己意识到经典的局限性时,她便跳出了这些刻板印象的桎梏——在这个时刻,她摒弃了哲罗姆或让·德·默恩等人的文本,而是用了一个寓言故事(是谁画的狮子?)。詹金和艾莉森一起坐在火炉旁,阅读着一份“装订成一册”(681行)的文本手稿,这幅画面为整个场景注入了另一种中世纪晚期的“现实主义”格调。换句话说,它鼓励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场景会是什么样子:真有一个女人坐在那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听着那些关于女人的可怕故事。在用七十行的篇幅描述了詹金的厌女言论之后,艾莉森直截了当地说道:“谁能体会,或者谁能想象一下 / 想象我的内心有多么痛苦和悲哀呢?”(786—787行)这便是听到残酷无情的厌女言辞的感受——难以想象,无法言说。也正是在这个文本人物描述她的记忆和情感的时刻,她邀请读者进入她的内心世界,试着想象成为她会是什么感受。艾莉森和她的文本远不是反女权主义刻板印象的体现,在此,她实则鼓励我们要去批判那些厌女的原始资料,并去思考和想象个体的经历,而非盲从官方权威。
至关重要且令人不安的一点是,这本书成了暴力的导火索。艾莉森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因为一本书而被揍了”(712行)。于是,生活与文本、历史与文学在这里交织在了一起。如果我们假设文本与生活(即权威与经验)可以完全分离,文学中的刻板印象与生活现实完全没有关联,那我们可能就会忽视一种暴力,而恰恰是因为人们在书中读到了某些内容,这些暴力才会被施加于身体。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写,女性在生活中被对待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受到冯·X 教授(Professor von X)的幽灵的影响,是他“撰写了那本题为《论女性在精神、道德和身体上的劣等性》(The Mental,Moral and Physical Inferiority of the Female Sex)的巨著”。巴斯妇的故事有很多内涵,其中之一是中世纪女性的现实经历与攻击女性的厌女文本之间的不协调,后者对女性的正常行为(例如再婚)大加挞伐。这些关于恶妻的书是真实存在的中世纪书籍,即厌女文本的汇编,而乔叟一定接触过。艾莉森在描述这本书时,她首先提到了瓦莱里乌斯(Valerius)、泰奥弗拉斯托斯和哲罗姆的三部著作。经鉴定现存的 35 份手稿要么包含哲罗姆的《驳约维尼安》(Adversus Jovinianum)外加瓦莱里乌斯或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作品,要么包含全部三者的作品,其中包含全部三者的有11份。对于真实的中世纪寡妇而言,就算她们的行为完全正常,甚至实际上也受到社会鼓励,但仍然不得不与千百般侮辱她们的书籍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