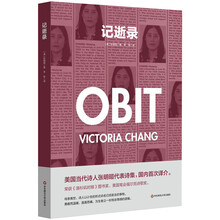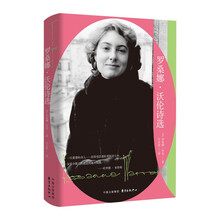离开酒店时正在下雨,蒙蒙细雨,十月的东京时常会下的那种雨。我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远——只要走到昨天来时的地铁站,再坐两趟地铁,沿着小街走一会儿就能到达博物馆。我拿出雨伞撑开,拉高外套拉链。清晨的街道,行人络绎不绝,大多都从地铁站出来,不像我们,是向那里走去。母亲一直紧跟着我,仿佛我们一旦分开,这如潮的人流会把我们越推越远,再也无法回到彼此身边。烟雨霏霏,绵绵不绝。地上汪出一层湿漉漉的水雾。细细一看,路也不是柏油路,而是由一块块小方砖铺成的砖路。
我们是昨晚到的。我的飞机比母亲的早到一小时,我就在机场等她。太累看不进书,我拿了行李,买了两张机场快线车票、一瓶水,还从删机上取了点现金。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要买点别的,比如茶啊,吃的什么,不确定她下机后的心绪。她从出口出来,虽然隔得很远,看不清她的脸,但她举手投足的姿态,或者说步态,让我一眼就认出了她。走近了,我注意到她的穿着打扮依旧得体考究:珍珠扣棕色衬衫、烫得笔挺的长裤和小件玉饰。正如她一贯的穿衣风格:衣服都不贵,但都是精挑细选的,剪裁合身,搭配巧妙,质地精良,看起来就像二三十年前电影里那种精雕细琢的女人,优雅却过时。她还带了那只大箱子,我从小时候记到现在。她把箱子塞在衣柜最上面,森森然罩在我们头顶,大多数时候就这样束之高阁,用到的机会屈指可数,直到父亲和兄长相继过世,回香港奔丧才拿下来。箱子上一块污迹都没有,现在看上去还像新的一样。
年初我让她和我一起去日本旅行。我们住在不同城市。我成年后,母女二人从未相伴出行过,我开始意识到这很重要,虽然理由还说不明白。一开始,她很不情愿,经过我一再劝说,最后终于答应下来,也不是那种言之凿凿的应承,只是慢慢地,她反对得越来越少,每次我在电话里问她,她都在那里犹犹豫豫的,这些迹象表明她终于向我发出了“可行”的信号。选择日本是因为我去过、母亲没去过,我觉得游览另一个亚洲国家会让她更自在些。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去日本旅行会让我俩都变成“外国人”,占据平等地位,获得同等待遇。选择秋天是因为这是我们最喜爱的季节,一年中这个季节的花园和公园最美。深秋之后,一切丧失殆尽。只是,我不曾预料到这季节还有台风。天气预报已经发出几次警告,从昨晚开始雨就没停过。
进入地铁站,我把交通卡给她,穿过闸机。我搜寻地铁路线和站台,努力把站名、颜色和昨晚在地图上做的标记匹配起来。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换乘方式。站台地上清晰标出了排队上车的记号。我们顺从指示候车,等了几分钟后列车进站。车门边有个单人空位,我示意她坐下,我站在她身旁,看着一个个车站飞驰而过。城市如钢筋水泥,灰蒙蒙的,在雨中显得分外阴沉而陌生。我能辨识出高楼、天桥、火车道口的外部轮廓,可它们的细部和内部材料构成上却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而吸引我的正是这些细枝末节又意味深长的变化。约二十分钟后,我们换了辆不那么拥挤的小列车,这次我得以坐在她旁边,注意到建筑物变得越来越矮,直到进入郊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房屋,白墙平顶,车道上停着小轿车。我突然想起上次来这里,我是和劳里在一起,时不时地想起母亲。现在,我和母亲在一起,却时不时地想起他,想起我们从清早到深夜,在城里东奔西走,逛来逛去,观察一切,感受一切。那次旅行,我们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狂热激动,说个不停,笑个不停,永不满足。我想起那时曾想过要和母亲分享这段经历,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在那次旅行后,我开始学习日语,可能潜意识里在规划这次旅行。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