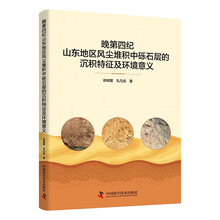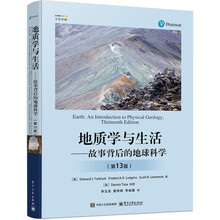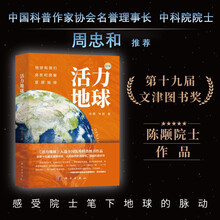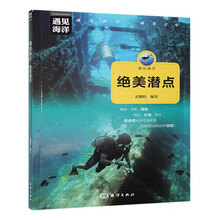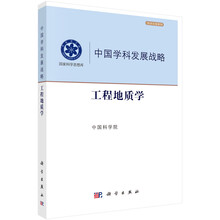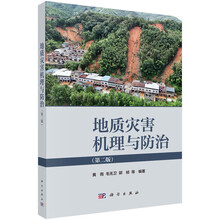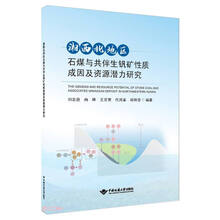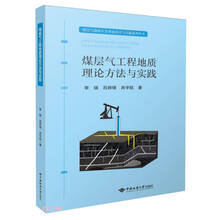第1章 绪论
深层页岩气是我国未来天然气增储上产的战略接替,对开创我国油气勘探开发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至今深层页岩气的资源探明率仍然极低。究其原因,是深层页岩气在地质、工程和地球物理等方面存在比浅层页岩气更加复杂的影响因素,许多科学问题亟待解决。深层页岩气的高效勘探开发,面临诸多理论、方法挑战及工程技术风险。
1.1 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潜力
1.1.1 页岩气
页岩气,英文名为shale gas,是指以吸附或游离状态的形式,赋存于暗色泥页岩或高碳泥页岩中的天然气。
页岩气属于连续生成式非常规天然气,成因类型包括生物成因、热解成因或二者混合成因,成藏机理介于根状气(如煤层气藏)、根缘气(如狭义深盆气藏)和根远气(如常规的背斜圈闭气藏)之间。
按照埋藏深度,页岩气被划分为浅层页岩气、深层页岩气和超深层页岩气等类型。其中,浅层页岩气是指埋藏深度小于3500m的页岩气,深层、超深层页岩气则分别指埋藏深度为3500~4500m和4500~6000m的页岩气。
页岩气的勘探开发,主要包括资源评估、勘探启动、早期开采、成熟开采和产量递减5个阶段,涵盖了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学科,以及测井、钻完井、储层改造、动态监测等技术。
1.1.2 深层页岩气的勘探开发潜力
北美“页岩气革命”的成功,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科技资源,针对页岩气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在深层页岩气领域,有些国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展现出了巨大的勘探开发潜力。
1.国外深层页岩气的勘探开发潜力
早在2005年,北美国家就掀起了页岩气开发热潮,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获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美国,先后建成了巴尼特(Barnett)、马塞勒斯(Marcellus)、尤蒂卡(Utica)、二叠纪(Permian)盆地、伊格尔福特(Eagle Ford)、巴肯(Bakken)、安纳达科(Anadarko)、海恩斯维尔(Haynesville)、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和奈厄布拉勒(Niobrara)等页岩气生产区,使页岩气产量获得了爆炸式的增长,已实现连续多年的高速发展。202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持续增长,在全球页岩气总产量7688×108m3中,美国占95.3%(约7330×108m3,当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为11680×108m3,页岩气占63%),远超当年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页岩气产量(200×108m3)。如图1-1所示,自2007年以来,美国页岩气产量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长;截至2022年5月,美国页岩气产量已接近22.7×108m3/d(约800×108ft3/d),当年总产量超过8000×108m3。当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外,墨西哥、波兰、德国、英国、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等也加强了页岩气勘探和开发。
其实,除了浅层页岩气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外,以美国为代表的页岩气商业开采国家,也极其重视深层页岩气的开发。目前,美国已经在Eagle Ford、Haynesville、迦南-伍德福德(Cana-Woodford)、希利厄德-巴克斯特-曼科斯(Hilliard-Baxter-Mancos)、曼科斯(Mancos)等5个深层页岩气开发区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这些区域,深层页岩储层平均埋深为3600~4648m。其中,Eagle Ford是典型的深层页岩气产区,针对埋深3500~4500m的深层页岩储层实施完钻水平井1976口,占整体气区的31.7%,许多钻井的垂深约4000m,测深超过了7000m;Haynesville深层页岩储层平均埋深3658m,早在2018年深层页岩气的产量就已达到669×108m3,占美国当年页岩气总产量的12%。可见,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潜力极大,是未来储量与产量增长的现实领域,在国外早已备受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2.国内深气层页岩气的勘探开发潜力
我国页岩地层在多个地质时期均有较好发育,在南方、北方、西北和青藏等广大地区广泛分布,既有总有机碳(total organic carbon,TOC)含量高的古生界海相页岩,也有TOC含量丰富的中、新生界陆相页岩。据自然资源部2012年的测算,全国页岩气资源总量极大,除主要分布在四川、鄂尔多斯、渤海湾、松辽、江汉、吐哈、塔里木和准噶尔等含油气盆地外,在我国广泛分布的海相页岩地层、海陆交互相页岩地层及陆相煤系地层也都有分布。其中,川南、川东、渝东南、黔北、鄂西等上扬子地区是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的主要远景区。
10余年来,我国针对页岩气领域加强了科技攻关,页岩气勘探开发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2013~2018年,我国用了6年时间使页岩气产量突破100×108m3。至2021年底,已建成页岩气田8个,探明页岩气储量2.74×1012m3;2022年页岩气产量持续增长,达到240×108m3。预计2025年,中国天然气产量将达到2500×108m3,而页岩气年产量将超过400×108m3。未来,页岩气将成为我国天然气增长的主要动力。
然而,目前我国页岩气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来自涪陵、威远等四川盆地及周缘3500m以浅的上奥陶统五峰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比如,2021年我国页岩气总产量为230×108m3,主要产自位于四川盆地的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和中石油威远、长宁等页岩气田,页岩气产量分别为71.65×108m3和111.7×108m3。我国仅四川盆地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气地质资源就高达21.9×1012m3,其中11.3×1012m3属于深层页岩气,占51%;而川南已落实的10×1012m3资源中,深层页岩气占比高达87%。就全中国而言,页岩气地质资源量为123×1012m3,其中深层页岩气地质资源量高达55.45×1012m3,勘探开发潜力巨大。
1.2 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面临的问题与关键技术挑战
尽管深层页岩气具有巨大的勘探开发潜力,但存在页岩气富集规律不清、复杂构造区微幅构造和小断层识别难度大、水体动荡区沉积微相平面刻画难度大等地质难题。同时,在相对比较复杂的页岩气勘探区域,存在地震资料静校正、各向异性处理、精确成像等难题,面临着突出页岩气地震响应特征处理、裂缝检测、含气性识别等“甜点”预测、综合评价、随钻跟踪及井轨迹优化调整等诸多挑战。
1.2.1 面临的地质与工程问题
(1)页岩气富集规律不清,控制产量的决定性因素需要进一步探索。页岩气作为一种连续型非常规气藏,虽然其具有面积大、分布广泛的特点,但若要实现效益开发利用,仍需要寻找资源相对富集的页岩“甜点”区。勘探开发实践表明,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井之间的地质参数、单井产能差异大,页岩气富集规律不清,控制产量的决定性因素需要深入探索。
(2)不同构造区,页岩储层差异大,地质成因需要深化研究。多数页岩气探区的实际钻井揭示,在不同构造单元,页岩储层参数(孔隙度、渗透率、脆性等参数)差异大,规律性差,地质成因不明,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3)水体动荡区,沉积微相刻画难度大,平面展布特征难以精确描述。在某些页岩气探区,受断裂、沉陷等地质活动的影响,水体动荡,加之物源、沉积速率差异性明显,发育泥质深水陆棚、砂泥质深水陆棚、浊积砂、泥质浅水陆棚、砂泥质浅水陆棚等多种沉积微相,且具有纵横向快速变化的特点,如果钻井较少,沉积微相平面展布特征难以精确描述。
(4)现今地应力与古地应力的演化机理欠清晰,制约了对地质现象的科学判断。古地应力、古地貌演化、构造演化、保存条件、成藏过程等差异,与勘探开发效果密切相关。现今地应力是古地应力的演化残余,与微幅构造、断裂与裂缝的分布等密切相关,尤其对裂缝和渗透性比较敏感。与浅层相比,深层页岩储层受地应力影响更大,应力差异更显著,地应力演化机理认识难度更大,导致微褶皱、破碎带、小断裂、微裂缝的空间分布及断裂与孔隙连通性等复杂地质特征难以科学判断。
(5)超致密储层渗透机理研究欠透彻,制约了对深层页岩储层品质的客观评价。渗透率受孔隙与裂缝发育程度、开启程度、连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又受沉积环境、岩性、压实作用、流体黏滞性、孔隙压力、地应力状态等制约。可见,深层页岩储层的渗透性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响应。与浅层相比,深层页岩储层沉积环境更复杂,压实程度更高,致密程度更高,孔隙发育更差,渗透性更差。渗透率的敏感特性、影响因素和渗流机理研究不透彻,不利于深层页岩储层的客观评价和高产富集目标的发现。
(6)各向异性介质理论研究欠深化,影响深层地质目标的精细分析及勘探开发。在岩石颗粒的定向排列、沉积环境、构造演化等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储层地应力的大小与方向、渗透率的矢量特征、流体的空间分布等往往呈现出各向异性。与浅层相比,深层页岩储层岩心取样难度大,对成熟度、TOC含量、含气量、矿物组分、岩石物理性质、力学性质及其关联特征的认识程度不深刻,仅基于各向同性介质、均匀介质等理论,难以厘清岩性、渗透性、地应力、层理与天然裂缝、孔隙、流体、孔隙压力等与储层各向异性之间的关系,影响对深层页岩储层的全面认识,必然影响勘探开发成功率。
(7)深层页岩储层研磨性和可钻性理论研究欠完善,影响高效施工。深层页岩气开发过程中,将遭遇高温、高压、高地应力等复杂环境,储层横向非均质性显著,压实程度高,抗张、抗剪和抗压能力强。如何克服井塌、井垮、井漏等工程问题,提升钻井与完井效率,需要深化研究储层地质力学理论,科学评判深层页岩储层的工程品质。
(8)深层页岩储层有效体积改造理论欠完善,掣肘单井产量和*终可采储量(estimated ultimate recovery,EUR)。深层页岩储层脆性差,韧性高,破裂压力与裂缝闭合应力高。通过压裂改造提升储层渗透能力的过程中,水力裂缝的延展受控于天然裂缝,压裂液容易滤失增加,裂缝宽度变窄,支撑剂运移受阻,导致加砂困难和压力陡升,容易产生导管变形、损坏等工程事故。需要深化复杂缝网扩展机理研究,改进渗透机制,完善储层有效改造体积(effective stimulated reservoir volume,ESRV)理论,使深层页岩气充分解吸和高速自由运移,才能大幅提升单井产量和*终可采储量。
1.2.2 面临的地球物理问题
1)深层页岩气岩石物理、测井、地震综合研究深度不足
受深层页岩气钻井数量、岩心取样成本等因素制约,针对页岩气开展的岩石物理测试、对比分析、敏感参数规律总结等研究有限,与测井、录井、地震等数据结合研究程度不高,直接影响到页岩含气性、TOC含量、脆性等关键参数的对比分析,难以形成规律性很强的岩石物理-测井综合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岩石物理“根基性”作用和测井“桥梁性”作用的充分发挥,难以有效排除后期地震预测的多解性,不利于提高地球物理综合预测精度。
2)深层页岩气地震资料处理难度大
(1)突出页岩储层地震响应特征难度大。受近地表复杂条件影响,多数探区原始资料噪声较重,尖脉冲、面波、高频干扰尤其发育,这些噪声对反褶积、叠加成像影响较大。不同位置单炮信噪比、能量等有一定差异,主要目的层层间信号较弱,部分有效信号淹没于噪声中。在尽量不损伤有效反射信号的前提下,采用保真度较高的去噪方法,适度压制各类叠前噪声,提高资料的信噪比是地震资料处理的难点与重点。
(2)深层页岩气地震分辨率提高难度大。深层优质页岩储层的埋深超过3500m,地震波传播时高频衰减较快,导致频带收窄。一般情况下,优质储层厚度较薄(几米至十几米),常规技术处理资料很难满足储层识别的要求。在确保目的层高信噪比的前提下,需要尽可能提高分辨率。
(3)局部区域静校正问题难以有效解决。有些深层页岩气探区地表岩性分布较复杂,灰岩、砂岩等岩性出露,采空区低降速带横向变化剧烈,导致了较突出的静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