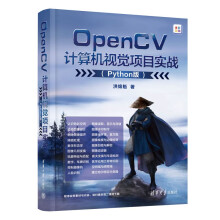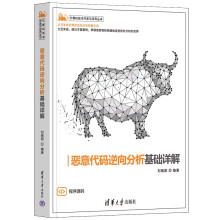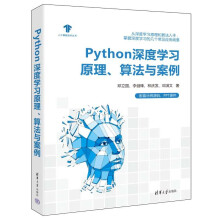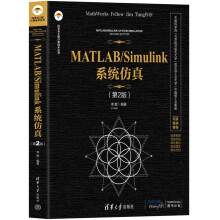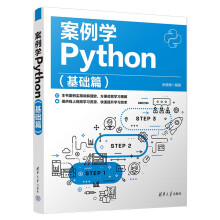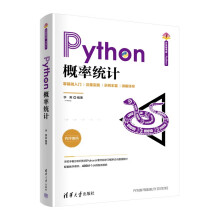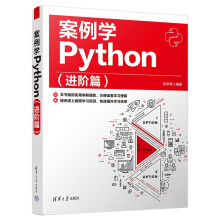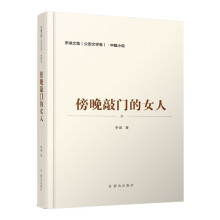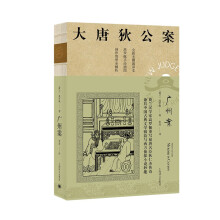01 珍爱生命,追求零糖
既然本书讨论的主题是零糖社交,在进入这个主题的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人类和糖的恩怨情仇的纠葛史。当然,了解这些常识,不是误导我们将一本阐述社交关系的书籍当成一本养生书籍,而是希望能通过糖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延伸和过渡到社交“去糖化”这个主题范畴。
人类对于糖的需求,源于身体的本能需求,就如同生命离不开水。可以说,我们一生与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当我们从母体中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味蕾就可以从母乳以及其他食品中敏锐地感受到甜味。要知道,母乳中有超过40%的能量都是通过乳糖提供,而自然界中水果蕴含的果糖成分,更是让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感受到生命的甜蜜。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番情景:远古时期物资匮乏,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一群原始人正在跋山涉水,艰难地寻觅食物,汗水不断从他们黝黑发亮的皮肤滴落,饥饿激发了他们求生的本能。他们穿过布满荆棘的丛林,四处采集可以食用的植物和野生果实——采摘就是那个时代人类最重要的生存方式,而他们采摘的果实含糖量非常高。在不懂得生产技术的原始社会,糖分因此成为人类得以繁衍的主要能量——突然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原始人发现一棵挂满熟透野果的果树,他们的味蕾立即本能地跳动,身体内的激素在不断变化中释放无穷的快乐。他们迫不及待地爬上树,摘下甜美的果实往嘴里塞,饥肠辘辘的痛苦顿时烟消云散。这种感觉在进化论上被称为“适应性心理反射”,它能够暗示人类更好地摄取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
就这样,在人类不断进化过程中,对甜味的偏好就成了一种本能反应。人的大脑越来越贪恋这种甜蜜的气息。即便到了现代社会,在物质生活比较发达的情况下,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再依靠糖获取营养,但我们依然对甜食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爱好。
快乐和痛苦是人的两种最主要的情绪,如果有一种食物可以抑制我们的痛苦,放大我们的快乐,我们就容易对它着迷。毫无疑问,糖就是这样一种充满魔法的食物。学过生物学的我们都了解,人的大脑含有一种奇妙的物质,名为内啡肽,它的作用就是减轻我们的疼痛感和压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减少内心的痛苦,有时吃一颗糖就能起到“精神止痛”的作用。
朋友们,现在你总算明白了吧,为什么有人在面对压力和焦虑时,会疯狂地食用甜食。因为他们需要摄入高糖量来刺激内啡肽的分解,让自己从焦虑的泥潭中解脱出来。
糖除了可以分泌内啡肽这种减少和解除痛苦的物质,它还有一个容易让人上瘾的重要原因就是,可以直接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物质。没有人不喜欢多巴胺,多巴胺就是一个快乐小天使,奖赏给我们的就是幸福快乐的体验。当一个人通过吃糖获得了快乐体验时,为了追逐更大的快乐,就要摄入更多的糖分,从而形成了很难戒掉的糖瘾。
一个人痛苦时想要吃糖,一个人快乐时也想要吃糖,糖分就是如此轻松地控制了我们的大脑。如果我们将内啡肽与抑制痛苦、多巴胺与传递快乐比喻成一种社交关系,糖分就是维系这种关系的一根纽带。如此的话,我们在讨论人类和糖的纠葛时,就为后面的社交去糖化埋下了一个伏笔。在我们的社交行为和社交场景中,究竟要保留多少甜腻度才是合适的?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表,让我们继续梳理人类和糖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纷扰。我们可以说,我们喜欢吃糖,是身体机能的需求使然。但我们不能将身体对糖的需求视为糖瘾的唯一原罪。因为在古代,人类的制糖技术和工艺还很落后,那个时候糖就是一种奢侈品,产量低,物以稀为贵,一般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口福享用,只有位高权重的达官贵人,或者腰缠万贯的富豪们才能享用。因此那时糖对人类身体造成的危害微不足道。
P3-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