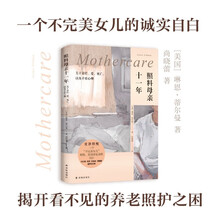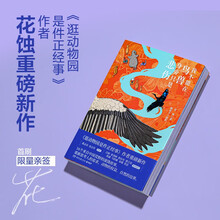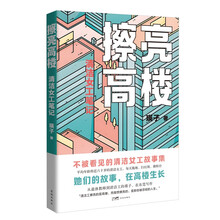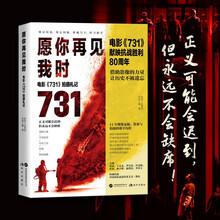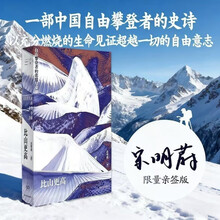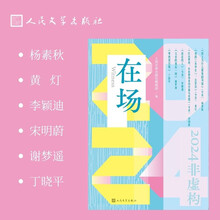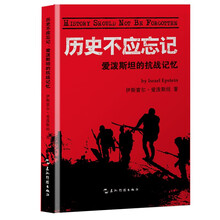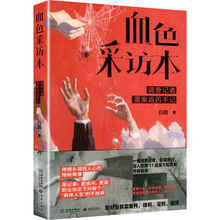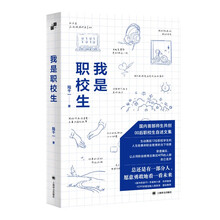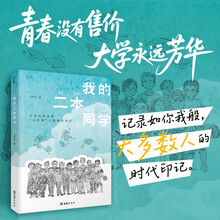忆成都七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校长刘文范
温辅臣
2020年4月末,欣闻同窗言,成都七中易校长欲将七中校志内有关刘文范校长任职时之一段历史加以补充,并要求我等知情人提供素材。我对敢于求历史真相的行为从来持尊敬态度,加之我妻子、女儿均为七中校友,故自觉应对此尽责,并以文悼念刘校长。——题记
“成都第七中学校”这一校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三年才使用的。国民政府时期及成都解放初期,其校名为“成都县立中学校”,简称“成县中”。校门上方有石材一方,上阳刻七字,金光灿灿,故口碑上有“金字招牌成县中”之美称。国民政府时期,末任校长为周开培先生。我便是这位校长任期内最末一届招入的学生,班级编号为男初六十七班。1949年9月入校,12月中旬即因时局紧张,学生未经期末考试就离开了学校。
1950年3月初,校方张榜通告,全体学生返校就读,且又招入一届新生,即男初六十八班。开学典礼上,一位身着解放军军装的中年人,经介绍之后步上讲台,以一口地道成都腔向全校师生训话。他就是刘文范先生。当时介绍其身份是“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驻成县中代表”,简称“军代表”,亦有称为“刘代表”的,其职责是对成县中进行全面领导,行政职务是副校长。他身高一米七左右,瘦瘦的,但十分精干,五官端正,无特别可言,唯有那上唇处短而黑的八字须,在教师中亦属独有,腰系一条军用皮带,右侧皮盒内插有勃朗宁小手枪一支。我辈初一小男孩自然只敢敬而远之。后来在校内常与其相遇,见他常常笑脸相迎,与周校长时期训育主任竹棍伺候大相径庭,故渐生好感。
军代表终日在校巡视,的确是大有缘故。1950年的成都治安状况不好。国民党政府留在大陆的敌特分子四处破坏、造谣,邪教组织“一贯道”更在夜间小巷内装神弄鬼,令市民、学生人心惶惶。学校环境堪称内忧外患,刘校长亲自视察必不可免,更须求得良策以解困,今日反思有所理解。刘校长有以下举措,现一一述之。
改变自己。他脱去戎装着民服,只穿中山装,没有了挺胸收腹的气态,似乎还可踱方步。这一与众多教职工相一致之举,立刻大大缩短了与师生之间的距离。此后学生们常在节假日傍晚时分,于东马棚街一带,或于法国医院(即今市三医院)近处,见其与夫人(王仲雄,时任成都一中校长)散步。向其敬礼以后,他不单真诚地笑脸相迎,有时还与学生浅谈几句家常。面对和蔼可亲的长者,学生们对其“军代表”的称谓便自然地过渡为“刘校长”了。
组织师生保卫校园。这是刘校长坚持了一年之久的大举措。此举不单严防了敌对分子的破坏,还达到了增强师生之间的感情,加强学生之间的团结,提高教职工、学生政治觉悟,锻炼学生胆量气魄的目的。1950年冬,夜深人静时,常有鬼哭狼嚎之声传来。刘校长着手组织了夜间巡逻队,巡逻队由一青年男教师领班,每班四五个学生,设三个固定哨位,教师带一学生为游动哨,刘校长每晚亲自查哨监督。全校学生参加巡逻,初中生亦然。1951年秋我住校后便参与了巡逻队,因个子小而只能安排为固定哨,发给我的“武器”是垒球棒一根。月白风清夜,手握球棒,顾影自怜的同时,亦颇有些丈夫气概。一次我轮为深夜班(每班两小时),见一人前来,便立刻大叫一声“口令”。来人低答之后走到我身前,才细声说道:“询问口令只能用低沉小声,只需来人听得便可。”同时又问了我所在的班级和姓名。谁知此后,刘校长一见我面便能呼出我的姓名,令我十分惊异。夜间巡逻工作直至1951年底才告结束,那时成都市民已安居乐业了。
正确引导学生,提高政治觉悟,树立正确劳动观点。1950年秋冬之交,刘校长宣布成立新中国成县中的首届学生会,主席、委员由各班提名,经全校酝酿后,由班长会议决定候选人,再由全校学生投票,选举票多为当选者。过程这般民主,自然是风平浪静地便产生了首届学生会的领导者,而且迅速开始了工作。工作内容是刘校长安排的。这些学生会成员,主要是高中学生中的意见领袖,此举之成功颇含了“擒贼擒王”的意味。然而对于这些“王者”而言,这则是他们的人生转折,此后由于多与学校领导接触,得到更多正面教育,其中有人调市团委工作,有人未毕业便投笔从戎,入朝抗美,首批入藏人员中也有其身影。由于校领导的正确指引,学生会成员也确有工作能力,校内不少大的活动都是由学生会具体指挥完成的。刘校长并非事必躬亲。例如上文中谈到的巡夜人员安排即为其一。又如学生会指挥的首项活动是“迁女校”,将数百张桌凳由茶店子转至青龙街,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但顺利完成,校产几无损坏。再如1951年初的首届校运会的组织等。尤其是校园的清洁工作一直不由工人完成,而是全校各班分片包干,学生会检查评定,这一工作成绩突出,效果明显,“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此举当属把学生中的意见领袖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并将全体学生引向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道路上的成功举措之一。
P7-9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