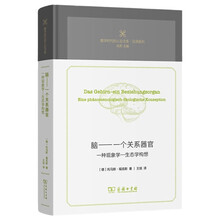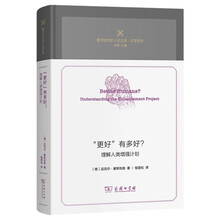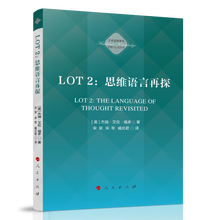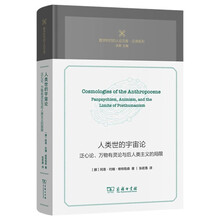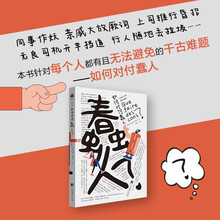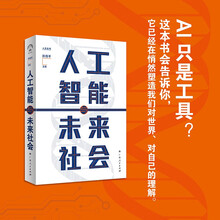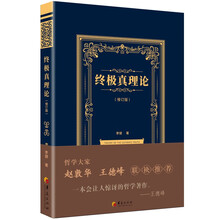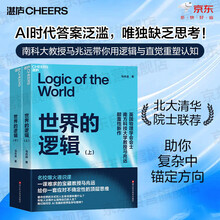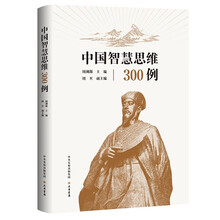导论:探索自然心智的起源
利兹 斯旺
一、自然心智
心智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所有努力背后的唯一统一力量。如果将它放入生物符号学和更广泛的生命科学的背景下,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在自然世界中生物心智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为什么是这样进化的?心智是人类所特有的还是与其他动物甚至更简单的生命形式所共有的?它是地球生命*有的,还是宇宙基本结构的一部分?
本书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如果我们把心思(mindedness)现象概念化为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一个客体的话,我们将在理解心思现象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将心智概念化为一个客体的悠久传统迫使我们去寻找符合其理论描述的东西,即使这意味着仅仅因为我们处于更好的位置去理解某个客体,我们就不得不在心智和某个客体之间进行拙劣的类比,结果却发现,有了这些新知识,我们离真正理解生物心思并没有更近一步。
相反,通过询问心思现象需要什么,我们已经将其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客体。美国实用主义者清楚这一点,并完全从这一视角进行写作。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也试图通过关注存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经验或正在进行的过程—来回避心智问题。心思是一些有机体参与其中的一个过程,心思的每一个实例在不同物种之间,甚至在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之间都会有所不同(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人类)。
根据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先验唯心主义,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本体(物质)世界,尽管人类心智的结构限制了我们只能体验到一个现象(表象)世界。这是心灵哲学史上*有力的尝试之一,它将人类的心思概念化,将其编织到自然世界的结构中。虽然康德并没有成熟的进化论可以借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在3/4个世纪后才出版],但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心智可以通过其内在结构和功能以特定的方式去体验世界,这一观点在大约200年前就预示了进化论在心智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康德的*特之处在于,他综合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因为他提出了关于人类心智结构如何从根本上塑造我们,如何构建自己对世界的经验从而认识世界的进步观点。从本质上讲,康德对心灵哲学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提出知识既不是源自内在,也不是源自外在。相反,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从人类关于世界的具体经验中涌现出来的。这个洞见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在当代认知科学中可以看到其影响。
遵循康德传统的心灵哲学,尊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合理平衡,开放性地把生命科学的见解纳入其心智理论,把抽象的概念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然而实际情况是,20世纪大多数的心灵哲学在分析哲学传统的主导下,完全脱离生命科学中的发现和见解但依然蓬勃发展。当然,它确实涉及计算机科学,因为功能主义—当时*流行的心灵哲学—是建立在机器功能和人类意识之间的比较之上。然而,重要的一点是,生物科学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纳入主流心智分析哲学的心智理论中。
关注当代心灵哲学的问题是一种容易让人屈服的诱惑。本书抵制了这种诱惑,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从一个自然主义的、科学的角度论述了什么是心思。因此,本书旨在对我们如何在自然世界中产生有机意识的科学和哲学理解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关于心思的生物符号学文献与现代心灵哲学文献有一些交叉。特别是,我很高兴地发现了生物符号学文献中对哲学家约翰?塞尔关于心智和意识的研究的应用(见Brier,2012;Barbieri,2011;Kravchenko,2005;Hoffmeyer,1997)。塞尔关于意识是一种生物现象的观点—他称之为生物自然主义(Searle,1992)—在我看来,应当成为当前和未来心智科学研究的基石;采用这种见解作为一种规范的方法论原则,将严重限制对极其抽象的心智模型的构建和讨论,这些模型不仅与大脑的复杂细节脱节,有时甚至与现实脱节。
心思是一种生物现象,完全依赖于复杂生物体,如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以及较不复杂生物体中更分散的神经系统。这一简单的观察表明,心思以不同的水平存在于生物世界中,这就意味着心思不是人类所*有的,而且我们特有的这种心思只是自然界中*新的设计—早在人类进化之前,心思就以各种形式存在了。
心智科学中的模型
虽然这些简单的见解得到了我们对自然世界的了解的充分支持,但在认知科学的大部分历史中,研究无生命的、无意识的物体(尤其是计算机),并从这些物体中得出关于心智的推论,一直都是传统。物理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休斯(R.I.G.Hughes)就科学模型如何运作—特别是模型的结果如何转换回所讨论的现象—开发了一个元模型(Hughes,1997)。图0-1抓住了休斯理论的精髓。
图0-1休斯关于模型在科学中如何运作的DDI元模型
自然现象的某些要素通过模型的某些要素来指示,然后模型被用来证明某些理论的结论。*后,对这些结论进行解释,以便对自然现象做出预测。因此,就像物理学家使用特定大小和体积的波纹水槽来模拟某一段海岸线,并用这个水槽来演示与海岸线相关的一些波动力学的细节。事实上,波纹水槽与开放水体没有任何物理相似性,但这并没有关系,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了解水的运行方式,关键在于模型中所使用的是水。由于现象和模型之间的物质组成的这种关键一致性,当实验结果在波纹水槽中得到证明时,实验者有理由使用它们来预测自然水体运行的各个方面。
进一步的思考会使这项实验的重点更加清晰:如果物理学家由于波纹水槽中的水的行为与开阔水域非常相似,就因此推断波纹水槽就是海洋或海洋就是波纹水槽,这将是错误的。物理学家不会这样推理,因为这样做会混淆模型和现象。但这似乎正是在认知科学中所发生的事情。在DDI元模型应用于心智科学的背景下,预期的方法是让生物系统启发非生物系统中的模型,并通过这些模型的结果来理解生物系统(图0-2)。
图0-2DDI元模型在心智科学背景下的应用
注:这是一幅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用于说明模型应该如何在认知科学中起作用的图
认知科学的主流观点一直是并且仍然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作为一种心灵哲学,只关注认知系统的行为而非其物质实例。出于这个原因,认知科学家系统地模糊了生物系统和非生物系统之间的界限。人们发现,关于大脑的诸多发现可以在硬件和软件中实现;同样,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发现也被假定可以转化到人脑中。然而,与物理学中的例子不同:在物理学中,物质(水)对于现象和模型来说是共同的;而在认知科学中,硅基创造物被用来模拟有机大脑。把模型与现象当作相同的事物来谈论,或者反之亦然,这在哲学上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模型中的基本材料与现象中的物质是不同的。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生物心智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多深刻的认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在计算机模型中准确复制生物大脑中发生的事情,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生物心智的计算模型所能做的是复制大脑自然功能的某些元素,比如计算,而且计算机执行这一功能的速度比人脑快得多。但是,从这个成功的建模推断出计算机就是大脑(或像大脑一样有意识)则是错误的,同样,把人的大脑说成是计算机也是错误的。计算主义,当被应用于除计算机以外的任何事物时都是毫无用处的,除非我们能够很好地解释有机大脑的“计算”意味着什么,如果它计算的是符号,那么这些符号在大脑潮湿的灰质中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哲学家彼得?戈弗雷-史密斯(PeterGodfrey-Smith)在一篇论文中阐明了实用主义者如何为心智的自然主义理解开辟道路。他概述了方法论连续性原则,根据该原则:要理解心智就需要理解它在整个生命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认知应当在“整个生物体”的语境中进行研究(Godfrey-Smith,1994)。这个合理的原则之所以没有被普遍遵循,是因为研究心智的和研究生物体的通常不是同一批人,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哲学家使用抽象模型,认知科学家使用软件和硬件模型来研究心智,而研究生物体的生命科学家通常并不研究心智问题—实验心理学中研究动物认知各个方面的离散项目显然是一个例外。
心思如何进化以及为什么进化的大问题,需要多学科的合作研究。生物符号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空间,吸引了生物学、认知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众多学者,他们认识到生物圈中从*简单到*复杂生物体的连续性,他们被联合到这个项目中,试图在这幅全面的生命图景中解释语言和意识。到目前为止,生物符号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主要关注微观世界中的编码、指号和指号过程—这一事实反映出该领域在微生物学和胚胎学中的强表征性。心灵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能够对日益增长的交叉学科研究所做的贡献是洞察生物符号学的世界观如何应用于像人类这样的复杂生物体,其中指号和指号过程构成了人类社会和文化。
二、心智的生物符号学理论
在这一部分,我将概述心智的生物符号学理论(biosemiotic theory of mind,BTM)的起源。在这里,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我对心思的看法:可以说不存在“一个心智”(amind)这样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心智”这个术语是一个概念性的占位符,它代表了我们和其他一些动物通过大脑和身体的协同工作所能达到的一系列能力,比如交流、表达感情、想象、满足我们的需求、学习、记忆、持有信念和计划。所有生物都具有一系列*特的能力来适应特定的环境,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倾向于将其概念化为“有心”(having a mind)。下面我将解释BTM与心智分析哲学和神经哲学中其他当代理论所提供的心智图景有何不同。
(一)BTM不同于心智分析哲学
*先,BTM不同于心智分析哲学,因为它并不关注心智的抽象理论—这些理论只在哲学中发展和使用—而是把心思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其描述与我们在生物学和认知科学中了解的自然世界(包括大脑和生物体)的所有内容相吻合。
一个关于哲学家所说的感受性(qualia,即经验的定性方面)的例子,将有助于阐明心智分析哲学与BTM之间的区别。当代心智分析哲学中有人认为,如果物理主义是正确的,那么作为物理存在,我们应该能够感知任何颜色、声音或味道,并对其做出适当的反应,而无须伴随任何定性的感觉(Chalmers,1995)。需要注意的是,“人类是物理存在”这个潜在的假设,既然物理存在不会体验到任何东西,我们也不应该会。因此,这个论点是,要么我们需要某种超越物理主义的东西来解释定性经验[这是哲学家戴维?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的立场],要么我们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思考物理主义。
我相信,提出我们为什么会有现象性经验这个问题表明,我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思考物理主义—例如,把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理实体混为一谈,并期望它们有相同的行为,这就是功能主义。因为自行车和人类都是物质实体,所以自行车没有感觉,我们也就不应该有感觉,这显然是糟糕的推理,因为它证明了一个错误,即相信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世界的真实情况。
世界上任何对我们有意义的东西—一*喜欢的歌*、一张熟悉的脸庞、一次令人烦恼的头疼、一盏绿色的交通灯、朋友的拥抱和咖啡的味道—都是质性经验。生物符号学大胆地承担起理解意义如何在生物系统中产生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通过气味、声音、景观和感受,质性地体验世界,而且我们知道在生物系统中我们并不是唯一能这样做的,解释意义如何从物质中涌现才是一个挑战,在这里,生物符号学比那种否认这种可能性存在的哲学观点更有用。
质性经验的问题在BTM语境下并不神秘。假设质性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对生物体机制是多余的,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及如何激发生物体去做任何事情。比如,它假设我们会在不感到渴的情况下知道喝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