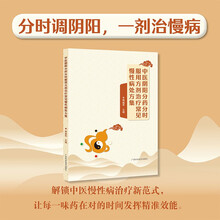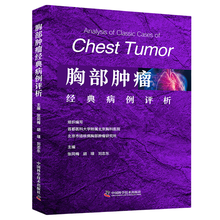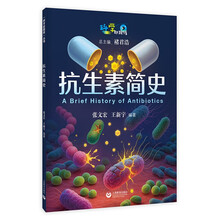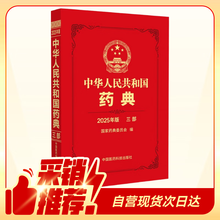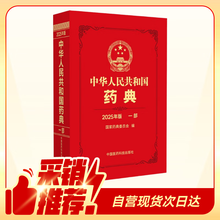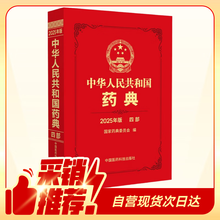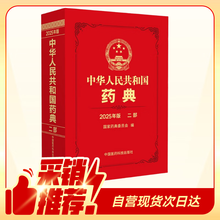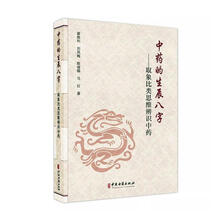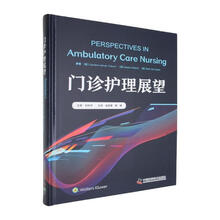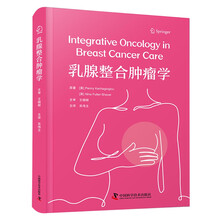总论
一、彝医药发展简史
彝医药学是中国传统医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扎根于彝族先民与自然界长期作斗争、求生存、繁衍和发展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与其他民族医学一样,药物在彝族医学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彝医药学拥有数量庞大的药物资源,涵盖了动植物药和矿物药等多种类型,其中以植物药和动物药的应用*为广泛。彝医药学研究的范围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尤其以植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药物在彝医理论的指导下,被用于临床实践,呈现出*特的应用特点和形式。彝族药物的起源、采集、加工、功能以及治疗应用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与彝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居住环境密切相关。
彝族人口约有983万人,主要分布在四个省份(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其中,云南是彝族分布*为密集的地区,约有507万人,主要聚居于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峨山、宁蒗、石林等地。四川有大约319万人,其中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大的彝族聚居区,有约300万人。贵州有约100万人,主要分布在毕节、六盘水和安顺等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有约1万彝族居民,主要分布在隆林和那坡两个县。此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少部分彝族分散居住。彝族聚居的这些地区主要位于中国的西南高原和东南沿海丘陵之间,地理环境多样,包括高山、深谷、丘陵、河谷等地貌,气候条件复杂多变。这些地区有海拔3000m以上的高寒山区,如滇东、黔西的乌蒙山地区以及四川的大凉山地区,气候寒冷;还有海拔1000~2500m的山区和半山区,如小凉山、哀牢山、无量山等,这些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另外还有海拔1000m以下的丘陵和河谷地带,如金沙江、元江谷地等地,这里气候炎热,降水稀少。这种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彝族聚居地区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为彝族先民认识和利用各种药物治疗疾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彝族的远古居民栖息于深山密林之中,与毒蛇猛兽为邻,过着艰苦的游牧生活。在与自然环境和各类疾病长期抗争的过程中,彝族的祖先逐渐积累了对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的初步认识,并逐渐积累了运用草药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具特色的彝医药学体系。彝族学者刘尧汉先生曾记载了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在很久以前,彝族的祖先在进行狩猎和放牧时,留意到家畜及野生动物常常受到寄生虫或皮肤病的困扰,这些动物会前往岩谷之间的地方打滚摩擦,似乎是在获取天然硫黄和火硝。于是,彝族的祖先采集了这些物质,并尝试用于治疗家畜的寄生虫和皮肤病。后来,当彝族人自己患上皮肤病时,他们也开始尝试使用硫黄和火硝的混合物来治疗,效果令人满意,这种治疗方法逐渐传承下来。这个古老的传说生动地描绘了彝族医药传统的渊源。
1. 哎哺原始时期至大理国时期
在彝族人民的传说中,远在天地形成之前,整个宇宙呈现出一片“太空空、大虚虚”的混沌景象。后来,由于“气”的发展和变化,清浊之气分化,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人体与天地之体相似,同样由清浊二气演化而来,彝族用“哎哺”这一术语来指代这一过程,而哎哺后来成了彝族*早的氏族名称。哎哺谱系的历史可追溯至五百多代,按照每代约20年的计算,延续时间超过一万年。值得一提的是,在哎哺时期,彝族的祖先就已创造了天文学,并开始使用文字。在母系社会时期,彝族社会已经掌握了采集身边自生植物并将其用于内服、外敷或熏蒸等治疗疾病的技巧。古老的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中有记载:“毒蛇咬伤的,麝香拿来敷;蜂子蜇伤的,尔吾拿来敷。”支格阿龙是彝族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创世英雄,在他与雷神的对话中,涉及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其中包括多种药物,是目前已知的*古老的彝族药物疗法。彝族所使用的这些药物的名称也常被用作某个部落或部族的代称,甚至有的山岭也以药物命名,如“达罗波”、“达日波”和“舒祖波”等,这些名称分别指代着黑色的阙山草、阙山草以及杉树繁茂的山地。这种以植物来命名地理特征的习惯,从母系社会一直延续至今,凉山地区迄今仍然存在以植物为名的地区,如勒乌(大黄)和尔吾(土香薷)等地名。
汉代《说文解字》载:“菖蒲,益州生。”《图经本草》记载了彝医使用菖蒲的经验,如“蜀人用治心腹冷痛者,取一二寸捶碎,同吴茱萸煎汤,饮之良。黔、蜀、滇蛮人亦常将随行,卒患心痛嚼一二寸,热汤或酒送,亦效。其生蛮谷中者尤佳”。另外,《名医别录》中也有关于彝族先民生活地区药材的记录“麝香,无毒,生益州”“犀角,生永昌(今云南保山)及益州”。
汉代以后,有关彝药治疗疾病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据《大理古佚书钞》载:“诸葛亮南征,将士于落马坡误食哑姑泉,将士三百余人失声喉痛,后遇孟获之兄孟节,孟以苦良皮、黑霸蒿、青茶、紫茎菊熬水服食,而肿消毒平。”这个案例可以视作西南地区彝医药治疗疾病的一个缩影。
晋代,彝药中的附子、犀角等已成为皇宫的贡品。东晋《华阳国志》载:“堂螂县(今云南会泽、巧家等地),因山名也。出银、铅、铜、杂药,有堂螂附子;牧麻县(今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山出好升麻;会无县(今四川会理); 土地特产犀牛。”堂螂县和牧麻县等地自古以来都是彝族的聚居区。古代人们常常以地名来命名药材(如“堂螂附子”),或以药材名称来命名地名(如“牧麻县”),这足以证明在汉晋时期,这些地区的药材就已经享有盛誉。值得注意的是,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所称的“杂药”,显然指的是那些当时汉族人尚不了解或未纳入正式典籍的民族药物。
南诏时期,南诏政权与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保持密切的交流。在此时期,彝汉医药交流频繁,一些彝族药物被纳入了唐代的汉医药书籍中,同时汉族医药也传入彝族地区,受到了彝族先民的欢迎和应用。如在唐开元时期(713~741年),陈藏器编写的《本草拾遗》中提到了一种彝药,被描述为“*自草,有强烈毒性,涂抹箭镞上,中者即刻身亡”。
此外,据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提到“南诏的石榴子颇大,果皮薄如藤纸,味道胜过洛中(即今天的河南)产的石榴”。这表明了当时彝族地区的石榴被汉族人采用,并被认为是上品。彝族传统上喜欢使用石榴的根、果皮等部位来治疗疾病,后来的《明代彝医书》中也记载了使用石榴皮入复方来治疗风疹的情况。
在大理国时期,彝族名医杜清源被尊为药王,他在彝族社群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孙子杜广整理并记录了《点苍药王神效篇》(后失传),其中详细记载了四类药物,包括草药、木材、昆虫和矿石等,共计1400多种,详细描述了它们的色形、药性、配方、注意事项、炼制丹药的方法等。这些记录都是在古代七百余年的南诏政权时期积累的验方经验。此外,宋代《淮城夜语》还记载了元宣和年间,在滇西一带,彝药如龙珠草、重楼、天南星、虎掌草、百毒消等在治疗外伤方面显现出良好的疗效。
此外,宋代的《岭外代答》记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蛮之所赉,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这表明彝族药物的大量输出,彝汉之间的商品交换一直保持着持续的活跃状态。
2. 明清至民国时期
明代是彝医药古籍文献成书的重要时期,当时,朝廷通过屯军、屯民和屯商等措施,大量汉族人口迁入云南等西南地区。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中原地区文化和技术,如精工造纸术和先进的医术,也随之传入,促进了彝族地区造纸业和医学的发展。同时,商人的流通和医患的互动也促使纸张在彝族地区普及,导致彝族民间改变了传统的书写习惯和材料,这是至今为止保存的彝医药纸书文献多为明清以来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部分汉族医生也迁入彝族地区,他们带来了书写和传抄医书的习惯,进一步促进了彝医与毕摩的发展。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集彝医和中医理论于一身的医学大家,如云南嵩明人兰茂(1397~1476年),他所著的《滇南本草》是一部著名的地方性本草,用汉文书写,收录了507种药物,该书汇集了许多分布于滇中和滇南一带的彝药,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于明代问世的《双柏彝医书》一书,又称《明代彝医书》,成书于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尽管它并非专门的本草书籍,但其中所记载的彝族植物用药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书中详细记载了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皮、全草、树脂及植物寄生的药材,达数百种之多,包括根及根茎类66种,叶类17种,皮类12种,果、籽类19种,全草类34种,茎木类6种,寄生、树脂、菌类6种。《双柏彝医书》总结了16世纪以前彝族人民的医药经验,迄今尚未发现有容纳如此丰富的彝族医药专门书籍。在此之前,彝族的医药经验分散于各种经书和史书中,记录零散而有限。然而,《双柏彝医书》在不到5000字的篇幅内详细描述了多种疾病的治疗药物和使用方法,这些疾病和药物均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地方性。这一时期,彝医开始广泛使用动物药,其中入药的部位包括皮、毛、骨、角、血和脏器等。
清代以后,许多典籍开始更为详细地记录了彝族药物的使用情况。《献药经》成书于清初,书中彝族动物药的比例高达92.8%。《彝族治病药书》(公元1664年)发掘于今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该书收录了384种药物,其中包括动物药79种,植物药290种,矿物药15种。此外,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及《宇宙人文论》均成书于清康熙三年至雍正七年(公元1664~1729年)间,这些书籍涵盖宇宙万物的起源、历史、哲学、天文历法等内容,对彝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期的《启谷署》分为5门28类260方,该书的治疗方法和方药配伍合理,将彝药的治疗方法和配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造药治病书》成书于16 世纪末,发掘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该书收录了201 种药物,其中包括60 种动物药、127 种植物药以及14 种矿物药和其他药物。另有《娃娃生成书》,又名《小儿生成书》,创作于公元1723~1736 年,专门介绍妇科和儿科生理知识。同时,还有《医病书》(公元1731年),其中包含97种药物,包括25种动物药,72种植物药,以及68个方剂。而《医病好药书》(公元1797年)则在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茂山乡被发掘,其中收录了426种彝药,包括152种动物药、269种植物药以及5种矿物药,相较于《医病书》,该书内容更加丰富,范围也更加广泛,总计317个处方,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药物的多种作用和配伍关系。此外,《元阳彝医书》(公元975年)也值得一提,收载了200多种药物、68个病名,以及一些简易的外科手术方法,它的发现为彝族医药史的研究提供了更有价值的史据,是彝族医药史研究的重大发展。《老五斗彝医书》成书于晚清,于1987年被发掘于今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老五斗乡。该书收录379种药物,包括123种动物药、235种植物药以及21种矿物药。《洼垤彝医书》成书于晚清,1986年发掘于今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洼垤乡,其中收录了336 种药物,包括75种动物药和261 种植物药;《三马头彝医书》也成书于晚清,发掘于今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洼垤乡三马头,该书收录植物药168种,动物药80种,矿物药15种。这些彝族药物古籍的发掘和整理,体现了深厚的彝医药历史底蕴,为彝族医药的发展增添了辉煌篇章。
3. 新中国成立至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医药。20世纪70年代,云南省、四川省等彝族主要分布区的医药卫生专业机构积极开展对古彝医药文献和彝药资源的系统调查、研究和整理工作;同时采集原动物、植物、矿物标本以进行鉴定工作,基本查清了常用彝药的资源种类,并在古代彝药本草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1970~1986年期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对彝药资源进行数次大规模调查。楚雄州组织百余人的专业队伍进行彝族医药普查,共发掘彝医药古籍28册,包括著名的《双柏彝医书》,并采集鉴定各种药物标本1013种,同时筛选出基原清晰、临床常用、疗效确凿的103种彝药,编纂成《彝药志》。自1984年开始,楚雄彝族自治州相关单位历时4年,再次对全州的中草药资源进行了全面普查,结果显示,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的各种药材资源包括243科1381种,其中有560种为彝族药材。在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省玉溪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