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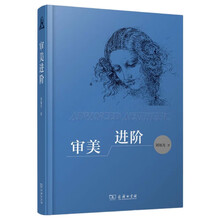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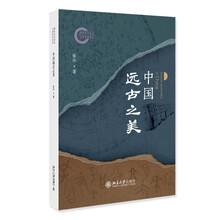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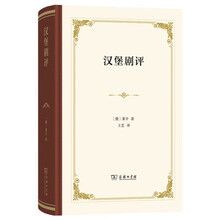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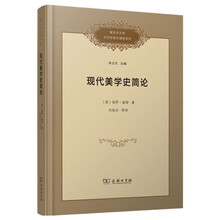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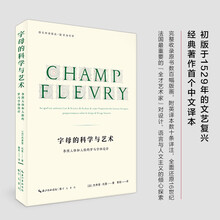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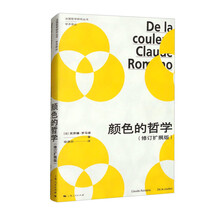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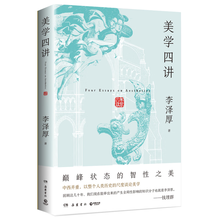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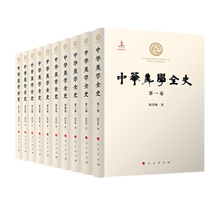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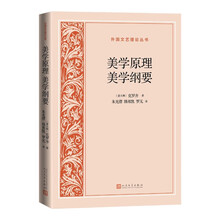
1、喜剧的本质,就是人性的本质!
笑,像呼吸一样自然,但你可曾想过:我们为何发笑?好笑的事物为什么好笑?
《喜剧的本质》几乎是惟一一部专门探究笑的学问、洞察喜剧性内涵的权威经典
从喜剧中读懂社会,在笑声中看透人心。学会让人笑,理解被人笑,是蕞精妙的智慧。
2、诺奖得主柏格森的哲思精粹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大师,字字珠玑的大家小书
语言风趣幽默,文风犀利深刻,读者:“我愿称柏格森为金句大师”
3、大师推崇的大师!
弗洛伊德、萨特、普鲁斯特、伍尔夫、梁启超、梁漱溟、朱光潜、柳鸣九、木心等名家都深受影响
4、喜剧人的灵魂之书!
喜剧影视、脱口秀、相声小品、搞笑视频创作者&爱好者建议人手一册
创意产业从业者、大众文化爱好者、社会现象洞察者皆会深受启发
5、全新无删节典藏版
旅法艺术家、索邦大学哲学硕士法语直译,呈献全新优雅译本
典藏精装,玩味设计,精致小开本,通勤出游轻松携带
笑,如同呼吸一样自然。然而,我们为何发笑,以及触发幽默反应的主题和情境,却少有人深入思考。
在《喜剧的本质》一书中,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试图捕捉并分析这种难以捉摸的喜感的本质:我们为何发笑?可笑的事物为什么可笑?在喜剧、闹剧、小丑的鬼脸、俏皮话、文字游戏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喜剧和正剧的区别在哪里?
通过探究人类事务中所有幽默的元素,精微分析形式、动作、情境、语言以及性格的喜剧性,柏格森希望提炼出喜剧背后的共同运作方式,对社会、想象力和文化形成更深刻的理解。
柏格森认为,喜剧性是人类独有的特质,而冷漠与超然是发笑的前提条件。喜剧不完全属于艺术,又不完全属于生活,它具有社会功能,促使人们省察自己,令社会机体保持活力。
在文艺经典中,关于笑的洞察非常罕见,而柏格森对喜剧本质的论述则是一部独特且不容错过的作品,书中提供了一系列深刻隽永的见解,关于我们为何觉得事物有趣、这些事物如何揭示我们自身,以及如何教会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第一章 喜剧通论——形式的喜剧性和动作的喜剧性——喜剧的张力
笑意味着什么?可笑的事物中到底蕴含着什么?小丑的鬼脸、文字游戏、滑稽剧中的误会和高级喜剧的场景有什么共同点?我们要如何从形形色色的作品中——它们中有的散发出浓烈的气味,有的散发出优雅的芳香——提炼出始终如一的精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伟大的思想家都遭遇过这个小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总是在压力下极力闪躲、溜走、逃脱,却又总是再次回来,对哲学思辨抛出傲慢的挑战。
我们之所以也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并不想把喜感的美妙局限在一个定义之中。我们在其中首先就看到了活生生的东西。不论它多么微不足道,我们都应尊重它,就像我们尊重生活。我们仅限于观望它成长,看它开花盛放。喜感通过一些不易察觉的阶段,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进行着奇特的形变。我们并不会轻视观察到的任何东西。或许通过这样持续的接触,我们可以获得比理论定义更灵活一些的东西——一些实际的、亲密的认知,就像从一个交往许久的朋友那儿获取的那样。或许我们还会无意间发现一些有用的认知。喜感即使在它最偏离正轨的表现当中,总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喜感带有一定的疯狂的意味,但它的疯狂总也会根据一定的方式,喜感也带有梦幻的性质,但在梦幻之中却能唤起一些能为整个社会立即接受和理解的幻象。喜剧的幻象怎能不告诉我们人类想象力,特别是社会性、集体性和大众性想象力的工作方式呢?既然它源自现实生活,与艺术相关联,它又怎能不对艺术和生活本身有所启示呢?
我们先要提出我们认为是基本的三个观点。这些观点和喜剧本身关系较小,而与该去哪儿寻求喜剧这个问题关系更为密切。
一
我们请读者注意的第一点:唯独在人类的范畴内,才有喜剧。风景可以是美的、幽雅的、圣洁的、平庸的或者丑的,但它永远不会是可笑的。我们可以笑一个动物,但那是因为在这个动物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人类的态度或表情。我们或许会嘲笑一顶帽子,但那并不是在嘲笑做帽子的毛毡或者稻草,而是在笑人类所赋予这顶帽子的形状,笑人类在给帽子做造型时的突发奇想。为何如此重要、如此简单的一个事实却没有引起哲学家们足够的关注呢?有些哲学家将人类定义为“一种会笑的动物”。其实他们也可以将人类定义为一种会使人发笑的动物,如果有其他动物或者没有生命的物体也令人发笑了,那是因为它们身上有某种和人类相似的东西,因为人类在它们身上留下了一些印记或者拿它们来派什么用场。
现在我们要说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点:通常伴随着笑的是一种不动情的状态。看来只有在宁静平和的灵魂上,喜剧才能产生其震撼作用。冷淡疏离的心理状态是喜剧的自然环境。笑最大的敌人是情感。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笑一个让我们感觉怜悯或是爱慕的人,但是,在我们笑这个人的时候必须暂时忘了这份情感,关闭这种怜悯之情的开关。在一个纯知识分子的社会中,我们或许不再哭泣,但我们可能仍然会笑;而在另外一个社会里,人们的心灵都很敏感,身心完整合一,所有的事件都会引起情感的共鸣,那他们是不会认识也不会理解笑的。你可以试一下,在一个时刻,你对另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感兴趣,你设想着跟随别人的一切行动,感受别人所感受的一切,把你的同理心扩张到最大限度,那时你就会像是受到魔杖的支配,你看到的任何东西,哪怕再微不足道,都会变得重要,任何东西都会被镀上一层严肃的色泽。现在请你跳脱出来,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心态看待生活,生活中很多的正剧就会变成喜剧。在一个跳舞的沙龙里,如果我们把耳朵捂上不去听音乐,那么那些跳舞 的人就会瞬间变得可笑。人类有多少行为能够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呢?我们难道不能看到很多动作,如果脱离了与之相伴随的引发情感的音乐,就会瞬间从严肃变为可笑吗?所以喜剧为了产生它的全部效果,必须要求我们片刻的情感麻醉。喜剧只单纯诉诸智力。
只是这种智力活动需要和其他人的智力活动保持联系——这是我们想要大家注意的第三个事实。如果一个人感觉自己是被孤立的,那他就不太能感受到喜剧。似乎笑是需要一种回声的。请注意:这不是一个干脆利落发完了事的声音,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回响逐渐壮大延长的声音,就像山谷雷鸣滚滚翻响。但是这种回响不会持续到无限远。它可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扩张,但这个范围总是有限的。我们的笑总是一群人的笑。你也许在火车车厢或是聚餐餐桌上听到过旅客们互相讲述一些他们认为滑稽的故事,然后大家开怀大笑。如果你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你也会和他们一起笑;但如果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你便不会有笑的冲动。有一次,一个男人去听牧师布道,现场其他人都听哭了,只有男人没有哭,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哭,他回答说:“我不是这个教区的。”这个男人对于眼泪的理解用到笑这件事上或许会更准确。不论看起来多么坦率,笑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某种和实际上或想象中同笑的伙伴们的心照不宣,甚至可以说是同谋的东西。我们常说:在剧院里,观众越多,笑声就越大。我们也常说,许多和特定社会的风俗思想有关的喜剧是无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但就是因为有人没有理解这两个事实的重要性,从而在喜剧中只看到供人精神消遣的一种简单的好奇心,而笑,就只是一种奇怪的、孤立的、与人类其他活动无关的现象。由此可见,那些单纯将喜剧看作被精神所感知到的“智性的对比”和“情感的荒谬”之间的抽象关系的定义,虽然确实符合喜剧的各种形式,却一点儿都没有解释为什么喜剧会使我们发笑。确实,为什么这个特定的逻辑关系,一旦被我们感知到,就立刻链接到我们,使我们快乐,撼动我们,而我们的身体对其他的逻辑关系却无动于衷呢?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了理解笑,必须将它放置在它的自然环境中,也就是社会中;尤其应该确定笑的功用性,也就是它的社会作用。让我们现在就明确说明:这才是我们所有研究的指导思想。笑必须回应集体生活的某些要求。笑必须有一个社会意义。
让我们把这三个初步观察结论的交会点清晰地标注出来:当一群人聚在一起并把关注力全部放到其中一人身上,不动感情,而只运用智力的时候,就产生了喜剧。那么这时候他们的智力应该运用到什么上面去呢?回答这个问题,就已经把问题推进一步了。但有几个例子我们必须在这里列举一下。
亨利·柏格森为我们构建的哲学体系,本可作为诺贝尔奖理念的基石与支撑——这个理念旨在褒奖的不是人类的具体行为,而是通过杰出人物展现的新思想。柏格森那些崇高的著作致力于为人类意识重获直觉这一神圣天赋,并将理性置于恰当位置——服务于思想并加以调控。——1927年诺贝尔奖评委会
这本关于笑的哲理著作,对笑作为一种个人心理表象的缘由与各种形式,对笑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姿态所具有的功能效应,都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应视为关于笑之研究的一部十分权威性的著作,它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研究一样,也是20世纪人文研究中的经典。——柳鸣九
柏格森属于少数几个从源头上深入探讨笑和喜剧的重要哲学家。——马克·辛克莱尔
薄薄的一本小书,读起来才知道分量很重,它就像一个看起来简单,实质精巧的装置,每一句话都是装置中一个灵动机关的部件。作者辨析的独到和精微,让人叹服。——读者评论
我愿称柏格森为金句大师。——读者评论
活着,除了学会如何死,所余那就是学会如何笑,尤其是在洞悉了生命如何荒谬之后。所以,悲剧是为了接近人类精神的实质,喜剧就是重现眼前的生活。——读者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