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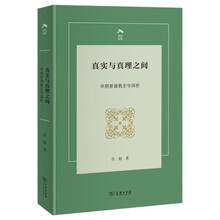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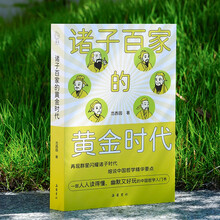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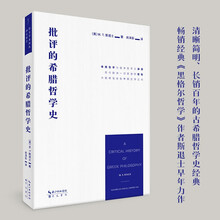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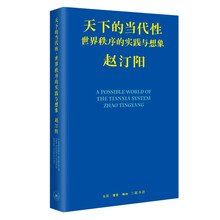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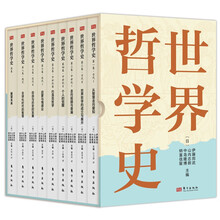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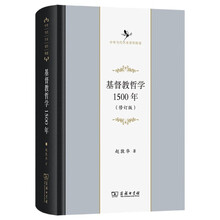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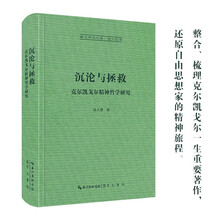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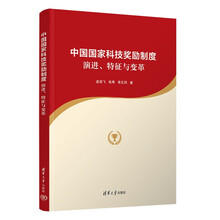

1.带领我们重新回顾了自黑格尔以降的哲学发展,尤其是科学大步向前行时,思想界所面临的道德与精神危机,这种张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2.一部尘封多年的译稿,历经战乱与浩劫,终于重见天日;
3.布雷伊耶作品的首个中译本,学术意义重大,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有助于汉语哲学界对1850至1930年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开展研究;
4.向汉语界推介了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雷伊耶;
5.译笔文白夹杂,具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风,极富特色。
《欧洲哲学史(1850—1930)》为布雷伊耶先生所作一套哲学史丛书中的最后一本。此书从1850年叙述至1930年,以尼采和柏格森为分界,分两期叙述前四十年和后四十年哲学的梗概和发展。其中牵涉到的哲学家有五十多人,著作有上百部。这本短小精悍的哲学史,其中心论点就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交锋。它带领我们重新回顾了自黑格尔以降的哲学发展,尤其是科学大步向前行时,思想界所面临的道德与精神危机,这种张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节选一
然而尼采对语言的研究,引起他对希腊的默想,他在希腊民族发现“一反历史的文化之实相,这样一种文化尽管是反历史的,或者恰恰就是因为它是反历史的,所以有说不出的富厚和说不出的丰饶”。他著的《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就是从他以叔本华的哲学去反省和解释希腊文化,以及从他的朋友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歌剧而产生的,他在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之前写这部书,一八七二年才刊行(一九〇一年译成法文);一八八六年版加上一副标题——“希腊主义与厌世主义”(Hellenism and Pessimism);古典的批评[这种批评上溯至文克尔曼(Winckelmann)]仅认识希腊艺术的一面,即塑像的艺术,阿波罗(Apollo,日神)的艺术,形式的神;这是均衡的、标准的、知识的和自我控制的艺术,适合于痛苦的世界中所作安宁的和无感觉的默想;“实在的世界盖上一层面纱,然而一新的世界,一愈加光明的、愈加智慧的、愈加幻想的世界,在我们的眼底产生了,且不断变化着”。和阿波罗的默想对立着的,则是狄俄尼索斯(Dionysius,酒神)的狂喜,那是意志统一的认识,是叔本华的厌世的观点;希腊的悲剧中,合唱则代表狄俄尼索斯的伴侣;“它使思想为英雄遭受打击的不幸而不寒而
栗;它表现这种不寒而栗之最高的和最大的力量的快乐”;它不寒而栗,因为极度的不幸不让它作阿波罗的默想;但这种极度的不幸引导它于生存意欲中把握不幸的原因,引导它否认生存意欲而获平静——这就是瓦格纳所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的思想,照尼采看来,瓦格纳的歌剧即希腊悲剧的再生;这种歌剧,“引导表面的世界到自行创造的,愿返于唯一的、真正的实相之庇护的内心境界”。
节选二
“真的哲学将深究爱情之本性”,康德与苏格兰(Scottish)学派的错误,在于仅使用悟性或抽象概念的能力,就以为内在的或外在的经验仅能达到现象而已;但我们可用活泼有力的反省,达到灵魂的实体,比朗(Maine de Biran)则为其好模范;如果灵魂,在第一次反省之下,显现为意志与努力(will and effort),那么蕴含在这努力中的欲求与趋势必然以与善相结合的感情为依据;这种结合非他,爱而已,爱实构成灵魂的真实体。
拉维松对于艺术曾作深切的沉思,这种沉思引导拉维松在形式的阳刚(rigidity of forms)之下,把握着一切内在的统一与内在的和谐;在美丽(beauty)之下把握着神思,在柔和的线条之下把握着线条所作波状的和蛇形的运动,在形式之下把握着音乐。“学习图案就是学习把握造成形式的歌咏。因为音乐与歌咏是全世界所包含者之最大的表现。那么,学习音乐之所以起于一切者,则求万有所说者成为可觉的。”一普遍的和谐乃若一散布万有之神恩,自然就是这样存在着。
节选三
在一八八〇年间,什么是流行的哲学思想呢?那个时候,我们只见斯宾塞的禁令、叔本华的消极、泰纳的简约,三者均消毁了实有,消毁了睿智的或道德的价值;斯宾塞的禁令,把精神关在不可知的铁圈里,并想把一切形而上学驱逐出境;叔本华消极的厌世主义,在一切存在之下,发现个人生存意志的虚幻;泰纳哲学的简约,把精神的事实,归约为感觉,复把感觉归约为运动,结果看出一切实在,物质的和精神的实在,皆从一极小极小的跳动(infinitesimal pulsation)而涌出,复无限地自相组合;与三者对立的哲学,除了拉舍利耶和布特鲁的思想尚坚强有力外,其余只是一种瘦瘠的和无足轻重的精神论,继续维持自由与意识之不可归纳,并把自由与意识建立在一直接的内部观察上。
首先,当时思想界尚流行一种宇宙观,将一切实际的和直接感受到的生命之意义与价值,全行抹杀、全行消灭,这种宇宙观似是理智和客观的苦痛所导出的;意识与德性一样是幻想,是生命力的谎言而已,易卜生(Ibsen)的剧本、尼采的哲学,指出人类的懦弱是多么危险,而哲学的任务,则宣布新时代之将降临;这种情况极端的结果,则见之于勒南的精神,他为尊敬真理之故,不得不宣示这些幻想,遂走到高级讽刺的路上去,将这种义务视作幻想,且由于他的保守精神,或由于他惮于为恶的意念,遂接受这些谎言:聪明反被聪明误。
节选四
记忆的问题供给这方法的应用以特别切实的机会:我们想象诸意象如同一些清楚的事件,每一事件消隐于意识之后,则保存在大脑的某部位中,若有其意象呈显于意识与之联合,则此一事件的意象后重新出现;这意象的后生与局部化是由另外的一些作用而完成的,这是观念联合论(associationism)所最可把握着的,可说毫无问题。但在柏格森这方面看,是不是有问题呢?柏格森的精神概念,若如他在《时间与自由意志》所宣布的,这似乎成为很难解决的问题了:一精神的生活维持着唯一的连续,与“忘记”所输入之显然的片段,两者是可调和的吗?“忘记”的问题,对于同一典型的思想家,如柏格森先生、普罗提诺或拉维松,是根本的问题;柏格森先生在《物质与记忆》绪言中曾经指出,这是他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如果知觉与记忆是纯粹的认识作用,那么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如果知觉与记忆将间断(discontinuity)输入精神之中,这就表明,在这些作用的行动层面,存在着如《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所描写的使事件碎片化的理智。但实际上,精神的连续要求某一意识生活之每一刹那里,全部过去的意识,呈现于当前;如果我们是一些纯粹的沉思的东西,是一些纯粹的精神,则全部过去显于当前是完全的和不灭的。然而我们有身体,换言之,我们全部器官,借神经系统之助,应以适合的反动应对外来的刺激:我们的注意为这种情况所支配,绝不能散乱和冲淡于遥远的过去里;若无当前的注意于每一刹那指导我们作适当的反应,则生活是不可能的;当睡眠的时候,当前的注意消失了,梦中的意象完全与当前的情势不符合,遂侵入我们之心境;人若没有身体,那就是永远做梦的人;那么,身体是阻止精神趋入歧途的法宝。身体乃最好的选择工具,于过去中挑选有用的意象,足供我们说明现在,或供我们当下利用;那么,记忆中的间断则由效用的原则而产生。普罗提诺说过:“我们看守着一切所见过者的忆念,这不是必要的。”
节选五
在《历史与科学中基本观念之连锁的研究》一书内,库尔诺尤喜称范畴为基本的观念(fundamental ideas),所以范畴不是由一种内在固有的效能而证明,但由许多不同的和独立的缘由而证实:例如经验,这是一;简约的演绎,即引一新的观念到某些愈简单的观念之演绎,这是二;想象的必要,例如原子论的来源,这是三;观念及观念所规定的事实中所作的和谐,这是四;观念以及各有关联的科学之基本意念间之和谐,此其五。总之,一基本的观念要求“为它的成就所鉴定,换言之,即要求为基本观念把秩序与联结放在我们的知识系统中鉴定,或要求为它在知识系统中所散播的扰乱及它所引起的冲突而鉴定”;例如,实体的观念,即由我们人格特有的同一性之经验而生,这一观念应用到可权量的现象是有功效的,此即经验告诉我们,在化学的分析中,重量有永恒性;但实体观念应用去解释不可权量的现象,如光线等,则毫无功效[库尔诺并不接受流体理论(theory of fluids)]。
因此,库尔诺的方法大大有助于各种科学的分界,如数学与力学的分野、天文学与物理学的界限、物理学与生物科学的疆界、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划定,界限分明,不相逾越,但这种划分并非凭借相当于本质的实相之知识而达到,而基于必须把新的基本观念输入到每种科学之内。在这点上,库尔诺的态度完全与孔德的态度相类似,他同孔德一样,主张诸科学之不可简缩,而两人也有不同之点。库尔诺的态度不是独断论的,而为概率论的,他抱着概率论的态度,把各种情形分开来研究:他觉得把一力学的原理,如活力守恒的原理,推广到全部物理学,这是有效能的;反之,如原子的假定,尽管它很合于经验并合乎我们的精神的习惯,“但绝不足以说明事物的奥秘,因为它既不能有系统地综合已知的事实,又不能发现未知的事实”。库尔诺由是而树立自一观念至另一观念之不可灭缩性——并非建立在自第二个观念推演至第一个观念之不可能上,而是建立在演绎所具有之复杂性上:所以应用力学能够用在天体力学上,但此时需要一些很复杂的假定,故最好是立刻输入一新的范畴,比如机械功或者牵引力。
目 录
第一期 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九〇年
第01章 时代概观 002
第02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007
第03章 演化论、进化论与实证主义 016
第04章 宗教哲学 056
第05章 批评论的运动 074
第06章 形而上学 100
第07章 尼采 124
第二期 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三〇年
第08章 柏格森的精神论 138
第09章 生命与行动的哲学:实用主义 151
第10章 唯心论 169
第11章 科学的批评 186
第12章 哲学的批评 200
第13章 实在论 226
第14章 法国的社会学和哲学 253
第15章 心理学与哲学 264
后 记 270
布雷伊耶此著得以翻译出版,学术意义重大,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有助于汉语哲学界对1850至1930年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开展研究。同时,译作出版亦向汉语界推介了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雷伊耶。
剑峰先生的汉语译文行笔通达流畅,使深奥的哲学原理得以准确贴切地表达,本书是值得一看的好书。
——夏书章(中山大学教授、原副校长)
那是一段科学知识热烈发展的时期,不论物理学、数学、化学,还是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这些知识被应用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引发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包括电力的出现、石油的开采、矿石和钢铁的炼制、汽车的诞生、飞机的发展、电话和灯泡的出现等等。这些发明和创造不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认知世界的方式。
《欧洲哲学史(1850—1930)》带领我们重新回顾了自黑格尔(Hegel)以降的哲学发展,尤其是科学大步向前行时,思想界所面临的道德与宗教危机,这种张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黄国象(哲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