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黑格尔、现代性和哈贝马斯
一
黑格尔的前耶拿时期和耶拿早期作品部分地反映了尼采所说的一种德国人的“乡愁”,一种对启蒙运动“正面性”的反感,以及对希腊城邦和早期基督教团体(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艺术)模式作为一种理解方式的向往,反其道而行文于现代哲学、宗教和政治生活之局限性。在这些文本中,启蒙运动对宗教的胜利被描绘成得不偿失的,被描绘成一个算计的、碎片化的理性模型的理想化,所有这些不过是将一个压迫的、外在的立法者以一种方式从外部转移到内部。这种启蒙是一种“没有牢固核心的虚荣的喧嚣”,一种对试图“把这种虚无转化成一个体系”的习俗与信仰的“消极”反应。在类似的这种观点方面,黑格尔和席勒、谢林等人代表了一种对现代性的“浪漫回应”,续写着卢梭的“论文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既在各种努力中联合起来拒斥现代制度的抽象、物质主义的“非人性化”的本质,又不准备回归前现代的思想形式。
然而同样众所周知的是,黑格尔在耶拿期间,虽然从未完全放弃这些希腊和基督教情愫,但他也开始拒绝基于怀旧或审美经验对启蒙运动的批评。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以及他对他所第一次加以理论化的“市民社会”的日益关注,使他相信现代社会和经济生活形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此外更重要的是,现代性问题的扩大。除了对现代社会的“异化”特征进行了著名的分析外,黑格尔还开始更加注重“理性”的独特现代形式及其说明和论证。尤其是,他对康德“第一批判”,而非仅仅“第二批判”和“第三批判”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兴趣的迅速增长,改变了他对现代哲学本质及其在现代制度中作用的理解。
他仍然以同样的方式构想了“现代问题”。现在,正是理性的典型现代概念,康德的自我立法或自我根据的纯粹理性,被认为是“异化了”,单纯无保证地“假设”自己是最高权威,隔绝于自然或事物自身,从而搅扰于怀疑论和一种心理哲学,并永久对立于内心的倾向和内容。正是这种对现代人完全“自主”之希望如此重要的理性概念,据说是不可接受地“有限的”、形式的、空虚的、无建构地消极批判的,从而不令人满意的。现代性问题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尽管可能晦涩的,一种关于个人与现代制度之间和解的黑格尔问题,但现在提出的解决方案据说是最终建立在对现代“反思哲学”的完成和超越之上的。现代哲学“将存在的独断主义改造成思维的独断主义”,并进展为黑格尔现在要解决的基本现代悖论。他声称,“真正的哲学”现在将从这一完成了的主体性哲学中显露出来,从而这一哲学革命将有助于建立核心的现代观念,即“绝对自由的观念”。
对许多评论者来说,这种坚称鱼与熊掌兼得的典型黑格尔式主张使黑格尔免于怀旧的指控,只不过代价是一种深深的、可能致命的晦涩。因为,正如熟知的批评所说,他能做到这一切的唯一办法,与他眼下所接受的现代主体性和反思的前提一致,是借助绝对的主体性理论,借助一方面把主体确定性和自我满足之间、另一方面把客观性和社会性之间的对立,解释为最终在某个单一的“宏大主体”或自我意识的上帝中的“扬弃”;亦即通过某种对一切“它在性”的理论否定,从而“总体化”一个自我意识的主体为“整体”。
哈贝马斯最近表达了这一标准观点,他声称黑格尔的解决方案“将理性设想为一个绝对精神的和解性的自我认识”,它“压倒了每一种[有限的]绝对化并作为无条件者,只处于对自身关系的无限处理,这种自身关系将一切有限物吞没于自身之内”。
或者,黑格尔“解决了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原初问题,但好得有些过头了”。
现在哈贝马斯有自己的理由用这种方式来描述黑格尔。他想确证更加怀旧的青年黑格尔的直觉,以表明黑格尔当时至少正在朝着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或至少是主体间性理论努力,该理论最终由哈贝马斯自己完成。在哈贝马斯的有影响力的叙述中(我将在本章最后一节中详述),黑格尔关于“认识论向社会理论转变”的所有示意,都代表了现代“意识哲学”的缩影,即首先怀疑、其次确保了主体的主张表现了客体、或客观地进行了判断的尝试,以及主体有意识地表象自身,可以成功地指向对象和提出关于对象的主张,而不只是自身的意识状态的主张。据说黑格尔“错过”了革新现代哲学问题的机会;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根本问题不在于表象对象的可能性(或客观判断、反映、意向性,或所有熟知的后笛卡尔问题),而在于交往活动,沟通理解的语言成就和主体间理解的可能性。表象对象的活动可以被视为根本依赖于社会、语言活动的;所有关于对象、行为、他人等的有意义主张,都可以理解为社会可交互的“有效性主张”的功能,而这种交互的条件(针对不同类型的有效性主张)在理想的言语情境中可以得到阐明。主-客模式的首要地位可以被主体-主体模式取代,而所有现代怀疑主义和异化(“乡愁”)问题都会得以避免。
这种一般批判主义的黑格尔理论立场,自左派黑格尔以来和在整个批判理论传统中已经相当常见。它们响应了阿多诺曾经提出的一个更具争议性的特征。作为书斋中的人类学家,他对观念论的返祖冲动加以思辨,并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评论道:
观念论——最明显地在费希特那里——无意识地左右着关于非我、他者,以及最终所有的关于自然低于我们,从而自我保存思想的联合会毫无顾忌地吞没自然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体系中腹部翻转为头脑,而愤怒是每一种观念论的标识。
无论多么富有争议,这一解释似乎与黑格尔在《哲学全书》“逻辑学”逻辑中的主张直接呼应,“人类全部努力的倾向都是去理解世界,使它适合于、服从于自己:为了这个目的,世界的积极现实必须像它被粉碎、被打破的样子,换言之,理想化了的样子。
这些证据似乎表明,黑格尔意在确证他所认作现代性的理论原则的东西——各种所谓的自我意识,或主体性,或更通常的说法、绝对自由——而这个结论仅仅借助了对哈贝马斯、阿多诺以及在他们之前许多其他人,如晚期谢林、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和叔本华所赋予黑格尔的极端地位的维护而得出。理论和实践的自由或许不会通过操纵或控制他人的培根主义掌控模式实现,但它仍然含有一种对抗偶然性或它在性的典型现代愤怒,一种思辨“吞噬”的否定,一种对显然偶然事件的重新解释,或者其实假设了一种无约束自规定精神。我在这里想捍卫一种看待黑格尔的理论现代主义的不同视角,而我的问题是,是否有其他某种方式来理解诸如刚才引用的这类表述,或随后这句摘自《差别》的话所表达的不同主张:“世界是理智自由的产物,这是观念论的规定和表达原则。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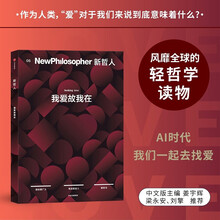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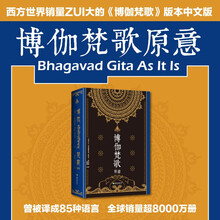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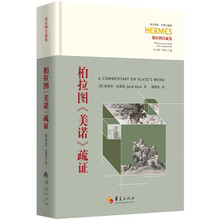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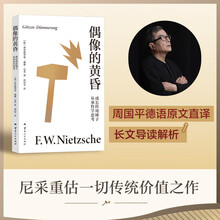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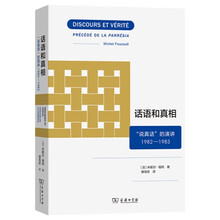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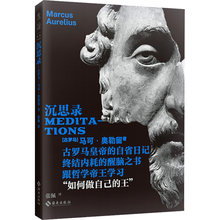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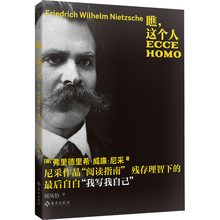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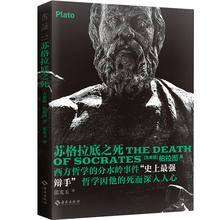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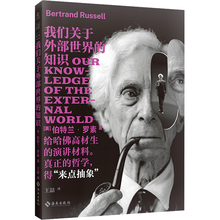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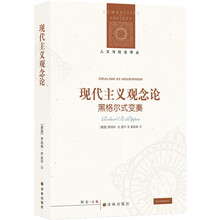
——《选择》
本书中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内容。皮平创造性地借鉴了黑格尔的对话,并且对黑格尔对当代问题的贡献有着深刻的理解。
——《形而上学评论》
皮平对黑格尔哲学的洞察力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分析黑格尔所发现的欲望与自我意识之间的联系时,其思想的深度也显而易见。
——萨莉·塞奇威克,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