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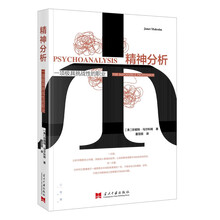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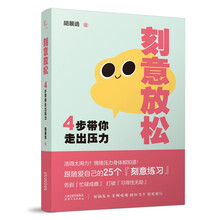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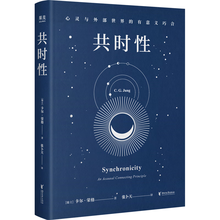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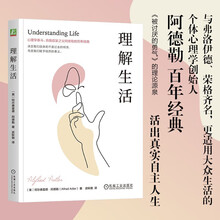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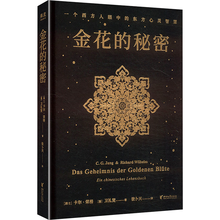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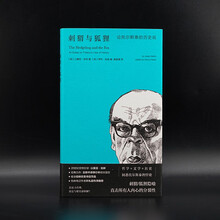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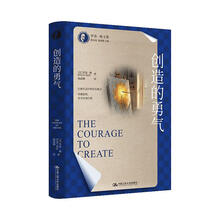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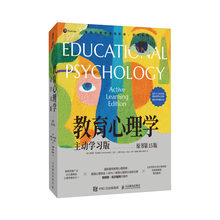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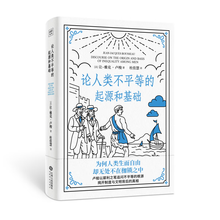
(1)模糊的丧失开创之作,帮助人们应对变故、失去与未解决的伤痛。全面、具体、深刻,最具说服力的模糊的丧失研究。精准捕获社会群体心理,对一种隐蔽但常见的伤痛情绪做出清晰的描述、深刻的剖析和充满关怀的建议。
模糊的丧失,是一种不明确且缺乏告别的丧失,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与传统意义的丧失不同,社会对此缺乏明显的界定、认可或仪式,人们不知道改如何应对。
本书首先通过精确地语言,来定义、描述人人普遍都会经历但是一直难以描述的状态。模糊的丧失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身体丧失。某位家庭成员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极端案例比如战争中失踪的士兵、被绑架的儿童,更普遍的情况是离异和领养家庭中的丧失,父亲、母亲或者孩子的身份是模糊的。第二种,认知或情感丧失。有些人虽然就在身边,但在精神层面无法沟通。比如阿尔茨海默病、成瘾症和其他慢性精神疾病患者,伴侣出轨、孩子叛逆、父母年纪大了变得健忘,过度沉迷于工作或个人兴趣爱好忽视他人的人也属于这一类。
本书剖析了模糊的丧失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个人的丧失感越模糊,就越难掌控情绪,产生抑郁、焦虑和家庭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作者给予多年研究,对缓解模糊丧失带来的压力提出了应对之法,她建议有相似问题的夫妻和家庭成员坐在一起讨论、交流,互相分享信息、看法和感受,珍惜目前拥有的,并哀悼已经丧失的。人们以此来得到认可和理解,然后继续走完悲伤的旅程,好好生活下去。
(2)诸多心理学者引用、阐释过,却一直没有正式引进中文版的概念。许多国内的心理类媒体已经对“模糊的丧失”发表过相关讨论,结合当前社会现象进行了解读,比如打工人、母胎单身者、留守儿童、被拐卖的儿童、亲人好友离世等等。这个主题下可延展的具体话题非常广泛,本书对这些群体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3)一种人们都深切感受过,却很难精准描述的心理状态。本书涵盖了诸多日常生活中的众多主题,有极宽的适用情境,帮助人们在悬而未决中恢复正常生活。
失踪或不确定是否死亡
- 灾难导致的失踪人口,自然灾害、空难
- 绑架、走失、拐卖等
物理上消失,心理上存在
- 残疾、截肢
- 关系破裂、离婚、出轨
- 成长离家、空巢、代沟
- 工作调动、异地、失联
物理上存在,心理上消失
- 老年痴呆、脑损伤、自闭症
- 精神疾患、心理问题(解离、抑郁)
- 毒品、酒精、赌博上瘾、网络成瘾
- 关系创伤:忽视、控制
- 慢性病,确诊癌症
- 失去原来的功能,运动损伤
(4)表达一种被无数文艺作品从不同角度表达过,打动了无数人的人类共通的情绪。这种微妙的感受,是诸多文艺作品灵感的源泉,因此,这些文学描述也成为对模糊的丧失的注脚。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沈从文《边城》
·“我发现了,哀伤意味着和不在场的人一起生活。”——珍妮特·温特森《时间之间》
·“我说不定忘了很多事,只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忘了。”——《我想念我自己》
·赫勒尔德,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回来……我等了五年,直到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在心里认定你已经死了。即使你没有死,对我来说你也死了。我不会再带着你一起生活。所以,我在心里杀了你,我埋葬了你,我为你哀悼,然后整理残存的一切,继续过没有你的日子。
——奥古斯特·威尔逊,《乔·特纳的来与去》(Joe Turner’s Come and Gone)
“模糊的丧失”概念开创之作,帮助人们应对变故、失去与未解决的伤痛。
“妈妈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还有必要来看她吗?”
“孩子长大离开家之后,家好像就散了。”
“他回家就打游戏,我觉得他虽然人在家里,心却不在。”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感到一种模糊的丧失。比如,当亲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认知障碍或精神疾病时,他们的部分记忆和情感流失,好像换了一个人;当某位家庭成员下落不明,多年的朋友不告而别,我们不敢相信,也无法接受;当家庭重组之后,我们不知道该和谁更亲近……
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失去所爱之人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生漫长的潮湿。”
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保琳·博斯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模糊的丧失”的概念,用来形容这种人们普遍深切感受过,却很难精准描述的心理状态,此后一生致力于相关研究。她在本书中毫无保留、全面、深刻地分享了研究成果,指引人们哀悼已逝之物作为告别,庆祝遗留之物作为新生活的开端,保留爱意的同时,继续前行。
我在中西部的移民社区长大,社区里有很多我敬仰的长辈,他们都是从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20世纪初,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横渡大西洋,来到威斯康星州南部肥沃的山谷,准备开启更好的生活,但他们发现一切并非如想象的那般美好,因为他们和远在瑞士的亲人断了联系。二战开始之前,他们还能和亲人互相通信,每封信的末尾都要写上一句:“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记得父亲每次收到他母亲或兄弟的来信后,都会一连好几天情绪低落。而我的外祖母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留在家乡的母亲,因为贫穷和战争,她知道自己恐怕很难再踏上返乡之路,也许永远没有机会见到母亲了。
那时候,我们家总是弥漫着乡愁。我不知道家人究竟包括哪些人,也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家,是故乡的那个家还是我们现在的家?从未谋面的那些亲人真的是我的家人吗?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清楚地知道,那是我父亲和外祖母的家人。他们的思绪常常飘得很远,远方的亲人明明还在,但又无从联系,就像天人永隔。这种莫名的悲伤始终未能平复,这些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小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南部农场的家是典型的沃尔顿家庭[ 沃尔顿家庭通常是指家人都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有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还有祖父和祖母。——编者注],但在我父亲和外祖母心目中,这个家并不完整,他们心目中的大家庭应该包括那些我从未谋面的大西洋彼岸的亲人——一直留存在他们记忆中的亲人。由于距离遥远,他们和亲人难以相见,这个家有一部分是缺失的。在我生活的社区,大部分人都是移民,人们都在思念着远方的亲人和故乡的家。我很好奇,为什么大家都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丧失感和挥之不去的忧郁。曾经有很多次,我听到父亲用浓重的乡音对那些来找他咨询的年轻人说:“如果要离开你的祖国,一定不要超过三个月,否则你就再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童年时的我根本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在移民社区生活了四十多年。长大后,我考上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每天从我住的村子到学校通勤往返。后来,我离开了家乡,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的那句话。虽然我只是搬到了双子城[ 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南部的明尼阿波利斯(该州最大城市)与圣保罗(该州首府), 组成著名的双子城。——编者注],与父亲的背井离乡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我却和父亲一样感到困惑,不知哪里才是我的家。我想念家乡的亲人,原来住的老房子一直没有卖掉,至今仍然维持着原样,就好像我会随时回来一样。
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适应并融入了大城市的生活,开始打造我的新家——一个小小的公寓,并且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孩子们会在学校放假和休息日的时候过来看我,我也经常和姐姐、母亲通电话,慰藉我的思乡之情。虽然没有和家人住在一起,但我很清楚地知道,家人始终都在我身边。
离开家乡后,我们会感到失去了许多东西,内心充满不安。不过,和长辈们相比,我的情况要好很多,我并没有因为贫穷和战争与亲人失去联系。从小乡村搬到大城市,起初我也很不适应,幸运的是,最脆弱的时候,家人的爱给了我力量。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包裹,用屠宰绳牢牢地捆住,包裹上贴满邮票。打开包裹,里面是一个鞋盒,装着父亲亲手种的土豆。母亲还附上一封信,信里写道:“用土豆做汤喝吧,你一定会有回家的感觉。”确实如此。
做人口普查时,调查员会登记一个家庭的全部成员,但未必包括人们心中的家人。由于工作变动、失业、家庭破裂、战争或者个人追求,有些人离开原来的居住地,与家人分离,这些家人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有移民的经历,我对这种感受有深刻的了解,我很清楚人们是如何放下过去,拥抱全新生活的。对于移民家庭来说,既有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也有心中的家人,所以家人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背井离乡的人普遍都面临着模糊的丧失,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心中的家人和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1)否则这种无法化解的悲伤会一代代延续下去,并且会逐步加重。这就是移民和迁徙带来的后遗症,是许多个体和家庭问题的根源所在。
作为家庭治疗师和研究者,我曾经帮助过四千多个家庭。我认为,家庭既是精神实体(家人之间的精神连接),也是身体实体(家人生活在一起),我想在这两种家庭结构之间寻找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如果一直处于模糊状态,那么儿童和成人的心理都会出问题,无法正常生活。
我对“家人”的定义是很宽泛的,但我使用的标准很严格。我所说的“家人”是指我们可以长期依靠的人,他们抚慰、关心、养育、支持我们,始终与我们保持着亲密的情感。家人是陪伴我们长大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原生家庭;家人还包括我们成年后自主选择的伴侣,通常称之为自选家庭;与伴侣组成家庭后会有亲生子女,也可能有非亲生子女,或者根本没有子女。我们会成为亲戚或朋友的孩子的“阿姨”(“姑姑”)或“叔叔”(“舅舅”),或者成为伴侣的孩子的“继父”或“继母”。这样的家庭超越了单纯的血缘关系,更强调精神实体与身体实体的结合。
即便是在自己的家里,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清楚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家人。随着情况的变化,在每个家庭成员心目中,家庭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有时会增加一些人,有时又会去掉一些人。外人往往看不出一个家庭的真实状况,但是做夫妻治疗和家庭治疗的心理治疗师一定要弄清楚。模糊的丧失给人带来许多困惑和痛苦,家人的精神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减轻痛苦。
临床文献中很少提及“模糊的丧失”,但歌剧、文学和戏剧经常会描述这种现象,并且把模糊的、不确定的感受加以美化。在《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失踪十年,他的妻子佩内洛普在家等待了十年。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作品《都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中,父亲坚称在空难中丧生的儿子其实还活着。对于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我们总倾向于把它们浪漫化,奥德修斯的妻子苦等十年,《蝴蝶夫人》[ 《蝴蝶夫人》是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的一部伟大的抒情悲剧。该剧以日本为背景,叙述女主人公巧巧桑与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结婚后独守空房,等来的却是背弃。最终以巧巧桑自杀为结局。——编者注]中的女主人公结婚后独守空房,本来是悲剧,我们却当成浪漫故事来看。人们越不理解,就越会用潜意识思考,然而,对于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来说,这种充满不确性和困惑的等待一点都不浪漫。模糊的丧失让人饱受折磨,压力倍增,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普遍存在,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除了艺术家之外,很少有人专门创作相关题材的作品,只有心理治疗的相关文献和艺术作品偶有涉及。虽然现象并不新奇,但从临床研究和观察的角度对它进行的描述和定义肯定是全新的。
在人际关系中会面临的所有丧失中,模糊的丧失是最具破坏性的,因为这种丧失始终都是不确定、不明晰的。有一首古老的英国童谣就准确地描述了不确定性带来的痛苦感受:
我走上楼梯,
那个人不在那里,
今天他还是不在那里,
哦,我多么希望他能永远消失。
从这首童谣可以看出,当我们无法确定一个人“在”还是“不在”时,那种感觉是多么荒谬。人们渴望确定性,明确地知道某人已经死亡,总好过一直处于猜疑的状态。
在波斯尼亚,有位老妇人在头骨附近发现一双熟悉的鞋子,就凭此判断这个头骨是她失踪的儿子的。老妇人所经历的正是模糊的丧失,亲人下落不明,她无法确切地说出亲人是死了还是活着,是濒临死亡还是正在康复。没有亲人的任何信息,也没有官方提供的死亡证明,看不到尸体,当然也就没有葬礼,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埋葬。这种不确定性让模糊的丧失成为所有丧失中最令人痛苦的体验,它引发的症状还很容易被忽视或误诊。我们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新闻:一架飞机在佛罗里达的沼泽地坠毁,遇难者的尸体无法找到,亲人悲痛欲绝;十多年前,儿子离奇失踪,母亲为他系上了祈福的黄丝带[ 黄丝带是亲人离散后的求助标志,也是为亲人祈祷的祝福标识。——编者注];飞行员在东南亚某地被击落,儿女却仍在盼着他有一天走出丛林。
模糊的丧失大多是战争和暴力事件引起的,在日常生活中,它表现得更隐蔽,不易察觉,对人的影响也更大。比如伴侣出轨、孩子叛逆、父母年纪大了变得健忘。即使我们相信一段关系是长久的、可预测的,也无法从中获得我们渴望的绝对确定性。
模糊的丧失会给个人和家庭造成很多问题,不是因为丧失对心理产生伤害,而是因为无法掌控的局面或者外界的某种束缚阻碍了人们应对和处理悲伤。如果能针对模糊的丧失进行心理治疗,那么即使亲人的信息仍然不明确,人们也能逐渐理解、面对并继续生活下去。治疗的理论依据是:一个人的丧失感越模糊,就越难掌控情绪,产生抑郁、焦虑和家庭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有时候,亲人不在身边,你却能感知到他们的存在;有时候亲人就在身边,你却觉得他们离你很遥远。这种感觉令人无助,会引发抑郁、焦虑和人际关系问题(2)。那么,模糊的丧失何以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呢?首先,这种丧失是不确定的,让人困惑,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人们无法理解现状,问题也无从解决,因为不知道丧失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如果不确定性一直持续下去,家人往往会做出极端的反应,要么就当已经彻底失去某人,要么拒绝承认生活发生了改变。这两种做法都没有什么帮助。其次,因为丧失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人们就无法重新定义自己与亲人的关系,建立新的规则,如此一来,夫妻关系或家庭关系就陷入了僵局。如果不能从心理上彻底做个了断,他们就会一直怀抱希望,希望一切都能回到过去的样子。第三,遭遇明确的丧失后,我们通常都会举行悼念仪式,例如,在家人去世后举行葬礼。而经历模糊的丧失的人并没有官方的死亡证明,无法举行仪式,他们的感受也就得不到认可和理解。第四,模糊的丧失是荒谬的,它提醒着人们,生活并不总是合理和公正的。如果某个家庭中有家人去世,周围的人通常都会提供帮助,但如果丧失是模糊的,人们只能选择回避,而不是伸出援手。最后一点,模糊的丧失是持续性的,经历过的人告诉我,这种无休止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感到身心俱疲。
丧失之所以是模糊的,可能是因为人们没有得到确定的信息,也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对某人的状态看法不一致。比如,一个孩子的父亲是战争中失踪的士兵,父亲下落不明,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而离异家庭中的孩子知道父亲在哪里,也能经常见到他,但对于父亲是否还是家庭中的一员,孩子与母亲之间存在着分歧。
模糊的丧失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某位家庭成员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比如战争中失踪的士兵、被绑架的儿童,对于家人来说,虽然他们不在身边,但精神是相通的。这些是丧失的极端个案;而更普遍的情况是离异和领养家庭中的丧失,父亲、母亲或者孩子的身份是模糊的。
第二种,有些人虽然就在身边,但在精神层面无法沟通。在阿尔茨海默症、成瘾症和其他慢性精神疾病患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个人的脑部严重受损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先是昏迷不醒,醒来后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过度沉迷于工作或个人兴趣爱好的人也属于这一类。
关于这两种丧失以及它们带来的影响,还有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讲解。但首先,我们要知道,应对模糊的丧失的方式与应对正常的丧失是不一样的,要面对的事情完全不同。在正常的丧失中,最明确的丧失就是“死亡”,有官方出具的死亡证明,还有火化、收集骨灰、下葬、追悼会等仪式,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这是永久的丧失,可以开始哀悼。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种丧失,它通常被称之为正常性悲痛[ 正常性悲痛(Normal Grieving)是指人们在经历重大丧失后,如亲人去世或离婚等,所经历的一种情绪反应过程。这种悲痛反应被认为是正常且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编者注]。正如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1917年发表的文章《哀悼与抑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中所说:“在正常性的悲痛中,康复的目标是放下对所爱对象(人)的依赖,最终投入到新的关系中。”哀悼虽然是痛苦的,但这个过程注定会结束。从这个角度看,心理健康的人可以很好地应对丧失,并且很快建立新的关系。
但也有些人在面对明确的丧失时会出现异常反应,弗洛伊德称之为“病理性忧郁症”,今天的治疗师通常称之为“忧郁症”或“复杂性哀伤”。具体表现是对失去的东西或人一直念念不忘,始终走不出来,比如有些丧偶的人不吃东西,行为孤僻,失去父母的孤儿脾气暴躁。
而在面临模糊的丧失时,忧郁症和复杂性哀伤都是复杂情况下的正常反应:失踪士兵的母亲无数次地去战场上寻找孩子;离异家庭的小孩会因为亲生父亲的离开变得情绪不稳定;丈夫脑部受损,性情有了很大变化,妻子因此而抑郁、孤僻。模糊的丧失难以应对,因为它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而不是内在的性格缺陷引起。悲伤之所以无法化解,是因为丧失是不确定的、模糊的。
遭遇模糊的丧失的人来寻求治疗时,如果以传统的方式进行评估,很容易就能做出诊断,因为他们看上去就是功能失调,表现出焦虑、抑郁和躯体疾病的症状。治疗师和医师在诊断的时候,应该多问患者一个问题:是否经历过模糊的丧失,导致悲伤无法化解?即使是心理非常健康的人,丧失的不确定性也会削弱他们的力量,阻碍他们的行动。
如果你遭遇了模糊的丧失,陷入无法化解的悲伤,不要因此而责怪自己或家人。临床医生也不要只评估患者的内在动因。如果是正常的丧失,比如亲人去世,我们会有一个哀悼的过程,最终会得到解脱,而模糊的丧失让情况变得复杂,也让哀悼的过程变得复杂。因为情况是不确定的,人们不能开始哀悼,感觉像是丧失,但又不是真正的丧失。人们从希望坠入绝望,又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如此循环往复,抑郁、焦虑和躯体疾病也伴随而来。起初只是影响到个人,然后就会产生涟漪效应,影响到整个家庭。因为其他家庭成员会感到自己被忽视,更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觉得被抛弃了。家人过度关注丧失,导致彼此的关系变得疏远,家逐渐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
家庭不同,丧失的性质不同,其严重程度也是不同的。为了说明模糊的丧失对当代家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看约翰逊先生和妻子的案例。他们的关系还没有破裂,但彼此越来越疏远。
约翰逊先生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他打电话给我说想带妻子来做心理治疗。约翰逊夫人有抑郁症,精神科医生正在给她做药物治疗,并建议她接受家庭治疗。这对夫妇第一次来到我的诊所时,我感觉他们就像两个陌生人,彼此之间没有交流,而是单独和我对话。他们都对我讲了自己在婚姻中的困惑。“真是一团乱麻。”“我感觉我们的婚姻全是假象,再也没有温情。”约翰逊夫人说,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感到很孤独,约翰逊先生经常出差,平时会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是否能回家。她说:“他太忙了,回到家也不说话,从不过问我的生活和孩子们的情况,有时我会主动跟他聊聊,可他好像并不感兴趣。”大约在一年前,她质问他为什么在家的时间那么少,他生气地说:“对我来说事业比家庭更重要,我不喜欢在家里待着。”她听了伤心欲绝,从那以后,她的抑郁情绪加重了,每天郁郁寡欢。两个孩子已经上高中了,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她,他们只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其他时间就躲进自己的卧室,要么看电脑,要么玩手机。在我的追问下,约翰逊夫人又透露说,她母亲“患上了失智症”,她觉得母亲也在慢慢离她而去。
约翰逊家面临的问题就是模糊的丧失。约翰逊夫人的抑郁症状比较明显,除此之外夫妻二人也说不出还有什么其他感觉,但模糊的丧失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家里的每个人。他们的婚姻是个空壳,家也是空壳。要想缓解约翰逊夫人的抑郁,要么家人做出改变(孩子们有意愿改变,她丈夫没有意愿,而她的母亲是根本改变不了),要么她本人做出改变,学会接受周围环境中的模糊性。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是走中间路线,她去弄清楚哪些丧失已经无可挽回,并为之哀悼,同时弄清楚她仍然拥有的是什么,是否还有磨合、沟通、复合、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个过程是夫妻和家庭治疗的基础,在此期间,我运用的是这些年来学到的关于模糊的丧失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的知识。
大多数人在咨询室内讨论的问题是:我是谁?我究竟要怎么生活?人们渴望某种确定性,而在生活中模糊的丧失却无孔不入。这本书不仅提供了一些面对变故、与悲伤共处的建议,字里行间流露的理解、共情与支持,更是给人重建生活的力量。
——简单心理创始人、CEO 简里里